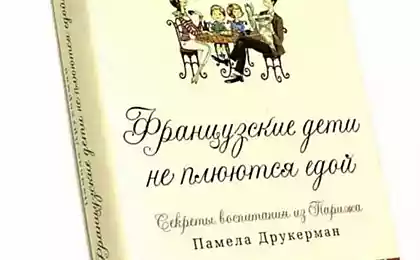455
启示大家庭的母亲

框架,从电影"你们、我和我们"
只是现在,我有四个孩子,我学会平静地回应了大胆的声明,其家长:他们的儿童将永远无法想象的东西"这种"没有让他们的孩子是永远不会用抗生素治疗,他们的孩子已经两年绘制的男子和八个可以二十个俯卧撑。 我平静地说:"75%的我的孩子也将永远不会想象这是不允许的,50%的我的孩子们从来没有用抗生素治疗,25%的儿童在两年学会了画画的男性和半悄悄地压甚至第二十和第二十五次"
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年轻的母亲一个男孩萨沙,这在我看来,我知道关于儿童的教育。 也就是说,我的孩子是一个示例的完成父母和教育的失败我的孕产妇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来到了一个不光彩的结束。 萨沙的增长无法控制的暴力和学校中没有表现出的艺术爱好或优秀人才。 在所有。 我做的一切我所能开发自己的智慧与学会的心脏知道的蒙台梭利的方法,Zaitseva,杜曼,尼基,购买杂志的文章有关儿童心理学、缝纫宝宝玩具、布的信中,塞荞麦和把古典音乐和表演册的画作的复兴。
但是,仍然在学习站在我的脚上,我的儿子成了一个暴君,他的公关和毫不妥协的、恐吓整个家庭。 他无处可去–两次访问的咖啡店和餐厅已经加冕与失败,吃剩的食物和nedoumevala-愤怒的眼神的其它访客。 因为萨沙,十八个月大,聪明的男孩,只是喊道。 他骂的房子,他大叫,在所有拥挤的地方,他大喊并且没有听到我们到处参观。 家里他把所有的电器,这可能获得甚至razvintili办公室椅子! 半年以某种方式nolavconsole与他接触,我充满了怀疑在有关的许多方法为发展儿童的智力–我决定,他们发明了一)对女孩b)对面的父母,而不是这些破烂就像我。
当我还是个妈妈的只有一个男孩萨沙,这在我看来,我知道关于儿童的健康。 萨沙,他是十一点现在–没有疼痛。 从来没有。 在所有。 只要宝宝治愈的肚脐我开始把他赤身露体,在衬衫,在一条毯子铺在地板上。 婴儿成长和发展没有帽子和袜子,得到无限量的乳牛奶睡了与他们的父母两年,并运输到海边,在一个营地,与沙子和"不卫生的条件",在六个月。 他的尿布是从来没有gladiolis,并菜都没有消毒。 所以当朋友的妈妈抱怨说,他们的孩子病了,我有我自己强烈的意见对这个问题,但自己的责任。 娇惯是不必要的。 和母乳喂养至少一年的一半。
然后我生了Katya. 如果吉亚是第一个和我唯一的孩子,我要肯定已经加入的母亲谁站在一边,与他的整听话的小小的一个,看着别人的丑脾气,说:"那是我的女孩永远都不会想象这是不允许的!"并且把一个体面的脂肪加。 卡佳是其中的一个婴儿,它们写感到困惑别人的麻烦父母:"为什么你闷闷不乐,你需要放松。 随采取的孩子与她的背包,出去走走,去展览,去看电影、参观–不是限制在四面墙壁,不要害怕,来进行宝宝你!"。 凯特从第一天睡在自己的婴儿,在另一个房间(不可想象的东西的背景下婴儿的萨沙)和可能花几个小时躺在那里,就悬挂着一侧的玩具,而她的哥哥高兴地从事地毯上的附近。 儿童嫉妒? 我有些话不知道我的孕产妇的自尊飙升。 卡蒂娜的头两个月,我们跑遍的基辅部分在切尔尼戈夫地区。 没问题留在路边吧,我甚至把凯特带他去大学和图书馆!
但在三个月内,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女儿不仅仅是一个热–她开始咳嗽。 我确信这不会发生,这不是我的现实–给孩子一些医药,导致医生在我看来,你只有更少的恐慌,更多的乳牛奶,上的磨损处理和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就是我毫无疑问,推荐其他的妈妈们有患病儿童。 我肯定这不是儿童生病,他们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咳嗽已经以某种方式失败。 医生按规定我们的一些抗生素一周前(an-ti-bi-o-ti-Ki? 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 坚定地说,因此,即使我听着,"你需要去医院。 立即执行。 在任何时刻的女孩可能开发的肺炎。"
两个星期里,我们花在医院里,越来越注射剂和各种各样的治疗。 我变得更加谨慎。 女儿生病平均每隔三个月任何病毒在空中飞行,如家用纺织品温柔无助的这个微妙的脆弱的金发碧眼的女孩和她生病了。 并且作为生病! 如果温度上升,不少于三十九! 和至少两个星期,坐在家里我们的保证。 在五年内,在春季晚些时候,当她哥哥已经游和追赤脚,在一个炎热的日,喀秋莎设法抓住双重肺炎。 七,在今年夏天,太强大喉咙痛。 八两个在一排肾盂肾炎。 谢谢卡,我学会了"阅读"血液和尿液检验,学会了如何做到注射和当繁殖的抗生素粉末喷射。 我们是众所周知,在至少三家医院的城市。 为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没有收到。
现在我之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孩子。 从出生的同样的父母亲使用同样的食物,生活在一个房间–以及令人惊讶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同的! 不可想象的,不可能为萨沙的事情他的妹妹不会轻松一样,没有这不是教。 同时,萨沙的自律、秩序、责任–外国人"在云中飞行"的卡秋莎。 我们最古老的女孩几乎没有去幼儿园,并可以坐就是几个小时,折叠拼图(沙夏,到一定年龄,这些难题ate),并提请伟大的照片。 听书,我可以读给她从早上到晚上。
如果她自己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学会了阅读和写。 但萨沙头六个月的学校是一个考验! 从幼儿园我的长子被释放与建议"的个人学习",并且坦率地说,在七年来他是绝对没有准备好的学校。 惯性,我继续为几年时间来考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失败者在每一个方式是合理的,在前一个老师,但是在五年级,它原来的萨沙是非常好的与数学。 此外,他开始读厚的小说从"库的冒险"和儿童的经典和也棘手绘制的工程绘图和地形图。
我真的很想要送他一些俱乐部,但是他从来没有抓到我们来到空手道。 四年来,萨沙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赢得一个蓝带和腹部。 儿子长大了,posolidnel,并已成为一个真正支持在家庭中负责任的组织,能够洗碗、做饭用于所有的美味的早餐,以改变一个轮胎在车里做了很多其他有用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很亲切和有益的。
当萨沙是在第一类,我有欧芙洛绪涅与尼基塔。 从第一次粗略地看一眼这个,很清楚谁是谁。 作为不同,因为白天和夜晚,他们没什么不像是哥哥和妹妹和一般的亲戚! 金发蓝眼睛,一口-一个按钮Erosia是通过性质完全的对立面,她的姐姐(投标、皮很薄的,安静)和更平静萨沙在同样的年龄。 如果萨沙"了她的"大喊大叫,欧芙洛绪涅来了更复杂和艺术的方式。 她很活泼、自信和非常有害的。 她是一个所有四个我的孩子来说一个严峻的声音,盯着的眼睛,并问:"这是什么,妈妈?" 寻找一个欧芙洛绪涅,我常常想到叹道:"我的女儿绝不会想象这是不允许的!". 同时,当欧芙洛绪涅开始画画–所有惊人的,如何确保获得招线从下她的小小胖胖的手指。
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尼基塔,出生七分钟后,棕色的眼睛(唯一一个出的四),骨,安静,顽固的和敏感的. 看这个,你知道,我看到喜欢的两个半部的一个单一的整体,补充。 尼基塔,当刚诞生了,就像一个小小的字Vizina的"操作y"。 安静,忧郁的,容易产生不合法的行动。 尼基塔喜欢的"奴隶"的妹妹和它后面的山。
在公园庆祝他的生日是能够把一个四年欧芙洛绪涅的成人"管",它不是东西,我不是害怕,并反应有谨慎的批准为严重,他说:"不是。" 尼基塔也充满了一个橡胶的环带,几乎掌握了小宝宝幻灯片,一个身高五英尺,并断然拒绝进行调查的更严重的娱乐。
当该团伙的年轻匪打开两个,我决定给他们上幼儿园。 多年来,我是一个坚定反对所有种类的学龄前机构。 长子去那里大约半年,遭受很大。 但情况下,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其他选择仍然存在。 我的女儿去大约一年,并遭受了甚至更多。 幼儿园,这可能是最糟糕的(除了医院的课程),曾经发生在她的生命。
萨莎和卡佳吸引的小舞蹈表演、组的经验教训,舞蹈和社会生活。 当然,经过几个星期我得到了使用,它们停止了哭泣的早晨,在更衣室,但是因为我继续哭从实现,我的孩子不属于那里。 "最长为六年。 在筹备组"—我在想早些时候,"不理解"家长们赞扬这些花园。 和突然冲击。 Konavoska是几乎两个,他们只是学会了去厕所和仍然不知道如何穿衣服–我把他们带到幼儿园。
我的大女儿坐在靠近我几年前的学校:安静像老鼠一样,一些绘图和切割出来的照片。 但在性质上有些儿童花园里的现场演出。 管理不善,活跃,在家里无聊,准备好团队合作Erosie和尼基塔们渴望在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们忙着与他们,恐吓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和我只是别无选择。 在这一点上,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妈妈了解绝对没有关于儿童和母亲。
我认为,为了孩子是不是有病,只是需要发脾气,并不得到抗生素"的第一个喷嚏". 它的工作具有完全的一半,我的孩子! 一旦(尽管是短暂的)我认为我的歇斯底里,在街上,减贫战略和可怕的行为取决于父母的教育。 事实上–我能教育的一个整体的儿童,他们从来不哭了,街道上的,没有家庭! 我认为,硬模式的一天喂养的遗留物的过去,但经验与双胞胎已经显示,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模式中,那么这些儿童不会成为妈妈。
在九点的房子开始撤退,并在早上七点上升。 几年前我们都去了的时候我想要醒来的时候,当我可以。 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渐进的,"绿色"。 我认为,人才的每一个孩子,表现为在早期的年龄,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的毅力。 事实上,事实证明,一切都非常个人和父母的毅力应该清单首先在儿童的发展是觉得他的爱无条件的,不管它是什么。
我真诚不了解,甚至讨厌那些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不得到卡秋莎在花园里。 现在我明白了,尽管经验,我绝对不能做任何事给任何人要建议。 所有的婴儿都是不同的,事实证明,只有母亲知道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她的孩子以及如何"权利"治疗和教育。 也许这是唯一的建议,我可以给毫无疑问,在他们自己的权利。
提交人:奥尔加Yatsenko
资料来源:d-yatsenko.livejournal.com/113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