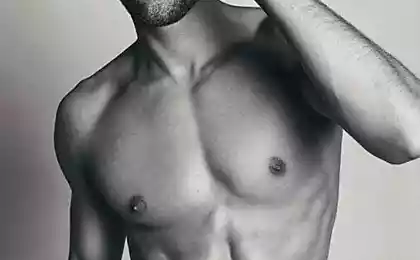1044
作为一个男人要看女人
惊人的文章谢尔盖·费多罗夫生活在一个短的皮带,或者作为男人依靠女人

当我的母亲是微笑,不管它有多好她的脸,这让好多了,周围的一切似乎veselelo。如果在生活困难的时刻,但我看得出来,微笑的一瞥,我不知道什么是山。
列夫·托尔斯泰。童年。青春期。青年
在我们的文化中,“网瘾”是画非常不利。那......和心理不健康的关系,其中扰乱能量的自然交换,但很多要求和委屈。
我想看看这个现象较为中性的,大家都是这样或那样依赖的东西为止。从空中看,食品,雇主或自然状态 - 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
。
依赖 - 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无需帮助或外部资源无法应付。体验安全的依赖,在我看来,是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帮助,照顾。相信你有权利它只是因为你的存在。
在幼儿期,孩子必须根据经验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往往就完全不同...
童年。 “爸爸可以,爸爸可以是任何人,只有我的母亲,但母亲不能!»
我,像许多苏儿,拍摄的“脏”妈妈出生后并放置几天在无菌隔离器。这是五月假期,三天后我得到的依赖经验。在她19年一位母亲,经验停滞和乳腺炎温度 - 注意力不集中,以他的口号的体验“医生最清楚»
。
(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家庭,两个大的孩子,包括我在内,没有给我妈了三天,我们都既紧张作为一个孩子睡恶心和两个年轻的已经获准把我母亲的肚子里,让其品尝初乳第一滴宝贵的。 - 他们更安静,更在晚上睡觉。)
更进一步:斯波克博士与他的母亲和儿童,解离的想法“断”生物种植护理方案,您的孩子的感受。而作为这种做法的结果 - 不想哭就哭,也无济于事。无助和恐惧的经历,我想。
我三个月的未来的妻子,年轻的父母单独留在家里,去电影院看电影。尽可能多的尖叫,关上门到房间和厨房,以免干扰。 “Pokrichit和冷静下来。”我的意思是,绝望,累了,睡着了床上紧张阳痿。良好的体验“安全”的基础。
我记得我,一个十年,如何设法得到了一块关心和照顾。我是一个资深的,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弟弟,我母亲抽搐,金钱,时间和精力都非常缺乏。我现在是一个成年男子很多孩子和爸爸,现在我明白了头,她为什么要保存自己很好,但后来我痛苦沙哑想成为一个小的,手无寸铁,无助,感到不可分割的目的只是给我的温暖。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因为三年来,我成了一个成年人 - 出生的弟弟。我可以吸引眼球恰到好处,“成人”的行动。
当我画一幅美丽的图画在一张旧墙纸柔和的蜡笔。蜡笔崩溃在他的手中,并弄脏了裤子。画面是一个伟大的太阳和两个明亮的黄色小鸡的大眼睛。我显得很美丽的图画!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走进了她身后的房间,导致了厨房,那里有我的绘画画架。这是给你的,妈妈是最好的!注意我,拥抱,佩服!
疲惫的点头。教训你做?博客带来。
博客平手。暴怒,大喊:“你画我一个小妞!”我想,她撕碎了图纸,并投掷。燃烧的不满和羞耻。 “我不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再次痛苦的肿块在乳房再次,再次独自...
我觉得这样强烈的反应 - 而我清楚地记得和痛苦这种情况下,到目前为止 - “我投,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复发的情况,和恐怖作为催化剂,反复强化的痛苦和转向平常的生活在精神创伤的一个插曲。
青春期。 “勇敢的我们唱一首歌的疯狂!»
我不知道发生了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据我了解自己,谁往往反叛其他男人。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喜爱有用的事迹和成就往往惨败:为好,并称赞例行停机,所有的时间赢得了奥运会和未获得影院有主导作用。但种种错误的东西引起的反应!是的,说脏话,是的,羞耻的,是酒,而是一个集中回应,多少能量,只有我!
因此,开始kontrzavisimosti阶段,这需要的口号下进行的“那会敲他的眼睛 - 是母亲曲线的儿子!”这是一个奇怪的状态时,你显然似乎并不关注任何人,但内心极其敏感的听力,什么第一回事所有的 - 有显著的成年人。你要学会识别步骤的心情期待下一个动作。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关闭注意从外面,我仍然可以听到我的家人,分散各地的公寓。并戴上耳机看电影或听音乐彻头彻尾的可怕 - 我突然怀念一些重要的东西。或危险。悬疑和准备 - 这就是房子的典型状态。我很厌倦了。我不得不跑,给自己一个突破。
在成年后往往逃逸掩盖理性的论据:工作,运动,业余爱好,“在小酒馆和浴室做生意。”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此外,爱。但我知道自己,这往往是所有的方式“逃离”不在家。也有好消息 - 经过几年的心理治疗变得更加容易。房子变得温暖,更舒适,焦虑减少,你甚至可以有乐趣。
Kontrzavisimosti只能从表面上瘾不同。事实上,与“减”这种关系 - 做相反。在我看来,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人也依赖于舆论和显著等的状态。这是常见的那么多男人,因为类似的外观不自由的形象,这是我们社会的转换。自由与财大气粗的力量 - 阳刚之气的主要特点
。
而往往这背后屏幕财大气粗的独立性隐藏一点小小的遗憾,抽鼻子擦的不满男孩的眼泪五岁左右。而对于更大的说服力重复像一个口头禅:“我不伤心,快乐的鸡!”这个不幸的年轻人里面流放深,没收和隔离。因为它是无法忍受一遍活...只有滑稽正在成为一个蓬勃发展和鲁莽!妈妈,注意我。妈妈!..
青春。 “自由的鹦鹉!»
最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男孩是够老的年轻人,可以在妈妈的脸上扔:“我想 - 走开!”。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入场的机构。倚负担自由的激励和惊吓。不要与任何人争,无处获得在童年缺少了什么。一个完形不闭合!
我父亲的部门 - 我通过参加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Mekhmat处理这个。爸爸说哭了,当我进入。我没有看到。这是“骄傲»。
然而,从密歇根州立大学学生戏剧工作坊多余的情感。要放置感官,这里面冷落的线圈。这个“都注意到»。
但是,这一切是不是!所有的进步都是别人受损起初很高兴逐渐需要更多关注的目光。托基停止。因为它不是!这就像吃所有的,当你想拥抱的时间。因为它需要一个“好妈妈” - 这将拥抱,倾听,理解,平静。也许,然后一个年轻人选择了一个清晰的路径 - 结婚!甚至在他的家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心理学家说,与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这是非常相似的父母......不一定对外一个声音。但在一些重要的(甚至是痛苦的)性能。我叫它为我自己:我的蟑螂寻找友好的外国元首。如果你是 - 很多情感!他的!
在19岁时,我结婚了。在老同学 - 我有时间来研究自然,蟑螂批准。爱疯了,情绪 - 乱舞。他们开始约会在五月和十月结婚了。她还在18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起,我相信 - 很好居住。我很高兴,人生从此发达。一个良好的,充满生机。但现在还不是这个。
几年前的日常的生活和令人难以忍受的重力,当满足他们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的方式通常,导致我们到了穷途末路郁闷的感觉。然后,分开,以心理治疗师。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个人和共同生活。
我们总是谈了很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变得更加诚实,语言表达什么是不可以接受,不愉快的:在家庭电源,约不信任约约的相互不满......期望
我一直以为我是很无私的。我一般不从别人的需要。从他的妻子了。原来,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诚实的对话与他们使我这个发现。
从他的妻子,我需要注意。我很苛刻,它有义务将其提供给我对我的任何愿望。
从他的妻子,我需要审批。批准所有我的想法,计划和项目。我的行为的批准。这类似于所谓的全面和客观的验收。他们说,这是唯一可能的母亲和无意识的,完全依赖婴儿之间,说长达一年或两年。它不应该生气,批评。甚至不理会不准。
妻子应该分享我的责任。未经其批准,我拿起的情况。如果你碰巧费尔,它不是那么糟糕。毕竟,它被批准的话,不要骂。
我希望他的妻子将是一个“好妈妈”。这就是一个没有。看到另一个活着的人,谁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决定到附近的生活 - 的艰巨任务
妈妈,我给你带来了鸡!
因此,这影响了“强和自由”的人吗?这样的威胁,并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识别/拒绝,批准/批评,屈尊/冷...易半圈的头,微微不屑的鬼脸不够热情的反应 -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是一个触发器,催化剂为整个风暴。不用说,那受伤的人可以uglyadet痛苦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很显然如此的平静和自信的人都是手工敲在桌子上。或举起手。或转走轻蔑。或者他用冰冷的礼貌毁灭性说。根据我从我的父母......了解到
静默或者说,他是单身,“妈妈,我发现我的母亲抱着我,妈妈!我给你带来了一只鸡 - 最好的,我有。妈妈!»
谢尔盖·费多罗夫
完形治疗师,企业教练,
IT专家,CEO积分。
学历:莫斯科国立大学(教师),以及莫斯科完形学院
。 结婚19年来,有三个孩子。

当我的母亲是微笑,不管它有多好她的脸,这让好多了,周围的一切似乎veselelo。如果在生活困难的时刻,但我看得出来,微笑的一瞥,我不知道什么是山。
列夫·托尔斯泰。童年。青春期。青年
在我们的文化中,“网瘾”是画非常不利。那......和心理不健康的关系,其中扰乱能量的自然交换,但很多要求和委屈。
我想看看这个现象较为中性的,大家都是这样或那样依赖的东西为止。从空中看,食品,雇主或自然状态 - 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
。
依赖 - 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无需帮助或外部资源无法应付。体验安全的依赖,在我看来,是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帮助,照顾。相信你有权利它只是因为你的存在。
在幼儿期,孩子必须根据经验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往往就完全不同...
童年。 “爸爸可以,爸爸可以是任何人,只有我的母亲,但母亲不能!»
我,像许多苏儿,拍摄的“脏”妈妈出生后并放置几天在无菌隔离器。这是五月假期,三天后我得到的依赖经验。在她19年一位母亲,经验停滞和乳腺炎温度 - 注意力不集中,以他的口号的体验“医生最清楚»
。
(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家庭,两个大的孩子,包括我在内,没有给我妈了三天,我们都既紧张作为一个孩子睡恶心和两个年轻的已经获准把我母亲的肚子里,让其品尝初乳第一滴宝贵的。 - 他们更安静,更在晚上睡觉。)
更进一步:斯波克博士与他的母亲和儿童,解离的想法“断”生物种植护理方案,您的孩子的感受。而作为这种做法的结果 - 不想哭就哭,也无济于事。无助和恐惧的经历,我想。
我三个月的未来的妻子,年轻的父母单独留在家里,去电影院看电影。尽可能多的尖叫,关上门到房间和厨房,以免干扰。 “Pokrichit和冷静下来。”我的意思是,绝望,累了,睡着了床上紧张阳痿。良好的体验“安全”的基础。
我记得我,一个十年,如何设法得到了一块关心和照顾。我是一个资深的,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弟弟,我母亲抽搐,金钱,时间和精力都非常缺乏。我现在是一个成年男子很多孩子和爸爸,现在我明白了头,她为什么要保存自己很好,但后来我痛苦沙哑想成为一个小的,手无寸铁,无助,感到不可分割的目的只是给我的温暖。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因为三年来,我成了一个成年人 - 出生的弟弟。我可以吸引眼球恰到好处,“成人”的行动。
当我画一幅美丽的图画在一张旧墙纸柔和的蜡笔。蜡笔崩溃在他的手中,并弄脏了裤子。画面是一个伟大的太阳和两个明亮的黄色小鸡的大眼睛。我显得很美丽的图画!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走进了她身后的房间,导致了厨房,那里有我的绘画画架。这是给你的,妈妈是最好的!注意我,拥抱,佩服!
疲惫的点头。教训你做?博客带来。
博客平手。暴怒,大喊:“你画我一个小妞!”我想,她撕碎了图纸,并投掷。燃烧的不满和羞耻。 “我不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再次痛苦的肿块在乳房再次,再次独自...
我觉得这样强烈的反应 - 而我清楚地记得和痛苦这种情况下,到目前为止 - “我投,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复发的情况,和恐怖作为催化剂,反复强化的痛苦和转向平常的生活在精神创伤的一个插曲。
青春期。 “勇敢的我们唱一首歌的疯狂!»
我不知道发生了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据我了解自己,谁往往反叛其他男人。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喜爱有用的事迹和成就往往惨败:为好,并称赞例行停机,所有的时间赢得了奥运会和未获得影院有主导作用。但种种错误的东西引起的反应!是的,说脏话,是的,羞耻的,是酒,而是一个集中回应,多少能量,只有我!
因此,开始kontrzavisimosti阶段,这需要的口号下进行的“那会敲他的眼睛 - 是母亲曲线的儿子!”这是一个奇怪的状态时,你显然似乎并不关注任何人,但内心极其敏感的听力,什么第一回事所有的 - 有显著的成年人。你要学会识别步骤的心情期待下一个动作。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关闭注意从外面,我仍然可以听到我的家人,分散各地的公寓。并戴上耳机看电影或听音乐彻头彻尾的可怕 - 我突然怀念一些重要的东西。或危险。悬疑和准备 - 这就是房子的典型状态。我很厌倦了。我不得不跑,给自己一个突破。
在成年后往往逃逸掩盖理性的论据:工作,运动,业余爱好,“在小酒馆和浴室做生意。”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此外,爱。但我知道自己,这往往是所有的方式“逃离”不在家。也有好消息 - 经过几年的心理治疗变得更加容易。房子变得温暖,更舒适,焦虑减少,你甚至可以有乐趣。
Kontrzavisimosti只能从表面上瘾不同。事实上,与“减”这种关系 - 做相反。在我看来,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人也依赖于舆论和显著等的状态。这是常见的那么多男人,因为类似的外观不自由的形象,这是我们社会的转换。自由与财大气粗的力量 - 阳刚之气的主要特点
。
而往往这背后屏幕财大气粗的独立性隐藏一点小小的遗憾,抽鼻子擦的不满男孩的眼泪五岁左右。而对于更大的说服力重复像一个口头禅:“我不伤心,快乐的鸡!”这个不幸的年轻人里面流放深,没收和隔离。因为它是无法忍受一遍活...只有滑稽正在成为一个蓬勃发展和鲁莽!妈妈,注意我。妈妈!..
青春。 “自由的鹦鹉!»
最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男孩是够老的年轻人,可以在妈妈的脸上扔:“我想 - 走开!”。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入场的机构。倚负担自由的激励和惊吓。不要与任何人争,无处获得在童年缺少了什么。一个完形不闭合!
我父亲的部门 - 我通过参加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Mekhmat处理这个。爸爸说哭了,当我进入。我没有看到。这是“骄傲»。
然而,从密歇根州立大学学生戏剧工作坊多余的情感。要放置感官,这里面冷落的线圈。这个“都注意到»。
但是,这一切是不是!所有的进步都是别人受损起初很高兴逐渐需要更多关注的目光。托基停止。因为它不是!这就像吃所有的,当你想拥抱的时间。因为它需要一个“好妈妈” - 这将拥抱,倾听,理解,平静。也许,然后一个年轻人选择了一个清晰的路径 - 结婚!甚至在他的家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心理学家说,与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这是非常相似的父母......不一定对外一个声音。但在一些重要的(甚至是痛苦的)性能。我叫它为我自己:我的蟑螂寻找友好的外国元首。如果你是 - 很多情感!他的!
在19岁时,我结婚了。在老同学 - 我有时间来研究自然,蟑螂批准。爱疯了,情绪 - 乱舞。他们开始约会在五月和十月结婚了。她还在18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起,我相信 - 很好居住。我很高兴,人生从此发达。一个良好的,充满生机。但现在还不是这个。
几年前的日常的生活和令人难以忍受的重力,当满足他们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的方式通常,导致我们到了穷途末路郁闷的感觉。然后,分开,以心理治疗师。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个人和共同生活。
我们总是谈了很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变得更加诚实,语言表达什么是不可以接受,不愉快的:在家庭电源,约不信任约约的相互不满......期望
我一直以为我是很无私的。我一般不从别人的需要。从他的妻子了。原来,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诚实的对话与他们使我这个发现。
从他的妻子,我需要注意。我很苛刻,它有义务将其提供给我对我的任何愿望。
从他的妻子,我需要审批。批准所有我的想法,计划和项目。我的行为的批准。这类似于所谓的全面和客观的验收。他们说,这是唯一可能的母亲和无意识的,完全依赖婴儿之间,说长达一年或两年。它不应该生气,批评。甚至不理会不准。
妻子应该分享我的责任。未经其批准,我拿起的情况。如果你碰巧费尔,它不是那么糟糕。毕竟,它被批准的话,不要骂。
我希望他的妻子将是一个“好妈妈”。这就是一个没有。看到另一个活着的人,谁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决定到附近的生活 - 的艰巨任务
妈妈,我给你带来了鸡!
因此,这影响了“强和自由”的人吗?这样的威胁,并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识别/拒绝,批准/批评,屈尊/冷...易半圈的头,微微不屑的鬼脸不够热情的反应 -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是一个触发器,催化剂为整个风暴。不用说,那受伤的人可以uglyadet痛苦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很显然如此的平静和自信的人都是手工敲在桌子上。或举起手。或转走轻蔑。或者他用冰冷的礼貌毁灭性说。根据我从我的父母......了解到
静默或者说,他是单身,“妈妈,我发现我的母亲抱着我,妈妈!我给你带来了一只鸡 - 最好的,我有。妈妈!»
谢尔盖·费多罗夫
完形治疗师,企业教练,
IT专家,CEO积分。
学历:莫斯科国立大学(教师),以及莫斯科完形学院
。 结婚19年来,有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