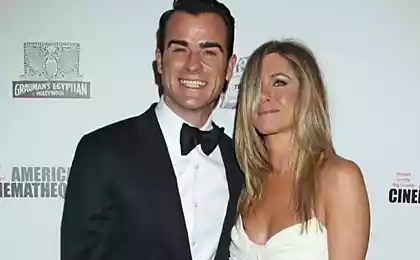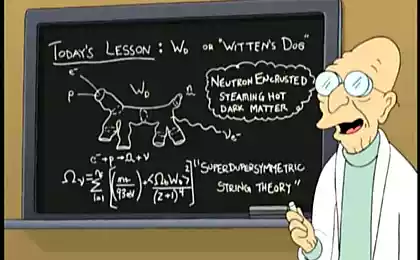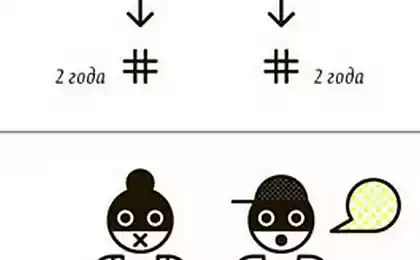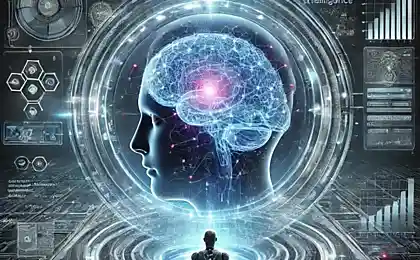896
生命菲利普·西摩·霍夫曼规则
菲利普·西摩·霍夫曼
演员于2014年2月2日在纽约去世
46岁
我想我是个糟糕的演员。毕竟,我不知道这更难:说“是”或者说“不»
。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开始演电影。我一直以为我会半生切三明治便宜的晚餐,然后娶了厚厚的下垂胸部一些傻瓜。
我当了演员意外。我认真从事的斗争,再大伤了他的脖子。随着战斗已经结束了。我正要过棒球,突然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们有一些东西打动了她,我想,“也许一个演员?”我记得那天晚上我问上帝:“主啊,我可以冲上去打棒球吗?毕竟,我很喜欢这个女孩。“我没听到答案,但是,很显然,他说:“是»。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菲利普·西摩·霍夫曼。通常,我会感到恼火,当人们使用他的中间名。我觉得很造作。但是,这不是我的情况。就在那一刻,当我在电影院里,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一个名为菲利普·霍夫曼,霍夫曼菲利普和两个男主角之一 - 这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添加西摩。
但我是一个有点高于每个人都认为,
很多人叫我背着我胖子。也有人说,我是矮子。有人写道,我的脸就像面团,和头发 - 拖。但听着,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男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人会想到来形容我与一个有吸引力的一面。我一直在等待有人写我,我很可爱。或者有趣。但该死的,大家都安静下来。在另一方面,我想我应该感谢的事实,胖混蛋我没有叫过。
我喜欢我的身体和我的出现让我玩是一个我最有趣的 - 任何人
我真的很想在玩“谋杀绿脚趾”,但在此之前,我认为长:这是地狱,科恩兄弟,和我的合同之下居住与他们。所以我决定只是来给他们做一些事情很奇怪。在一般情况下,我来了,开始尖叫和愤怒。突然间,他们就开始笑,那么响亮,他们,在我看来,小屁股没有破裂。我还记得我是怎么看的笑科恩和思想,“好了,管它呢,这个角色。虽然嘶鸣 - 这是好的»
。
很长一段时间,我生活的主要成就是,有一天,许多年前,当我在泳池,去迈尔斯·戴维斯(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 - 君子)。我想,“这样的话 - 但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冷却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它发生了»。
作为一个著名的演员和做一个好演员 - 这不是一回事
。
这是第一次,我开始学习,在街道上时,我29岁。人们看着我,我的每一个动作,这当然是一个冲击。我觉得,如果他失去了他的左胳膊 - 刚才的尴尬
我不需要更多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这事做。
今天,当人们盯着我在街上或在咖啡馆,我明白,这意味着我已经辨认,并不意味着我的胡子粘大幅一块食物,或更坏的东西。但我担心有一天有人会孵化我,我将是他的笑容是老朋友,却没有意识到我的胡子伸出沉重的生菜。
成功来对待没有更严重的超过肉汁。
谢谢逐渐剥夺你怀疑。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它可以做给你。
任何人谁是能够应付的恐惧,能够应付任何事情。
我想拍一部关于恐惧。环顾四周:由神经官能症统治的星球。人们害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控制恐惧,他们害怕死亡,贫困,不断骚扰一个小的担忧。一部电影一个很好的话题,对吧?
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更害怕比它是今天,这让我觉得害怕 - 这是什么,在我们每一天成长
我很喜欢这句话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菲利普·罗斯(美国著名作家 - 时尚先生。):«老年 - 这不是一场战斗,老年 - 大屠杀“。这高兴我这么多,我甚至想重复一遍,但也许我不会。
现年42岁的我,和我的父母还活着。几乎在每一个采访中,我问,“你怎么住? - 因为你已经年迈的父母”愚蠢的问题。没有人问父母,他们如何生活与老化的孩子。
人们开始变老的那一刻。当你来到第四十条,你突然意识到你和你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杀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开始找到它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 孩子。当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曾与他们联系这么多的问题,我自己的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真的不理解孩子,很少知道他们,但我是有一点肯定的:它是最强大的消费者的爱在这个星球上。所以,如果你有孩子,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喜欢给别人。
好了,冷静:当工作对电影人中间问我不喜欢?我总是说,“不拉屎是不是很酷。”你知道什么是酷?酷 - 是当一切都结束了。当工作完成后,当所有的握手,回家去了。这时候,我的感觉:是的,这很酷
。
作为一个演员 - 这是同样的事情,作为一个举重运动员。但你提高自己的用脑的帮助的严重程度。
当你阅读 - 你觉得,当你抽烟 - 你的想法。但是,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今天,当我读到“奥赛罗”,我可以很容易地摆脱对奥巴马的看法。
如果你是一个好演员,尝试至少每年一次在影院播放 - 这是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不是说我是个好演员,但每年你能看到我在看戏。
任何电影的拍摄始终是当你醒来在黎明并且认为这样的夜晚:“妈的,怎么烂怎么办»
我的生活是永久的恐慌状态。这听起来像被判了死刑,但它始终工作。也许,某个地方在我的心脏我不想活了,既做一件事,但实际上我做一百万个不同的东西。我在电影和舞台剧,我把玩了,我最近买了一个剧团在纽约。因此,恐慌是采取 - 所有这些事情不要让我一秒钟放松。我想我就要死了,即使是在一个恐慌。但最近,这种观点成为我更加可爱。
它的工作的地方冲过来了,赚到足够的钱,足够支付账单是很重要的。但一切 - 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
我喜欢让检查与长隆号码。而且,我喜欢的好电影来行事。作为一项规则,这两件事情很少发生接触,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占用所有的好电影 - 即使他们少缴。什么做 - 我总是拿出
。
贫困 -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太不可思议了,它适合极少数人。
我喜欢变化 - 小的,大的 - 种种。但是,在一顶牛仔帽,你不会看到我的永远。
在电影“不羁夜”,我吻了马克·沃尔伯格(美国演员,音乐家,也被称为Marky马克 - 君子)。我不能说,吻一个吻。
我的头,也许大小,真是疯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尼姑的下午。
我还没有买下此岛。
演员于2014年2月2日在纽约去世
46岁
我想我是个糟糕的演员。毕竟,我不知道这更难:说“是”或者说“不»
。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开始演电影。我一直以为我会半生切三明治便宜的晚餐,然后娶了厚厚的下垂胸部一些傻瓜。
我当了演员意外。我认真从事的斗争,再大伤了他的脖子。随着战斗已经结束了。我正要过棒球,突然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们有一些东西打动了她,我想,“也许一个演员?”我记得那天晚上我问上帝:“主啊,我可以冲上去打棒球吗?毕竟,我很喜欢这个女孩。“我没听到答案,但是,很显然,他说:“是»。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菲利普·西摩·霍夫曼。通常,我会感到恼火,当人们使用他的中间名。我觉得很造作。但是,这不是我的情况。就在那一刻,当我在电影院里,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一个名为菲利普·霍夫曼,霍夫曼菲利普和两个男主角之一 - 这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添加西摩。
但我是一个有点高于每个人都认为,
很多人叫我背着我胖子。也有人说,我是矮子。有人写道,我的脸就像面团,和头发 - 拖。但听着,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男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人会想到来形容我与一个有吸引力的一面。我一直在等待有人写我,我很可爱。或者有趣。但该死的,大家都安静下来。在另一方面,我想我应该感谢的事实,胖混蛋我没有叫过。
我喜欢我的身体和我的出现让我玩是一个我最有趣的 - 任何人
我真的很想在玩“谋杀绿脚趾”,但在此之前,我认为长:这是地狱,科恩兄弟,和我的合同之下居住与他们。所以我决定只是来给他们做一些事情很奇怪。在一般情况下,我来了,开始尖叫和愤怒。突然间,他们就开始笑,那么响亮,他们,在我看来,小屁股没有破裂。我还记得我是怎么看的笑科恩和思想,“好了,管它呢,这个角色。虽然嘶鸣 - 这是好的»
。
很长一段时间,我生活的主要成就是,有一天,许多年前,当我在泳池,去迈尔斯·戴维斯(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 - 君子)。我想,“这样的话 - 但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冷却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它发生了»。
作为一个著名的演员和做一个好演员 - 这不是一回事
。
这是第一次,我开始学习,在街道上时,我29岁。人们看着我,我的每一个动作,这当然是一个冲击。我觉得,如果他失去了他的左胳膊 - 刚才的尴尬
我不需要更多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这事做。
今天,当人们盯着我在街上或在咖啡馆,我明白,这意味着我已经辨认,并不意味着我的胡子粘大幅一块食物,或更坏的东西。但我担心有一天有人会孵化我,我将是他的笑容是老朋友,却没有意识到我的胡子伸出沉重的生菜。
成功来对待没有更严重的超过肉汁。
谢谢逐渐剥夺你怀疑。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它可以做给你。
任何人谁是能够应付的恐惧,能够应付任何事情。
我想拍一部关于恐惧。环顾四周:由神经官能症统治的星球。人们害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控制恐惧,他们害怕死亡,贫困,不断骚扰一个小的担忧。一部电影一个很好的话题,对吧?
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更害怕比它是今天,这让我觉得害怕 - 这是什么,在我们每一天成长
我很喜欢这句话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菲利普·罗斯(美国著名作家 - 时尚先生。):«老年 - 这不是一场战斗,老年 - 大屠杀“。这高兴我这么多,我甚至想重复一遍,但也许我不会。
现年42岁的我,和我的父母还活着。几乎在每一个采访中,我问,“你怎么住? - 因为你已经年迈的父母”愚蠢的问题。没有人问父母,他们如何生活与老化的孩子。
人们开始变老的那一刻。当你来到第四十条,你突然意识到你和你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杀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开始找到它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 孩子。当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曾与他们联系这么多的问题,我自己的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真的不理解孩子,很少知道他们,但我是有一点肯定的:它是最强大的消费者的爱在这个星球上。所以,如果你有孩子,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喜欢给别人。
好了,冷静:当工作对电影人中间问我不喜欢?我总是说,“不拉屎是不是很酷。”你知道什么是酷?酷 - 是当一切都结束了。当工作完成后,当所有的握手,回家去了。这时候,我的感觉:是的,这很酷
。
作为一个演员 - 这是同样的事情,作为一个举重运动员。但你提高自己的用脑的帮助的严重程度。
当你阅读 - 你觉得,当你抽烟 - 你的想法。但是,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今天,当我读到“奥赛罗”,我可以很容易地摆脱对奥巴马的看法。
如果你是一个好演员,尝试至少每年一次在影院播放 - 这是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不是说我是个好演员,但每年你能看到我在看戏。
任何电影的拍摄始终是当你醒来在黎明并且认为这样的夜晚:“妈的,怎么烂怎么办»
我的生活是永久的恐慌状态。这听起来像被判了死刑,但它始终工作。也许,某个地方在我的心脏我不想活了,既做一件事,但实际上我做一百万个不同的东西。我在电影和舞台剧,我把玩了,我最近买了一个剧团在纽约。因此,恐慌是采取 - 所有这些事情不要让我一秒钟放松。我想我就要死了,即使是在一个恐慌。但最近,这种观点成为我更加可爱。
它的工作的地方冲过来了,赚到足够的钱,足够支付账单是很重要的。但一切 - 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
我喜欢让检查与长隆号码。而且,我喜欢的好电影来行事。作为一项规则,这两件事情很少发生接触,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占用所有的好电影 - 即使他们少缴。什么做 - 我总是拿出
。
贫困 -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太不可思议了,它适合极少数人。
我喜欢变化 - 小的,大的 - 种种。但是,在一顶牛仔帽,你不会看到我的永远。
在电影“不羁夜”,我吻了马克·沃尔伯格(美国演员,音乐家,也被称为Marky马克 - 君子)。我不能说,吻一个吻。
我的头,也许大小,真是疯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尼姑的下午。
我还没有买下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