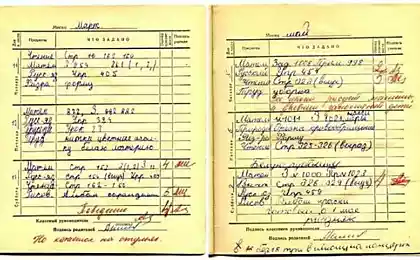516
我的故事是从日记
问候读者狂吠,这是我的第一个个人故事,从中我一直在他在北高加索地区服务的时间日记服用,可能会有点乱,不正确的,但是从心脏!我会尝试写没有医疗条件,很显然给读者!所以...
这是我的博客...
在那遥远的1999年,我只接受了医疗服务,军医,外科医生中尉的头衔,所以即使打电话给我们。而像许多年轻的军官,立即发送该请求的报告给我的任务是车臣。因为他知道,我觉得在那里我会更需要比这里把削减兵“应征入伍者。”反正我不喜欢写有关。
和2000年1月7日,我在城市附近格罗兹尼,当时的攻击开始了,咆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确实有点疯了,我记得。但经验丰富的“Prapor”看到我的圆圆的眼睛,说挨了两天来习惯。
下一步我们是674 BB desantura一个团,摩托化步兵不记得是谁了,各种好,“铠甲”。
该野战医院是一个大帐篷,灶具,“火炉”发电机“tarahtyaschie”,三个操作和一个大的空间,谁正在等待发送到主要医院的病人后操作。
我得说,从船的球权作为一个年轻的首次研究,由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的协助,但时间不长,因为情况不允许。只有这样,我才意识到什么口径子弹5,45 - 一个阴险的死亡。
带在腹部(肚子),一个小洞,“开放”受伤,但有肝,肾,胃等一个完整的“馅”当然,长战斗机没有住,但还是设法收集所有的地方...
有好几次我们的位置去壳用迫击炮和轻武器,希沙。原则上,强大的失利并不适用,所以才害怕。
在这些攻击之一,一个分裂的地雷反膝盖一兵一卒,在这一刻是栅栏和附楼之间,移动波萨。他一直没有见过。他躺下,躺在。我不喊,也没有呼救,等二十分钟。我发现它偶然,当我经过我们的“功夫”嘎斯-66的方向。他问:“你躺在泥”回复“我被打伤......”“妈的,没叫什么帮助???” - 我大喊他......他没有。也许震荡。但时间......时间......就像是不够的......它丢了。我觉得到五分钟前,失血量并不重要,士兵们能够存活下来......
2000年1月15日,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在格罗兹尼,“浮动”受伤,其中一人是一名狙击手,他不想给他SVDeshku所有咕哝着和重要。在他的右手是输入火,发现子弹刺穿了肺部,停在胸部的地区,1厘米从心脏肌肉。他们不明白她为什么不问他,“收”一切就绪,幸运的战斗机,非常强大。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战斗子弹时间跳飞墙,击中了他的身边。战斗机静夜中的位置,直到他失去了知觉。他如何从内部出血死亡,仍然是个谜。几个小时后,一名士兵在“转盘»。
碎片有时子弹倾向于“轻”的入口。即血难言。如果在飞机上没有通过。最肯定的,因为针刺入身体油。防弹衣,如果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钢板,一点点帮助。作为一般规则,也不得不从中提取件。子弹在他的身上来“包装”。
一般情况下,伤员的流量是巨大的,挫伤,枪械,高地雷炸伤,经常头部中弹,作为一项规则,以失败告终。 Lyutovali敌方狙击手。佣兵,不同的花色。
2000年1月16日,“飞”UAZ球探托里“Grushnikov”毛毯“gbeshniki”图明白,没有职称,无条纹,罪恶的枪口,熏黑的脸,呼号,密码知道UAZ - 筛,拖着尸体被要求急救。我期待,且有英文的身体大叫“他妈的”“SAK”,等等。原来,十九岁时我们的“战争”,razvedchiki-破坏者,他们的母亲hildren ......在很短的战斗中被俘教练与英国,这对于“美元”的理念帮助对抗邪恶的俄罗斯占领者chicham战斗! Nafig我只是包扎了,promidol花了总部组织说,军队还没有达到。我挂在软垫俄罗斯坦克在树干。折磨问心无愧......但哦...
2000年1月17日,杀害少将米哈伊尔Malofeev,副手。指挥官集团“北”的。他战死沙场。
也许很多人认为,一般情况下,这种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老鼠”的。当然,有没有,在那些年里,只是战斗的将军。谁一直接近他的士兵和军官。
他们的手工攻击希沙,援助还没有来得及突破。杀死所有的将军和他的助手无线电操作员,一名士兵“应征入伍者”,从手榴弹拍摄,并投掷手榴弹,他们并没有让他们来给CP(指挥所),被枪杀到最后的建设。当男人走出废墟,报务员所以秉持着机器的眼泪是不可能的,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空的。在充斥着“雇佣军”谁是战斗后没有采取希沙的尸体在街上。士兵和军官都同意自己和在城市格罗兹尼的囚犯团伙之间,不要服用。我没有看到他们。
2000年1月18号,带来了5人受伤,其中非常严重,头部受伤,子弹,眼睛右侧出现,左变形,但真的没有什么做的,做的是工作,换药,处理所有收集到的“骷髅头”,因为他们可以, valilsya脚,不睡觉了近三天,也有在晚上的士兵们在城市战!解释说,唱盘vecherami-不能在夜间飞行,要有耐心,直到早上,精神上说再见。他表现出菲戈“骨”,并在凌晨5点,我们就装在船上。飞人们生活和恢复。后来我才知道他活了下来。有人严重受伤,一只眼睛失明,第二次失去了50%,但人是活的!
2000年1月19日上午,我哭了,第一次在整个行程中,可能是生命。我累了,我已经厌倦了失去的人......妈妈,我不写这封信,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心......而我在这里两个星期,上帝帮助我,这么多的死在我身边......
2000年1月22日报道,明天是推动移动集团在格罗兹尼,许多受伤的平民,就必须直接向前线提供帮助。当然,我签署了第一位。我得到盔甲“重”,一包有你需要的一切。在“功夫”(燃气66)有半个晚上觉得promidol,绷带和所有包装成袋的快速止痛药。尤金·伊万诺夫给了手榴弹F 1,表示坚守在你的口袋里,如果有希沙捕捉到最好的挺举自己......不是投降,因为鸡蛋还是切断,塞到喉咙...
1月23日上午,我们飞到2 BMPeshki我们“咆哮”罪恶的枪口攀登到最后,并迅速沉没赶赴火灾的方向吼,射击和燃烧...
未完待续....如果是这样......

<切/>
资料来源:
这是我的博客...
在那遥远的1999年,我只接受了医疗服务,军医,外科医生中尉的头衔,所以即使打电话给我们。而像许多年轻的军官,立即发送该请求的报告给我的任务是车臣。因为他知道,我觉得在那里我会更需要比这里把削减兵“应征入伍者。”反正我不喜欢写有关。
和2000年1月7日,我在城市附近格罗兹尼,当时的攻击开始了,咆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确实有点疯了,我记得。但经验丰富的“Prapor”看到我的圆圆的眼睛,说挨了两天来习惯。
下一步我们是674 BB desantura一个团,摩托化步兵不记得是谁了,各种好,“铠甲”。
该野战医院是一个大帐篷,灶具,“火炉”发电机“tarahtyaschie”,三个操作和一个大的空间,谁正在等待发送到主要医院的病人后操作。
我得说,从船的球权作为一个年轻的首次研究,由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的协助,但时间不长,因为情况不允许。只有这样,我才意识到什么口径子弹5,45 - 一个阴险的死亡。
带在腹部(肚子),一个小洞,“开放”受伤,但有肝,肾,胃等一个完整的“馅”当然,长战斗机没有住,但还是设法收集所有的地方...
有好几次我们的位置去壳用迫击炮和轻武器,希沙。原则上,强大的失利并不适用,所以才害怕。
在这些攻击之一,一个分裂的地雷反膝盖一兵一卒,在这一刻是栅栏和附楼之间,移动波萨。他一直没有见过。他躺下,躺在。我不喊,也没有呼救,等二十分钟。我发现它偶然,当我经过我们的“功夫”嘎斯-66的方向。他问:“你躺在泥”回复“我被打伤......”“妈的,没叫什么帮助???” - 我大喊他......他没有。也许震荡。但时间......时间......就像是不够的......它丢了。我觉得到五分钟前,失血量并不重要,士兵们能够存活下来......
2000年1月15日,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在格罗兹尼,“浮动”受伤,其中一人是一名狙击手,他不想给他SVDeshku所有咕哝着和重要。在他的右手是输入火,发现子弹刺穿了肺部,停在胸部的地区,1厘米从心脏肌肉。他们不明白她为什么不问他,“收”一切就绪,幸运的战斗机,非常强大。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战斗子弹时间跳飞墙,击中了他的身边。战斗机静夜中的位置,直到他失去了知觉。他如何从内部出血死亡,仍然是个谜。几个小时后,一名士兵在“转盘»。
碎片有时子弹倾向于“轻”的入口。即血难言。如果在飞机上没有通过。最肯定的,因为针刺入身体油。防弹衣,如果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钢板,一点点帮助。作为一般规则,也不得不从中提取件。子弹在他的身上来“包装”。
一般情况下,伤员的流量是巨大的,挫伤,枪械,高地雷炸伤,经常头部中弹,作为一项规则,以失败告终。 Lyutovali敌方狙击手。佣兵,不同的花色。
2000年1月16日,“飞”UAZ球探托里“Grushnikov”毛毯“gbeshniki”图明白,没有职称,无条纹,罪恶的枪口,熏黑的脸,呼号,密码知道UAZ - 筛,拖着尸体被要求急救。我期待,且有英文的身体大叫“他妈的”“SAK”,等等。原来,十九岁时我们的“战争”,razvedchiki-破坏者,他们的母亲hildren ......在很短的战斗中被俘教练与英国,这对于“美元”的理念帮助对抗邪恶的俄罗斯占领者chicham战斗! Nafig我只是包扎了,promidol花了总部组织说,军队还没有达到。我挂在软垫俄罗斯坦克在树干。折磨问心无愧......但哦...
2000年1月17日,杀害少将米哈伊尔Malofeev,副手。指挥官集团“北”的。他战死沙场。
也许很多人认为,一般情况下,这种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老鼠”的。当然,有没有,在那些年里,只是战斗的将军。谁一直接近他的士兵和军官。
他们的手工攻击希沙,援助还没有来得及突破。杀死所有的将军和他的助手无线电操作员,一名士兵“应征入伍者”,从手榴弹拍摄,并投掷手榴弹,他们并没有让他们来给CP(指挥所),被枪杀到最后的建设。当男人走出废墟,报务员所以秉持着机器的眼泪是不可能的,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空的。在充斥着“雇佣军”谁是战斗后没有采取希沙的尸体在街上。士兵和军官都同意自己和在城市格罗兹尼的囚犯团伙之间,不要服用。我没有看到他们。
2000年1月18号,带来了5人受伤,其中非常严重,头部受伤,子弹,眼睛右侧出现,左变形,但真的没有什么做的,做的是工作,换药,处理所有收集到的“骷髅头”,因为他们可以, valilsya脚,不睡觉了近三天,也有在晚上的士兵们在城市战!解释说,唱盘vecherami-不能在夜间飞行,要有耐心,直到早上,精神上说再见。他表现出菲戈“骨”,并在凌晨5点,我们就装在船上。飞人们生活和恢复。后来我才知道他活了下来。有人严重受伤,一只眼睛失明,第二次失去了50%,但人是活的!
2000年1月19日上午,我哭了,第一次在整个行程中,可能是生命。我累了,我已经厌倦了失去的人......妈妈,我不写这封信,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心......而我在这里两个星期,上帝帮助我,这么多的死在我身边......
2000年1月22日报道,明天是推动移动集团在格罗兹尼,许多受伤的平民,就必须直接向前线提供帮助。当然,我签署了第一位。我得到盔甲“重”,一包有你需要的一切。在“功夫”(燃气66)有半个晚上觉得promidol,绷带和所有包装成袋的快速止痛药。尤金·伊万诺夫给了手榴弹F 1,表示坚守在你的口袋里,如果有希沙捕捉到最好的挺举自己......不是投降,因为鸡蛋还是切断,塞到喉咙...
1月23日上午,我们飞到2 BMPeshki我们“咆哮”罪恶的枪口攀登到最后,并迅速沉没赶赴火灾的方向吼,射击和燃烧...
未完待续....如果是这样......

<切/>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