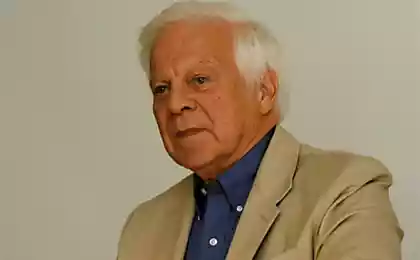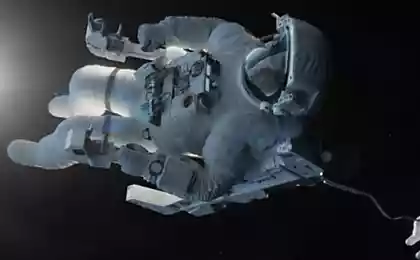788
Istoiya一伤
主要叙述前面的事件跑到我很可耻,但因为我住他们不会。回到家里,除了其他所有的烦恼,我发现我的嘴不完全关闭。当您尝试关闭的下巴有一个在左脸一阵剧痛。 “错位” - 听不见我告诉我的门牙。 “很明显”, - 证实的急性疼痛的面的左侧部分。当您尝试吃一碗汤是一个明确的必要急于急诊室或去婴儿食品和茶匙。后者并不吸引我,和我去伤害。
应该指出的是,多数市民是非常不负责任和粗心大意,但由于伤势很多人。如果一个人已经不用拐杖,然后坐下来对他来说根本不现实。其结果是,大约半小时我站在窗前和设想的睡猫。加,除其他事项外,有助于一些哥们做英语。你必须听我说出文章«的»。
最后,他闯入医生办公室,我感到非常惊讶:你见过扎波罗热哥萨克,外科医生?鲢鱼是失真的特点,并在演讲一些字母,甚至喜欢,熏肉和洋葱的气味。在衣架上一个丁字可以很容易地采取行动,当然是棋子,在特殊场合。很快就成了我的投诉和事故(我说我从楼梯上摔下)的详细信息,哥萨克开始谈论资本主义药相比,社会主义的缺点,说她妓女帝国主义和一切gorilka坏了。他说这十五分钟左右。老实说,我假装我不睡觉。然后医生狡黠斜视和狡黠的笑容问道:“好了,把梯子给的东西”。这样一种与杜利特尔博士博士vseponimayuschego类型MOWS。而我在它看起来像一个白痴,说我没打这么多梯子战斗。我觉得他很生气,甚至像一个掠夺性的外观拐杖。总之,他送我......到颌面外科医生诊断出颚破。
嗯,当然,我颤抖的地铁,嘴巴张开,下颌下提前给出。人们已经开始割,但随后转身离开,如果我只是看这个奇怪的公民。很显然,我看不好......唉,莫名其妙地达到了预期的车站,找到了医院,因此,外科医生。我坐下来,等着他在接待出于某种原因,沐浴套装,所以健康。他们是谁冲在整个医院的全貌?..外科医生,也被刮得干干净净,但没有刘海。并且仍然很暗,也许宿醉。很暗,他听了我的话,以及同样严峻,发送到X射线。接下来整个事件:我像一个疯子,跑遍在寻找免费的护士的医院,那么我们就已经与它运行了放射科医生,然后一名护士跑了从办公室的钥匙,回来说,它没有找到,然后放射科医生,傻傻的笑着,拉着他长袍的口袋里的钥匙。你应该已经看到了护士的脸......在X射线发现,我有一个覆牙合,但没有骨折,以及错位。医生建议我zamatyvat隔夜颌弹性绷带,但他的眼睛能读卷起在我脖子上的弹性绷带,去寻找酒精对修正案的健康一点点的愿望。所有回来的路上,我勇敢地试图关闭他的嘴,最后收。众议院透露,嘴里不再开放。随地吐痰可言,我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被告知,我有一个裂缝。虽然严重。当被问及他们如何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一个严重的骨折,他们拒绝回答,并要求到他们。此时,另一个医生显然第一静止被拉某处醇。今天,医生都怔怔的乐观,并说,我需要去给他们在医院里。上mesyatsok以上。我很乐观,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意。 “我们有专门的框架,你就会把头部和下巴,你将不能够动弹,因为它会愈合得很快”, - 医生说的话喜人。 “怎么我要去哪里?” - 我想。 “当颌面创伤食品灌肠” - 告诉我,来历不明的单调的声音。医生似乎没有听见。 “你到我们这里来,明天的小事情,我们会安排最好的方式......”, - 医生告诉我再见。
明天或任何公共医院后的第二天没有出现,当然我并没有后悔。一般用药有问题的科学。取而代之的是框架,我前往了当晚被包裹着绷带,并在2个星期去了。而且没有灌肠。
应该指出的是,多数市民是非常不负责任和粗心大意,但由于伤势很多人。如果一个人已经不用拐杖,然后坐下来对他来说根本不现实。其结果是,大约半小时我站在窗前和设想的睡猫。加,除其他事项外,有助于一些哥们做英语。你必须听我说出文章«的»。
最后,他闯入医生办公室,我感到非常惊讶:你见过扎波罗热哥萨克,外科医生?鲢鱼是失真的特点,并在演讲一些字母,甚至喜欢,熏肉和洋葱的气味。在衣架上一个丁字可以很容易地采取行动,当然是棋子,在特殊场合。很快就成了我的投诉和事故(我说我从楼梯上摔下)的详细信息,哥萨克开始谈论资本主义药相比,社会主义的缺点,说她妓女帝国主义和一切gorilka坏了。他说这十五分钟左右。老实说,我假装我不睡觉。然后医生狡黠斜视和狡黠的笑容问道:“好了,把梯子给的东西”。这样一种与杜利特尔博士博士vseponimayuschego类型MOWS。而我在它看起来像一个白痴,说我没打这么多梯子战斗。我觉得他很生气,甚至像一个掠夺性的外观拐杖。总之,他送我......到颌面外科医生诊断出颚破。
嗯,当然,我颤抖的地铁,嘴巴张开,下颌下提前给出。人们已经开始割,但随后转身离开,如果我只是看这个奇怪的公民。很显然,我看不好......唉,莫名其妙地达到了预期的车站,找到了医院,因此,外科医生。我坐下来,等着他在接待出于某种原因,沐浴套装,所以健康。他们是谁冲在整个医院的全貌?..外科医生,也被刮得干干净净,但没有刘海。并且仍然很暗,也许宿醉。很暗,他听了我的话,以及同样严峻,发送到X射线。接下来整个事件:我像一个疯子,跑遍在寻找免费的护士的医院,那么我们就已经与它运行了放射科医生,然后一名护士跑了从办公室的钥匙,回来说,它没有找到,然后放射科医生,傻傻的笑着,拉着他长袍的口袋里的钥匙。你应该已经看到了护士的脸......在X射线发现,我有一个覆牙合,但没有骨折,以及错位。医生建议我zamatyvat隔夜颌弹性绷带,但他的眼睛能读卷起在我脖子上的弹性绷带,去寻找酒精对修正案的健康一点点的愿望。所有回来的路上,我勇敢地试图关闭他的嘴,最后收。众议院透露,嘴里不再开放。随地吐痰可言,我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被告知,我有一个裂缝。虽然严重。当被问及他们如何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一个严重的骨折,他们拒绝回答,并要求到他们。此时,另一个医生显然第一静止被拉某处醇。今天,医生都怔怔的乐观,并说,我需要去给他们在医院里。上mesyatsok以上。我很乐观,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意。 “我们有专门的框架,你就会把头部和下巴,你将不能够动弹,因为它会愈合得很快”, - 医生说的话喜人。 “怎么我要去哪里?” - 我想。 “当颌面创伤食品灌肠” - 告诉我,来历不明的单调的声音。医生似乎没有听见。 “你到我们这里来,明天的小事情,我们会安排最好的方式......”, - 医生告诉我再见。
明天或任何公共医院后的第二天没有出现,当然我并没有后悔。一般用药有问题的科学。取而代之的是框架,我前往了当晚被包裹着绷带,并在2个星期去了。而且没有灌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