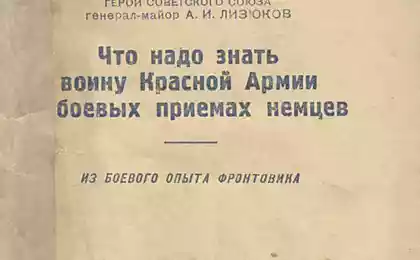1011
我们不再会

我的父亲在1991年12月去世,享年70岁心脏衰竭。在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去看看他在医院里,他急忙把他的手臂在我身边,用他的声音可怕的不确定性问:“儿子,我为什么要继续生活»
?
我抓住午睡问题,为此已上升突然他的一生,说实话,“我不知道。”而他不知道。因此,我认为,两天后他就死了。
他是第41次来到前从大学,被包围,然后去了游击队给他们打在布良斯克森林,接到命令的红星和许多奖牌。而在43日,他成为voenkorom,最近我发现它在互联网上的有趣“即将走到我们的”提取其中的“党派的道理。”而这个笔记,写更年轻颤抖的手,震撼了我为核心,以泪。
“在寒冷的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裹着破布,蜷缩在折磨的母亲的孩子。干,哭眼睛的女人看起来透过破窗在死者被肢解的街道。轻拍背部和饥饿的孩子们,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们重复了无数次:“很快会来我们»...»
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浮渣。有莫斯科之战,停止计划“巴巴罗萨”,以及库尔斯克,决定战争和许多重大战役的结局,但本质上仍然没有在其中。即使我们输了,并在莫斯科和库尔斯克,仍然赢了。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想法和感受的想法,写了我的爸爸。这篇文章是充满了,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 - 写在一口气,使一个民族立于不败之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发生了 - 我们来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是来自和爸爸的军用钞票不是瞎说的,纯粹的真理,它otlilos一些细胞,neubiennym乐观与它是无用的争辩。
信念在这些“我们”的代名词在他那个时代,苏联人民,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被世界资产阶级产生的,到最后是最坚实的在里面。当戈尔巴乔夫来到所有的动荡,我是先兴奋,然后失望,这是一本漫画封面他坚不可摧的信念说:“没事!我们站在附近的图拉!“而更多的我与他的反叛,没有他身后的胜利,认为和他在一起,更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种看不见的城市Kitezh的真的有...
但我到了岁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些坚实的Kitezh灵魂。唉,它是如此虚幻,那实际上是他的父亲,布尔什维克和关闭不比较。我意识到他就是我们的主要区别。他住的明天了一辈子的光线,它通过定义昨天是为他好。我,我们,现在谁住,越来越多的被吸引回到了过去。
已经加入了战争的共产党人,他叫陷入疯狂秘书长勃列日涅夫“brovenostsem”和“长臂猿”。但相信 - 我们的肤浅的复员,其中陆军说不可避免的,还是来了:“多他们改变了木乃伊,就更好了!我们是在路上!“他的生活的全部经验说,我们正在向一个更好的,并没有过激行为,像极河蜿蜒,它不能被撤销。为什么要弯来弯去,报以特有的幽默:“因为我们经历的未开发»
!
他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个偏远的村庄,甚至在村里,这是所谓Nepochetka的结束。作为一个孩子的世界对他来说最大的奇迹是给他犁地,“马”邻居的花园“fimichesky”铅笔。他活到加加林,彩电;第五轮他,卷起在莫斯科一个瘦小的钱包,把最优秀,而该国的大学 - 学院。 “这是 - 他说 - 民主,当一个农民的儿子有教育和该国在与部长的儿子相提并论任何职务的权利»
!
和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亲戚,在Boksane,纳尔奇克,格罗兹尼,在他开车送我曾经为一个对象的教训,表现出同样的增长。在仅仅一代人的周围被一盏煤油灯到e有所上涨;盖瓦屋顶材料的屋顶,而不是,那么石板和铁;购买“tevelizory”,“motsiklety”冰箱;开始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 那些谁最近一无所知更快的马车,没有人比农村牧师更重要。然后还有安雅与Nepochetki沃什卡Roslyakov儿子任教于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家大学!
当我的祖父向我的祖母不识字谁成为她的儿子在莫斯科,从她的感情摔在地板上的过剩,几乎没有抽。而我们的人已经从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是非常清楚的战斗在卫国战争中,他打了,我的父亲和祖父。只为“斯大林”谁也没有这样的非凡英雄主义不争的开始。
在斯大林的父亲敬佩既最伟大的天才,取得了全国很大,但在无辜受害者的成本。但他的无辜生命的村庄记忆饥饿和缺医少药的远远超过了所有的斯大林的镇压中丧生。他死了,因为这三个哥哥的。但他没有想到斯大林主义的回归,理解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伟大而悲壮,像每一个开端,一个点去一个更好的国家。他看向未来看作物的农民,耕,种血性水泡穿上它。
但这种收益的农民几乎没有了,zhrem主要来自国外的领域。而且看起来是矛盾没有离开国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过去。一些 - 在苏联,更加明显天堂他的球迷。其他的 - 皇家,第三 - 东正教陈旧,第四 - 在dopravoslavnoe甚至异教
。
而我,在耳边像任何振作未来滚灵魂在苏联前,这是更平等,博爱,以及音乐,文学,科学进步和成就激励个人不朽的爱的国家和信念。而在未来,除了腐烂的臃肿的肚子,我的生命,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的父亲是一样的,直到最后甚至一年零一个月他的生活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而且它肯定是最幸福的我的。
但是,在91年年底,结束一切,为他所居住的时辰已到了算总账的他最严重的生活。当面对前额叶利钦和突发事件委员会,他既不是一个也没有换另一侧。精确的人类的本能,以鲜活的生命,一旦他抓住了叶利钦,他的勇气我很钦佩起初 - 没有撒种,而不是一个建设者,和绝望的耗电驱逐舰
但是gekachepisty与他们的个人怯懦和相似与早先的“长臂猿” - 也为他“不是我们的。”而我们,谁根据他的信仰,他已经到了突破的关键,再也没有出来。他与所有可怕的真诚相信显然意识到,再也没有出来。
最卑鄙的话是“店主”,一直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结束。他喜欢普希金,柴可夫斯基,读津津有味教导莫诺马赫和他的祖国的其他病史。但是,我意识到,他战斗和生活的国家,为此,战斗,生活莫诺马赫,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及以上。作为店主的国家。但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他不喜欢。
然后,当俄罗斯开车像一些脏,高加索,我接到了父亲的90岁的老教师,从格罗兹尼,他此前曾派遣教孩子喷出的信。老人们不问,只是苦,所有我的父亲并不感到惊讶,并没有看到共享。我读了这封信 - 无论是从一些尼布楚环节,虽然老人回到了自己同样的热情斯塔夫罗波尔地区
但他是从国家,这是他建造与我的父亲驱逐出境。而且我认为还有我的父亲没能活着看到这丢人现眼!在此之前,使我们的人民,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再次发现自己在妇女在寒冷的房间,看起来透过破窗街道上的位置,该国 - 但没有什么不能告诉孩子们。既然我们不再来。
因此,我们pyatimsya癌症,回,请注意:我们的未来不亮,比我们能冷静下来最高的 - 不要去想它。一旦吃了他们的天然资源,那么我们和结束:没什么不收获future'm,该字段不耕,种,和工具递给自己Vtorchermet
。
但生活厌恶真空,如果我们不来我们的土地将不可避免地不是我们的。至于她都一样:谁是工作就可以了,撒种,她接受,并会生出
这些每年在本土多,他们的讲话zapolonyayut街上的陌生人 - 因为一旦德国乘客。但这个新的陌生人我不恶 - 他们是征服者,但和平,奴役我们的邪恶计划“巴巴罗萨”,而是由圣工
。
相反,我很珍惜他们更尊重濒临敬佩:他们如何管理定居在外国的土地,其所有的不友好的原住民和警察。但仍然难逃他们的感觉 - 我的父亲和祖父被击退了入侵者一样东西的时候 - 我不能
是的,我的祖先的幸福 - 不希望看到这一切的不幸,bessmyslyaschey他们的信仰,牺牲和努力。但你不必一定要收集我的后代失去了他们的背包在地上呢?
版权所有©«亚历山大Roslya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