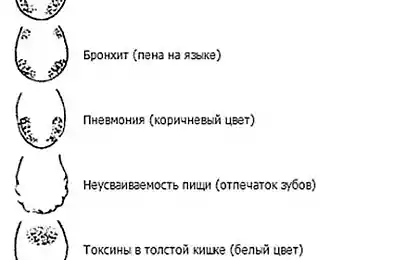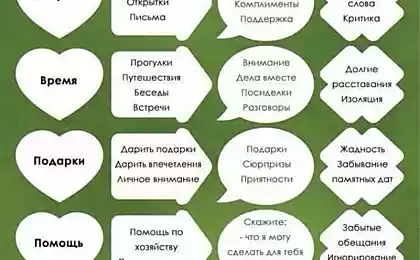828
心理学家 丽拉 博罗季茨基:学习一种语言将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
 (英语).
(英语).“学习一种语言将有助于理解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心理学家 莱拉·博罗季茨基(英语:Lera Boroditsky)讲述了语言如何塑造思考语言,显著影响人类世界的画面. 它界定了人类知识的这些根本基础,如关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思想. 心理学教授莱拉·博罗季茨基(英语:Lera Boroditsky)撰写的一篇关于亚马逊印第安人如何在没有数字的情况下,犹太儿童为什么在芬兰儿童之前就意识到他们的性特征,以及中国语言的特征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数学能力的文章.
安东·戈尔布诺夫
莱拉·博罗季茨基是斯坦福大学认知心理学助理教授,也是"文化心理学中的前沿"主编. 她的团队对现实的心理反射问题和语言对认知过程的影响进行研究.
我和一个来自波姆普劳的5岁女孩说话,这个小土著地区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半岛西端. 如果我要求她指向北方,她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正如我的指南针所示,绝对如此。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里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获得了科学成就奖和奖章. 我请他们闭上眼睛,以免看到邻居的行为,我建议他们指向北方。 许多人立即拒绝,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其他人则会思考一段时间,然后指出所有可能的方向。 我在哈佛,普林斯顿,莫斯科,伦敦和北京重复了这个实验,结果总是一样.
不可否认的影响
因此,一个来自特定文化的5岁女孩可以轻松地做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大科学家不能做的事情. 其中一个认知能力存在如此显著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令人惊讶的是,原因可能是沟通语言的不同. 语言特征可以影响认知功能的观点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表达出来. 从1930年代开始,他们在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和本杰明·李·沃夫的作品中得到确认. 他们研究了语言之间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不同语言的演讲者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观点最初得到了极大的热情,但不幸的是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支持. 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科学家对萨皮尔-沃夫假说变得幻灭,它被思想和言论的普遍性理论所取代.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事实材料终于出现,证明了在语言特殊性的影响下思想的形成. 这些事实驳斥了思想普遍性的既定范式,并在对现实的思考和想法的起源领域开辟了新的迷人的视角. 此外,调查结果可能具有重要的法律、政治和教学影响。
世界上有超过七千种语言,每种语言都需要特殊的语音转换. 假设我要报告42街上见过凡雅叔叔 对话者会知道我昨天才看过这部电影, 相比之下,在印度尼西亚语中,动词的构造甚至连我是否看过或只是要看看都不清楚. 在俄语中,我的性别会从动词中变得清晰,在普通话中,我必须澄清我们是在谈论父系还是母系的叔叔,还是在谈论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每个案件都使用不同的名词. 而用皮拉哈语(居住在亚马逊河支流之一的小部落说),我甚至不能说"42街"——里面没有数字,只有"小"和"很多"的概念.
在塔约尔语(英语:Kuk Tayore)中,没有"左"和"右"这样的空间概念. 相反,它们使用绝对方向的命名——北、南、东和西。 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无穷无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语言的演讲者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能否说,米安语、印度尼西亚语、俄语、普通话或皮拉哈语使用者最终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回顾和推理? 根据在我的实验室和其他几个实验室获得的数据,我们可以假定语言确实影响人类知识的根本基础,如关于空间,时间,因果关系和与其他人的关系等思想.
复次波罗蜜. 在塔约尔语(英语:Kuk Tayore)中,这个地区所讲的是"左"和"右"等空间概念. 相反,它们使用绝对方向的命名——北、南、东和西。 当然,英文中也使用这种概念,但只是为了说明全球方向。 例如,我们永远不会说“生菜叉被放在餐厅的东南!” 相对而言,在塔奥雷,所有空间尺度都使用绝对方向:例如,“杯子位于板块东南”或“玛丽以南的男孩是我的兄弟”。 因此,为了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你需要不断地在太空航行.
过去20年荷兰尼梅根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斯蒂芬·莱文森(Stephen C. Levinso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约翰·B·哈维兰(John B. Haviland)的开创性工作数据显示,使用绝对方向命名的语言在空间,包括不熟悉的地形或建筑方面,语言的讲法非常有方向性. 他们比说普通语言的普通居民做得更好;此外,他们的能力超出了现代科学思想的范围. 显然,这种惊人的机会是在语言特点的影响下形成的。
空间感知的特征意味着时间感知的特征。 特别是,我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同事Alice Gaby(爱丽丝·加比)和我向Tayor插图的演讲者介绍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不同事件——一个正在成长的男人,一个正在成长的鳄鱼,吃了香蕉。 混合照片后,我们要求主体按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
每位参与者两次执行该程序,位置不同。 讲英语的人用希伯来语从左到右以及从右到左散发卡片:因此,写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对时间组织的看法。 在塔约尔语演说者的情况中,画面不同:他们从东向西放牌.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正对着南面,牌从左到右分散;从北到右到左;从东到东,从自己.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主题,主要方向是如何方向的: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且自发地利用空间方向形成一个时间结构。
不同文化间对时间的看法也存在其他差异。 英语中说,未来是未来的,过去是落后的。 2010年,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研究员林登·迈尔斯和他的合作者发现,英语演讲者在思考未来时低头向前倾斜,在思考过去时向后倾斜. 然而,在安第斯人所说的艾马拉语中,未来是落后的,未来是落后的。 相应的,他们的姿态也有所不同:200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拉斐尔·努内斯,圣迭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娃·斯威瑟(Eva Sweetser)表示,艾马拉的演讲者在提及过去时会向前倾斜,向后倾斜.
皆以己法忆念.
不同语言的土著演说者对事件的描述不同,因此,他们对参与者角色的记忆也不同. 每个事件,即使是最短暂的,都是复杂的逻辑结构,不仅需要准确的重建,还需要解释. 例如,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打猎时不小心打伤了朋友哈利·惠廷顿(Harry Whittington)的著名故事. 历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描述. 比如说 "Cheney伤害了惠廷顿" 这直接指向Cheney的罪魁祸首 另一种说法是,“Wittington被Cheney打伤”,就是让Cheney远离事件。 你可以把切尼留在幕后 通过写惠廷顿Get Shot。 切尼本人也这么说: "当然,我是开枪扳机的人,开枪打伤了哈利",从而把自己和事故分割成一连串事件. 而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他听到翅膀的声音,转过身来,开枪,看见他的朋友受伤,”一句话把Cheney从事故的肇事者变成了一个证人。
机构被语言学家解释为一种语言构造的财产,其中一个人看起来不是行动的对象,而是物体. 简言之,一个人描述的情况似乎与他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事件受到他无法控制的情况的影响。
这种口头伎俩很少对美国人产生影响,因为在英语国家中,儿童和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逃避责任,非侵略性建筑听起来像是明显回避的东西. 说英语的人倾向于直接表示一个人在某一事件中的作用的短语,如 " 约翰打破了花瓶 " 。 相反,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经常使用"瓦塞断裂"(西班牙语:Se rompiu el florero)类型的非代理建筑,其中没有直接提及事件的肇事者.
我的学生凯特琳·M·福西(Caitlin M. Fausey)和我发现,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可以引起事件重播和目击者记忆的分歧. 在我们于2010年发表的研究中,英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发言者被放映了两个人打气球、打碎鸡蛋和溢出液体的录像——有时是无意的,有时是故意的。 然后,要求他们记得是谁对事件负责,例如指认嫌疑人。 就语言而言,结果是可预测的。 所有三种语言的演讲者都描述了使用"他刺穿了球"等代理构造的故意事件,并同样清楚地记得肇事者. 然而,意外事件的记忆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与说英语的人相比,说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与会者不太可能使用代理结构来描述事件,也不太可能记得他们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总的来说,他们的记忆能力并不逊色 — — 蓄意事件,当然,在描述中,罪犯是记得的,也是讲英语的人。
在希伯来语中,性别的称谓极为常见(即使“你”一词因不同而不同),芬兰语的使用频率要低得多,英语在这方面占据中间位置. 结果,在讲希伯来语的儿童中长大的儿童比讲芬兰语的儿童早一年认识到他们的性别。 语言不仅影响记忆,也影响学习. 在许多语言中,数字的结构比英语更明确地对应十进制(例如,在中文中,对十一和十二的"十二"没有例外,其中在数字表示单位中加入的一般规则是"十"的基础,类似于俄罗斯的"十"),他们的载体迅速掌握了这个帐户. 数字中的音节数影响记忆一个电话号码或脑中计数. 即使认识性别的年龄也取决于语言的特征. 1983年,安阿尔伯密歇根大学研究员亚历山德雷·吉奥拉(Alexandre Guiora)比较了母语为希伯来语,英语和芬兰语的三组儿童. 在希伯来语中,性别的称谓极为常见(即使“你”一词因不同而不同),芬兰语的使用频率要低得多,英语在这方面占据中间位置. 结果在希伯来语使用者中长大的孩子比芬兰语使用者提前一年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英语使用者的孩子采取了一定的中间立场.
什么影响什么?
我仅举几个不同语言的发言者在认知功能上存在差异的显著例子。 自然,问题就出现了 — — 语言的特点会影响思维还是反之? 显然,两者都是真实的:我们的语言取决于我们的想法,但也有相反的效果. 在过去十年中,一些有才智的研究表明,语言无疑在塑造思想中发挥作用. 事实证明,改变语言的构成会影响认知功能. 因此,为颜色学新词会影响阴影的差异,为时间学词会影响对时间的认知.
研究语言对思维的影响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流利的两种语言的人. 事实证明,对现实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人目前所说的语言决定的。 2010年发表的两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像和不喜欢这样的基本特征也可能受到影响.
一项研究由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奥卢达米尼·奥贡内克及其同事进行,另一项研究由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谢伊·但泽尔团队进行. 这两项研究都研究了双语科目的潜意识偏好——摩洛哥讲阿拉伯语和法语,美国讲西班牙语和英语,以色列讲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 特别是,后者提出针对不同词的表述迅速按键. 在一个案例中,当提出犹太名字(如“Yair”)或正面属性(如“好”或“强”)时,主体必须按“M”键,当提出阿拉伯名字(如“Ahmed”)或负面属性(如“坏”或“弱”),“X”键。 然后,条件发生了变化,一个钥匙与犹太名字和负面品质相对应,另一个钥匙与阿拉伯名字和积极品质相对应。 在所有情况下,都测量了反应时间。 这种方法被广泛用于评估潜意识偏好,特别是种族与正或负特征之间的关联.
例如,在中文中,11人无例外,其载体更快掌握比分. 令科学家惊讶的是,同一个人的隐秘偏好因所使用的语言而大不相同. 特别是在上述研究中,在使用希伯来语时,对犹太名字的潜意识态度比使用阿拉伯语时更为积极. 显然,语言对精神功能的影响比通常设想的多得多。 一个人即使在执行诸如区分颜色,计算屏幕上的点数或指向小房间等简单任务时也会使用语音. 我的同事和我发现,如果我们干涉言论自由的使用(例如,要求主体不断重复报纸节选),这些任务就中断了. 这表明不同语言的特征可以影响我们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 我们所说的思维是一套复杂的语音和非语音功能,可能没有太多的思维过程不受语言的影响.
人类思维最重要的特征是可塑性:当现实发生改变时迅速重建现实思想的能力. 这种可塑性的表现之一是人类语言的多样性. 每个都以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为特征,每个工具都基于这种文化中数千年来积累的知识和思想. 语言是理解、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祖先创造和培养的与环境互动的宝贵指南。 研究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我们如何形成关于现实及其规律的知识,达到新的知识高度——换句话说,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本质。
P. S. 记住,只要改变你的意识,我们一起改变世界!
资料来源:理论和实践.ru/posts/5662-izuchenie-yazyka-pomozhet-ponyat-chto-delaet-na-lyudmi-psikholog-lera-boroditski-o-tom-kak-yazyk-formiruet-myshle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