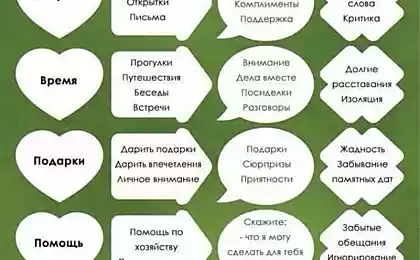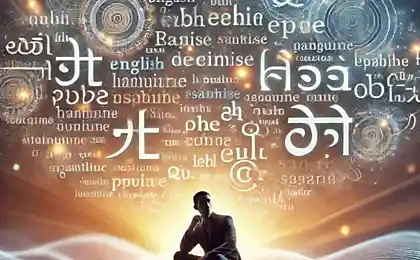1452
由于英语已经成为不正常

撰稿语言学家约翰·Makuorter(约翰·麦克沃特)
不,英语是不是唯一的明亮,功能强大,适应性强。但他,其实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其他一些语言更加诡异。
母语为英语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语言。他们知道它和它不是原生的人,这是教。那奇怪了,我们也看到与拼写相关的,而且,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噩梦。当它在英国没有拼写比赛没有发言的国家。在正常的语言拼写,至少假装是基本符合的与人发音的单词的方式存在。然而,英语是不正常的。
拼写是由于,当然,与写,而语言是,事实上,必须与讲话。它起源长信之前,我们说的要多得多,大约几十万世界口语很少或根本没有写百。但是,即使在他的英语口语很奇怪。他的古怪可以很容易地没有注意到,因为美国和英国的英语为母语的居民不是特别热衷于学习其他语言。
然而,我们的单语趋势使我们看起来就像众所周知的鱼,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湿”。我们的语言被认为是正常的唯一直到时间作为人没有得到的是什么,事实上,正常的语言的想法。
还有就是,例如,不同的语言,这将是足够接近英国在这个意义上一半的人说,这将是可以理解,从未从事过它,和其他一切人会学习,把举手之劳。也可以这样说,德国和荷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对泰国和老挝的。最接近讲英语的人可能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北欧语言叫做弗里斯兰:如果你知道tsiis - 这种奶酪和里,frysk意思是“弗里斯兰”,我们不难想象,是什么意思:布雷亚,bûter,EN griene tsiis是GOED Ingelsk EN GOED里,frysk。但是,这句话是人为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倾向于认为弗里斯兰语更像德国,对应于现实。
我们相信缺点是,在许多欧洲语言,没有任何理由的名词是由于性别,而法国月亮原来的女性,以及船 - 雄等。但是,事实上,国家是我们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属于一个家庭 - 印欧语系,而只是其中之一,在英国有性别没有这样的分类
大律师抽烟的中央刑事法院在伦敦的面前。美联社照片,阿拉斯泰尔·格兰特
希望陌生感更多的例子?好吧。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语言,现在需要一种特殊的端仅在第三人称单数。在这种语言,我写了这么:我说话,你说话时,他/她说话-S - 但为什么。在目前的紧张在正常语言或动词没有所有的结局,还是有一堆不同的结局(西班牙语:hablo,hablas,habla)。并调用你需要插入字拒绝做某件事,或者问一个问题另一种语言。你觉得难吗?除非你是不是最初来自威尔士,而不是从爱尔兰并没有出生在法国北部,它很可能是事情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的舌头这么奇怪?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什么样的语言,为什么它已成为呀?
英语,其实,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古英语不是那么类似现代版什么需要相当大的努力,以考虑同日而语的。 Hwæt,我们嘉丁在geardagumþeodcyningaþrymgefrunon - 这是真正的意思是:“我们的国王在丹麦的时候它是关于国王的荣耀听说过”?今天的冰岛人可以读这样的故事写在老扎前兆他们的语言1000年前,和,不过,对未经训练的眼睛诗“贝奥武夫»(武夫)似乎是写在土耳其的工作。
已经从原来的语言中删除我们的第一件事,如下:当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和头饰)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在英国,住在岛上的其他人说另一种语言。这是凯尔特语,而现在出现与威尔士,爱尔兰,并在频道在法国的另一面,甚至布列塔尼。凯尔特人被奴役,但活了下来,因为所有的大约25万德国侵略者 - 城市作为一个不起眼的泽西市的大致的人口 - 很快事实证明,大多数谁讲古英语的人,开始使凯尔特人
关键的事实是,他们的语言是英语有很大不同。例如,动词是在他们的第一。而凯尔特人是奇怪的构造与动词做的事:他们用它来制定一个问题,作出要约的负面 - 甚至创造了一种添加到动词:你走?我不走。我不走。现在,它看起来很熟悉,因为凯尔特人开始这样做,他们自己的版本的英语。然而,这样的建议前,会是十分奇怪的英语为母语的人 - 像今天它会看起来很奇怪的比我们自己的生存和凯尔特人之外的任何语言。请注意,这个奇怪的动词的十分讨论做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 因为如果你说,你的嘴总是语言
迄今为止,世界上其他语言,除了凯尔特人和英语的存在,其中的动词是用来做相同的。因此,英语的陌生感开始与改造人的嘴,越来越习惯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继续聊他们一样,我们做的方式,我们自己就不会浮现在脑海中。计数当你说«eeny,meeny,MINY,教育部»,你有没有过,我们所谈论的一些账户的感觉?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 凯尔特人的数字,它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回去用英国的村民们的话时,他们计算的动物,或玩游戏。但是,儿童歌曲的话:«山核桃,dickory,码头» - 所有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这里的解决方案:字hovera,dovera,迪克在同一个凯尔特语是指八,九和十个
。
然后另外一个事件发生,影响岛上的英语,越过来自大陆,出现了大量的人谁是德语的运营商和谁曾非常严重。这个过程开始于九世纪,而这一次的入侵者讲了话在德语的另一分支 - 在老扎。但是,他们并没有强加给他们的语言。相反,他们结婚了当地妇女和过渡到使用英语。然而,这些都是大人,大人平时不容易学习新的语言,特别是当我们在谈论一个社会里使用的口头语言。
有没有学校,没有大众媒体。学习一门语言那么意味着有必要认真倾听,并把巨大的精力去了解。我们只能想象我们是多么地说德语,如果有只所以要教他 - 那就是,与他在录制的视频会议,深入了解他的板(屠宰的动物,与人交往等),而不是仅仅工作在我们的发音。
虽然征服者能够报告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确定的。的弗里斯兰提供的只是和表演的降低清晰度 - 但是,这可以用一个很粗糙的版本的语言来完成。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做什么预期,他们谈到古英语很差。他们的孩子都听到很多不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古英语。生命的流逝,很快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美英语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北欧做过英语更容易
。
在这里,我必须作出澄清。在语言界冒险谈论的是,有些语言比另一种“更好”,因为测量由作出客观的评价没有统一的制度。但是,即使有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光带,我们不会说,没有在上午10点和生活之间的区别的生活在晚上10点。也可以这样说,关于语言 - 其中一些听起来更花俏比别人好。如果有人说,他被赋予了一年学习无论是俄罗斯或希伯来语,然后他就已经开始拔出钉子每做一个三分钟的测试过程中的错误,检查自己的知识,只有一个被虐待狂会选择俄语 - 除非正是在这个时候不再受一些相关的语言所拥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英语中的“更好”比其他日耳曼语言,所有的维京人。
在古英语中有一种疯狂的类别,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很好的欧洲语言 - 但北欧人特别注意他们没交,所以现在他们还没有。注意这个奇怪的英语。此外,维京人已经学会了曾经美丽的前共轭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在第三人称单数,且有一个孤独的结局-s,现在它被卡在那里就像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死的昆虫。在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维京人平滑的复合材料。
他们也跟着凯尔特人的例子,改变语言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自然的。非常清楚,他们已经增加了数千名新词在英语中,包括那些在我们看来其实完全“我们”:唱的一首老歌«获取快乐» - 在标题的话向我们走来,从挪威的语言。看起来,有时候他们会离开的语言指令“我们在这里了,”因此,补充了我们的母语文字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等同物。这样一来,有话堤的复印件(他们)和沟(与我们),散(他们),和粉碎(我们)和船舶(他们)和队长(在老扎跳过意味着船,所以队长 - 托运人)
。
然而,上面的字只是刚刚开始。他们留在英语语法自己的印记。幸运的是,现在学校的老师很少说,这是错误的说法哪一个城镇,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来自哪个城市)。我们谈论的是使终端到终端,而不是一个借口,开始WH字后,立即把它。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就会响起这样的:“你的城市你来»(从哪个镇,你来了?)英文句子?”不同的借口“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并且不会导致伤害任何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有关利湿鱼:在正常的语言介词不是孤立的,也不挂在句末。西班牙本土注:这句话萨尔瓦多老兄QUIEN哟lleguéCON(男人,我想出了),是一样自然穿裤子里面翻出来
。
不时有些语言让你做这样的事情 - 在一个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在墨西哥土著语言,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是在利比里亚的语言。有的则没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东西被视为奇怪。但你可知道,同样的事情被允许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现代的丹麦保存?
我们可以显示在一个句子中的示例中,所有这些奇怪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说出下面这句话:这就是你走在与该男子(这里就是你进来一个人)。令人奇怪的是,因为1)定冠词没有具体的形式是阳刚之气,以符合这个词的人(人); 2)动词的步行路程(步行),没有终点,以及3)你不说«在与你走路»。所有这些古怪造成的事实,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很好的旧的英语一样。

伦敦卫兵换岗皇家骑兵卫队。 ©美联社照片,阿拉斯泰尔·格兰特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 在英语中,无论从消防水带,连接字流在一些其他语言。经过斯堪的纳维亚来到了法国。诺曼 - 同维京人的后裔被证明是 - 征服英格兰,它统治了几百年,而此时英又增加了10000新词。然后,从十六世纪起,受过教育的英语为母语的人开始培养英语作为成熟的作家的手艺的工具,因此它已成为时尚,以使语言更高尚的性格源自拉丁语借词。
由于从法语和拉丁语新词的涌入(往往难以确定的特定词的原始源)在英语中是这样的话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基本(基本),高清(确定)和结论(结论)。这些话如今被认为是英文的,但是当他们是新的,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在十六世纪(及以下)认为这些烦人的自命不凡和侵入,那就是如何他们会欣赏那句“烦人的自命不凡和突兀»(不快自命不凡和侵入)。
想想法国学究现在折叠他们的鼻子,用流动渗透到他们的语言的英语单词碰撞。有人甚至那些谁愿意替换原始的英文单词夸夸其谈拉丁借用作家,这是很难不后悔过其中的一些损失。而不是钉在十字架上,根本的,定义和结论,我们可以交叉,groundwrought,saywhat和endsay < BR />
然而,语言往往会做什么,我们从他身上想。但模具已经投:英语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新词,开始与英语单词的竞争来描述同样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有三胞胎,这使我们能够表达的想法,有不同程度的形式化。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词“帮助»:帮助 - 这是一个英文单词,援助 - 法国血统一句话,协助 - 拉丁文。这同样适用于“字王室»:王道 - 英文单词,皇家 - 法国血统一句话,富豪 - 拉丁文。请注意这句话钢筋的字的每个新版本的重要性王道听起来几乎嘲讽,富豪 - 在同一条直线,像一个宝座,而这个词王室是在中间的某个地方 - 一个体面的,但不排除错误的君主。
再有双胞胎 - 他们比三胞胎那么显着,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是滑稽。我们都在谈论这样的英法的夫妻,为的是与词的情况下“开始»:开始和展开,以及与这个词愿望:希望和愿望。应当指出尤其是烹饪转型:我们杀了一头牛(牛)或猪(猪) - 这是一个英文单词 - 让牛(牛)或猪肉(五花肉) - 法语单词。这究竟是为什么?大概主要是因为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讲英语的工作人员在屠宰场工作过,并担任如此丰富的法语和盛宴。不同的方法来指代肉依赖于人的地方对事物的现有系统,以及阶级差别回落,我们在非侵入性的形式。
然而告诫讲师(纬度让慧眼识英雄 - 大约Perevi)英语的传统解释往往夸大我们的演讲正式进口水平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一旦他们这样做享用丰盛的英语。正是这种观点是由罗伯特·麦克雷(罗伯特·麦克拉姆),威廉·KREN(威廉·克兰)和罗伯特·麦克尼尔(罗伯特·麦克尼尔)在他的著作“英语»(英语的故事,1986)历史召开。据他们介绍,拉丁单词的第一个大的借款成本已让人们在古英语发言,表达抽象的概念。
然而,没有人在数量上定义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的(谁是这些人,各阶层人民的发展,这可能表明缺乏抽象思维,甚至没有表达出来的能力?)。此外,这样的语言是不知道的地方指同一概念,只有一个字。在语言,是人类思想,太多的细微差别 - 甚至是不确定性 - 以使他们能够保持这样的基本。我没有一个书面的语言有正规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