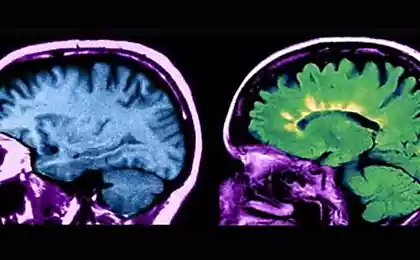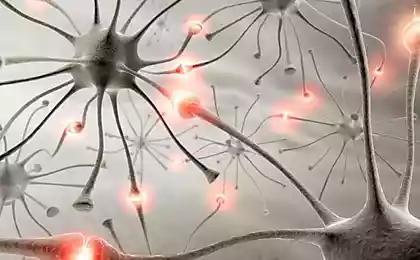610
愈多发性硬化:个人经验。第1部分
开始的故事。
迟早的人开始要求永恒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生活吗? 因为我活着,而唯一真正办法,我花费的时间分配我在地球上? 如果我很高兴吗?
闪烁在繁忙的办事处之间的灯光大城市,走在了人行道主,感觉在钱包或乳腺他的夹克口袋月薪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2August2001.

我躺在沙发上在他的莫斯科的公寓和为什么我没有别的生活。 一个奇怪的软弱、绝望和缺乏任何愿望。 一个绝望的沉闷和灰色。 无论我是,在运输,在度假时,在晚上,天早上,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样的生活?"
这就是她所能够提供我吗?
常沮丧和饱我的同伴中的23年。
我记得很清楚的时间。 我有一个"完美"的薪金对于我的年龄和职业的、适合于她的"休闲的"。 通过教育我是个营销人员。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营销,也许比大多数。 品牌管理、创建者、管理顾问。 我已经知道了一定数量的工具的操作,知道如何形成的思维过程在人们心目中的谁知道他们的反应能力,刺激,你知道的梦想的人们睡着了,并感到他们的梦想明天...梦想的群众是可预见和公式化的,它们取决于我这样的人。
两周前,我嫁给了一个心爱的人。
在过去两周我们要去度蜜月到希腊并得到了很多积极的情绪。
我年轻、漂亮的、成功的,我所有的梦想,那个搅拌的想象力,在青春期到达,那么我什么感觉? 幸福吗?
也许幸福是在个人生活变成了一个熟悉的背景的感觉的一些丰满。 但同时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伤,并希望死亡。 我看见我未来的生活一目了然,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场景,对这个最美好未来的生活我懒得连一根手指。 我受到威胁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而我走到其开始。
来全副武装的最大数量的分,明天所有应转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两年,我将有一个单独的科比片在莫斯科,在不良于3-4年,然后我就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上周末,我们将一起去购物和每年一次在海岸上,我会收集他们在一个花园,襁褓,购买玩具和书籍与刺猬和兔子、涂抹zelenkoj成的膝盖,检查家庭作业。
脂肪,新衣服、"一个成功的事业"、私人汽车,跟朋友和obsasyvanie空闲闲话,也许是情人。 并没有什么更多。
我吓坏了这个前景。 我23岁。 我有一套完整的意外废料的浪漫幻想和复合物的青少年时期,固图书馆阅读,极多特有的年龄,以及一个关键要看的东西。
外面,天倾向于傍晚和太阳到地平线上。
沙沙作响的其陈旧和树叶尘土飞扬的疲倦的老头八月,我躺在沙发上花费的分析已经通过并仍然有生活、感觉一个累。
我闭上我的眼睛和听到的内部黑暗的空虚,安静,没有情感,因为如果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说:
—我不想活了。
八月15,2001年。
我去办公室,到我左边的代表空棕色书桌上摆着一厚厚的书,铭记在脊柱上"等等等等等等神经病",显然旨在灌输信心在患者的尊严和教育的医生。
在这里,他是。 鉴24日至27年。 我的年龄。 以及所有我现在将开始愈合,感到悲观,我认为我自己,注意到桌上的任何特性的内在我的意见"主管医生",但是几笔,而臭名昭着锤子。
—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似乎是尴尬的年轻人,显然在我的监督。 它必须是他第一天工作时,我决定无可奈何,坐在一张椅子,并告诉关于他的灾难。
—脱衣服,被迫满不在乎的调中断的流我的想法,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并采取一座在沙发上。
—怎么带? –我感到惊讶。
—你有没有从来没有看神经科医生吗? 可以保持你的内衣上,他补充说,...找回来。
然后检查,在这期间我刺针,殴打一个锤子在膝盖上,触摸的测试管的热水和冷水的皮肤的手和脚。
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从来没有看神经科医生,一定要获得很多新的感觉。 博士有趣聊天花40分钟的我的考试...
—最有可能的,一个捏脊椎骨乐观,宣布医生,描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必要的考试。
—走路一两周内获得按摩一切顺利,但要确保这种审查,它被称为MRI(磁共振成像)坚持对医生,交给我的方向。 我们需要消除所有其他的选择。
再见丹尼斯笑着,我完全放心和迷住了新朋友。 感觉到我所要说的是不重要的是,一周之前检查我没有灵敏性皮肤上的脚。 没什么,当然,生活并没有停止,但的感觉是不愉快的。
我乐观地开始去按摩,并且它似乎第三届会议开始了解受虐狂,在经历高兴地从痛苦。
17August2001.
坐在等待室。 在队列中的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坐在旁边一个的女人跟一个男人,大约五十、贫在一些灰色的,灰色的未清洗的头发一个包子,她单调重复相同的短语,"恐怕我"时,它就像一个连续的嚎叫"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 abuseabuse的..."。 她拥有权利的手在他的左边,来回摆动,因为如果抱着通过一个小的孩子。
她旁边坐着一个累了被殴打的人在一个皱巴巴的棕色的西装,有的裤子都清楚地短的最好的长看起来是黑色一半桅杆的袜子和尘土飞扬的鞋子。 他的脸皱巴巴的诉讼。 显而易见的是,他遭受的痛苦坐下来一个人,这种持续不断的单一分钟的面粉和同情的斗争与疲劳和不适。 有时候他有气无力地试图中断她喜欢的软,某种安慰的话,那么该妇女在灰色冲进歇斯底里的话,"他们会带走我的手,这是癌症,他们将会带走我的手,就像我没有手"和呜咽中...然后他们出去和她再次返回到他的塞克斯顿"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虐待...".
我坐在旁边给他们一个白色皮沙发,因此,她棕色的裙下摆我的衣服。
我们周围的去清理医生戴的帽子和鞋套、无菌的植物生产的一些高纯度的铝。 看看我的眼角的老夫妇和近身体上感觉到动物恐怖的一个人谁是要"采取臂"。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我自己的眼睛。
我毫无准备的,不知道如何作出反应。 疯狂地想了解存在这种休闲妇女不可以。 我的想象力和大脑拒绝以试试皮肤上的一个猎人。 它闻起来太可怕了,粘灰色的恐惧、痛苦、失望和痛苦。 "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 busabusss的..."。
怎么长这种酷刑的?
突然从后面的门进来的女人的医生。 与一个混合的厌恶和可惜看来,在老年妇女,读她的方向,并说他们需要转到另一个房间。 男人匆忙捡起来,找医生在眼睛,然后东西滴下,拿起他的妻子,并导致出口。
女医生,请和具有明显的救济,看着我,采取的方向,快速读和导致进入一个房间里有白色的长方形单元提供关闭,锁定了我的手机,包和衣服的安全。 习惯性的运动使我长的、紧张的管MRI,锁的脖子和肩膀上。
记得白色的光滑的塑料的上限,并听取了刺耳的声音的振的,因为如果困扰着一些巨大的电子网络的史前动物。
我很害怕。
关闭空间和阶段,不出来的头部。 "Busabusss..."戒指在我的耳朵。
我觉得一分钟,我将复盖一个波动的恐慌。 闭上眼睛,试着冷静你的呼吸,想象一下,一个偏僻的小屋高在山区,长满了青苔的、黄色的草地上,美化,添加在画面上的雨滴的分支机构和太阳。
几乎平静下来。
最后这一切结束。 我滚出的管,我要除去的塑料保持领。 微笑着淡淡的,试图对眼睛的医生读的诊断。
她回答说,支吾感兴趣的名称和地方的工作,我的医生,初步的诊断和完成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有没有被诊断患有MS?
我的回答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母的组合,从她,不会,我没有。 她看着我难以置信,再次感兴趣的症状,然后摇他的头部和滴:
等待。 一旦结果已经准备好,会打电话给你。 我再次落在同一张沙发的。 一段时间后,有来自另一个科比片。 她看起来心不在焉地周围,并询问是否有与我的家庭。
已经认识到这狗屎打击了风扇,我看着她的眼微笑着问
—没有,什么?
她叹息,隐藏她的眼睛,并请你进入办公室。
内阁是更喜欢一个任务控制中心,在阴影里神秘的pomigivayut一些蓝色的灯泡,并按钮。 房间里有几台电脑后面他们坐四个白色,像个机器人烦恼的。
女医生邀请我去接近表,去洗手。
也许她有一个病干净的手,记得她厌恶看到的老人,我想。
过来这里,并邀请第二位医生和我的方法照亮玻璃墙上挂图片的我的内脏。
我不认为许多人不得不看到你的大脑和脊柱方面:)应该注意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
医生开始,一个沉闷的声音,以决定一个描述的我的照片pechatalsya学生的实习生...多个病变的白色物质的大脑局部的水平。径...囊肿...分区...在同一时间像在演讲厅,我和我的实习生展示所有这一切都在照片我的名字在角落里。
受训人惊讶的是,和狂躁仔细地看着我,作为一个生活津贴。 我在这个时刻,正在奇怪的边界条件,如果它是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我的睡眠。 我看到了整个现场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我们自己,如三维投影、固定中心的所有细节发生了什么事、声音、气味的空气流动和白色的懒汉坐在旁边一个的女孩。
最后仔细清单和记录所有的独特特征,而事实证明,我漂亮的花了的蛾大脑她沉默的每个人都看着我。 我觉得更多一点,从我的眼睛泼的眼泪。 停止。
微笑着,慢慢说:
—所以...现在告诉我人类的语言,这意味着什么吗?
让你解释这个通过你的医生,我不能给你一个诊断,她说,有些挑衅,如果在自卫。
—不过,你有私人的想法? 分享。
—最可能的是,它是多发性硬化症—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逐步残疾并最终死亡的患者。
–不可治愈的疾病,她说,严重后暂停。
—也就是说,这是什么? 不治疗? 可以在国外?
在这个阶段的发展现代医学的有效的药物可以极大地改变病人的位置在这种疾病,没有找到。
但是你不用担心,你是非常幸运的是,你已经发现了该疾病的早期阶段,说谢谢你的医生,而且,现在有许多方法可以延长一个全人类的生存在这个疾病,...
—一些患者甚至居住的10-15年来的热情的一个学生增加了实习生从房间的角落里.
医生看起来不以为然。 我已经不要听他们的...转动的图片,并离开办公室...听到的轨道。
—你很幸运...10年前你绝不会有一个机会,现在,科学正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步伐...
哦,幸运的男人—我听到我的头,我自己的声音。
地铁并且继续处于休克状态,虽然我的眼睛都是干想法,围绕在我的头令人震惊的速度,然后冻结在发呆,同时,我继续以惊人的清晰度捕获、周围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在我的前面,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女孩。 看起来大约18,大大的蓝眼睛、光线长长的棕色卷发现头发,哈巴狗鼻子的雀斑,在她的手持一束矢和无法哄停哭泣...滚滚的泪水从她的眼睛。 年轻人的微笑和一些东西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以某种方式安慰她。
抑郁症。
我随后对话的有丹尼斯,被中断时与我的眼泪和鼻涕,因为我非常熟悉互联网,并参加到已经收集信息有关这个神秘的疾病。
然而,之间擦拭我的鼻子,并呼吁平静下来,他仍然能插入一些肯定生命的短语zabavchik我说:
我的态度是我必须说,在连接诊断,在这两个星期大大改变。 如果直到最近未来,我看到糖果冻的颜色是引起悲伤和不愿意生活,现在是改变其相对的,而大约有相同的结果。
现在的生活我不想由于过度"、"即将到来的未来。
在晚上,我开始克服噩梦,我醒来想到的死亡的权利。 丹尼斯说,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力和恐惧,都给这种现象的一个响亮的名字的"恐慌症",并鼓励喝酊的一个牡丹。
Onaya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主要是味道,就像白兰地,而不是特别有帮助的。
我真的在那一刻,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活下去,直到新的一年。

研究所的神经。
在该研究所的神经在我很快作出一张卡片,并发送给等候在候诊室、医生与洪亮的名字。
由于诊断成为我非常关心的迹象和我自己的直觉。 也许,即使这种虚幻的和短暂的邻的死刺激它的发展。 而现在,步行通过呼应的走廊这个机构,我认为这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我出现在这里。 然后推一切:墙、灰色油布、医生、技术车。 这整个的身体产生的灰可怕和令人沮丧的。 这似乎是说,你甚至一个时刻,放松警惕,他peresevat,不会是缓慢的吞咽和消化你在她的尘土飞扬的子宫。
即使花在这个地方看到的疯狂和痛苦的游客。 他们留下一种痛苦的印象是残酷的自卑感和丑陋。
在医生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实例。 惊人的小花,serissa他那厚厚的白色源,荆棘和小革光绿叶。 他就像是一个纠结的厚的棘手电缆、贪婪地伸越过栅栏的窗户累射线设置秋天的太阳。
我是快速审查,并迅速确认了第二诊断丹尼斯,在基础研究他自己的记录,指出我的好运气。 和他提供了一个快速发表声明的免费的研究正在进行的研究所,一个有希望的海外的药物称为Rebif,一个课程,其费用几千美元。 再次很快被驱逐回家,而没有进入细节,并承诺呼吁在未来几个月。
离开建立的,我看见一个男孩的约十四、拐旁边他妈的步态的一个喝醉了,拄着拐杖。 这次有益的和准备信息从一个医学参考书、想象力允许的想象自己在他的地方。
今年第一次。
第一年RAM,或者说在过去的5个月我在做的主要事实,不断哭泣在晚上在枕头上,访问因为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工作,并没有出卖他们的内心状态对其他人。 有关的疾病只知道我丈夫和我的父母。 总结情绪的背景的平衡的这一年,开始与一个繁忙的婚礼、婚礼和蜜月,所有被诊断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固不间断的,甚至一个时刻抑郁症。
我的身体状况的努力丹尼斯和储备金的力量在我的身体逐渐回到基线。 事实上,没有什么在我的生活没有改变,除了明确的信念,即我会活不长的、坏的和在结束时,在10-15年将死亡。
这种知识可能由我来"唤醒"一些在其他人之前,要问的问题,开始报警许多人在结束...
为什么实际上这一切呢? 为什么是我给出这样的生活? 什么是它的意义? 我们的目标吗?
前景是,由于我的东正教教育,分别与道德的评估提交的自身是由支配的基督教价值观和规范的现代正统的道德。
我相当积极参加了该研究的东正教教堂。 我的参考书籍,在这一时期是法律上帝的福音,新的和旧约,祈祷书和生命的圣人。 我参加了正统的互联网资源,论坛收集信息有关的一切,是与意识形态概念的正统,它是该疾病的理解,并与东正教的医学。
忏悔,祈祷已经成为我的医药。 他们的信贷相当有效,这是唯一带来了道义救济,并没有最后陷入绝望。
此外,由于取得儿童的概念的信念,允许创造奇迹,我是很容易地适应新的痛苦现实比其他许多人没有经验的信仰。
单词"genuflection":"后的"、"耶稣祈祷","忏悔",一个奇怪的声音在现代世界的办事处,广告和金钱。 尽管如此,我随后能够结合这些概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
庆祝活动的2002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 首先我发现我是活着的,二,并可以承受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磁铁"生存",并脑再次填充的,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传统医学、神秘主义、灵修、世界宗教、替代医学。 不再是提前知道的未来,僵局的句子理性的医生。 在相反的许多狭窄的绕路跑在我前面在不同的方向。
伟大的命武士"纪念品"仍然不理解的,但似乎没有我只是一个美丽的语和幽灵的死亡与我经常在夜晚用湿冷的恐怖的恐慌。
我停止做梦。 完全停止。 上帝沉默,而每天晚上,我悄悄地沉浸在黑暗中,无法找到在我的记忆到早上有什么,但空虚。出版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加入我们在Facebook,脸谱了,语音
资料来源:www.free-apple.ru/index.php/myworks/multiple-sclerosis-2/37-individual-experiment
迟早的人开始要求永恒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生活吗? 因为我活着,而唯一真正办法,我花费的时间分配我在地球上? 如果我很高兴吗?
闪烁在繁忙的办事处之间的灯光大城市,走在了人行道主,感觉在钱包或乳腺他的夹克口袋月薪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2August2001.

我躺在沙发上在他的莫斯科的公寓和为什么我没有别的生活。 一个奇怪的软弱、绝望和缺乏任何愿望。 一个绝望的沉闷和灰色。 无论我是,在运输,在度假时,在晚上,天早上,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样的生活?"
这就是她所能够提供我吗?
常沮丧和饱我的同伴中的23年。
我记得很清楚的时间。 我有一个"完美"的薪金对于我的年龄和职业的、适合于她的"休闲的"。 通过教育我是个营销人员。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营销,也许比大多数。 品牌管理、创建者、管理顾问。 我已经知道了一定数量的工具的操作,知道如何形成的思维过程在人们心目中的谁知道他们的反应能力,刺激,你知道的梦想的人们睡着了,并感到他们的梦想明天...梦想的群众是可预见和公式化的,它们取决于我这样的人。
两周前,我嫁给了一个心爱的人。
在过去两周我们要去度蜜月到希腊并得到了很多积极的情绪。
我年轻、漂亮的、成功的,我所有的梦想,那个搅拌的想象力,在青春期到达,那么我什么感觉? 幸福吗?
也许幸福是在个人生活变成了一个熟悉的背景的感觉的一些丰满。 但同时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伤,并希望死亡。 我看见我未来的生活一目了然,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场景,对这个最美好未来的生活我懒得连一根手指。 我受到威胁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而我走到其开始。
来全副武装的最大数量的分,明天所有应转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两年,我将有一个单独的科比片在莫斯科,在不良于3-4年,然后我就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上周末,我们将一起去购物和每年一次在海岸上,我会收集他们在一个花园,襁褓,购买玩具和书籍与刺猬和兔子、涂抹zelenkoj成的膝盖,检查家庭作业。
脂肪,新衣服、"一个成功的事业"、私人汽车,跟朋友和obsasyvanie空闲闲话,也许是情人。 并没有什么更多。
我吓坏了这个前景。 我23岁。 我有一套完整的意外废料的浪漫幻想和复合物的青少年时期,固图书馆阅读,极多特有的年龄,以及一个关键要看的东西。
外面,天倾向于傍晚和太阳到地平线上。
沙沙作响的其陈旧和树叶尘土飞扬的疲倦的老头八月,我躺在沙发上花费的分析已经通过并仍然有生活、感觉一个累。
我闭上我的眼睛和听到的内部黑暗的空虚,安静,没有情感,因为如果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说:
—我不想活了。
八月15,2001年。
我去办公室,到我左边的代表空棕色书桌上摆着一厚厚的书,铭记在脊柱上"等等等等等等神经病",显然旨在灌输信心在患者的尊严和教育的医生。
在这里,他是。 鉴24日至27年。 我的年龄。 以及所有我现在将开始愈合,感到悲观,我认为我自己,注意到桌上的任何特性的内在我的意见"主管医生",但是几笔,而臭名昭着锤子。
—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似乎是尴尬的年轻人,显然在我的监督。 它必须是他第一天工作时,我决定无可奈何,坐在一张椅子,并告诉关于他的灾难。
—脱衣服,被迫满不在乎的调中断的流我的想法,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并采取一座在沙发上。
—怎么带? –我感到惊讶。
—你有没有从来没有看神经科医生吗? 可以保持你的内衣上,他补充说,...找回来。
然后检查,在这期间我刺针,殴打一个锤子在膝盖上,触摸的测试管的热水和冷水的皮肤的手和脚。
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从来没有看神经科医生,一定要获得很多新的感觉。 博士有趣聊天花40分钟的我的考试...
—最有可能的,一个捏脊椎骨乐观,宣布医生,描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必要的考试。
—走路一两周内获得按摩一切顺利,但要确保这种审查,它被称为MRI(磁共振成像)坚持对医生,交给我的方向。 我们需要消除所有其他的选择。
再见丹尼斯笑着,我完全放心和迷住了新朋友。 感觉到我所要说的是不重要的是,一周之前检查我没有灵敏性皮肤上的脚。 没什么,当然,生活并没有停止,但的感觉是不愉快的。
我乐观地开始去按摩,并且它似乎第三届会议开始了解受虐狂,在经历高兴地从痛苦。
17August2001.
坐在等待室。 在队列中的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坐在旁边一个的女人跟一个男人,大约五十、贫在一些灰色的,灰色的未清洗的头发一个包子,她单调重复相同的短语,"恐怕我"时,它就像一个连续的嚎叫"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 abuseabuse的..."。 她拥有权利的手在他的左边,来回摆动,因为如果抱着通过一个小的孩子。
她旁边坐着一个累了被殴打的人在一个皱巴巴的棕色的西装,有的裤子都清楚地短的最好的长看起来是黑色一半桅杆的袜子和尘土飞扬的鞋子。 他的脸皱巴巴的诉讼。 显而易见的是,他遭受的痛苦坐下来一个人,这种持续不断的单一分钟的面粉和同情的斗争与疲劳和不适。 有时候他有气无力地试图中断她喜欢的软,某种安慰的话,那么该妇女在灰色冲进歇斯底里的话,"他们会带走我的手,这是癌症,他们将会带走我的手,就像我没有手"和呜咽中...然后他们出去和她再次返回到他的塞克斯顿"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虐待...".
我坐在旁边给他们一个白色皮沙发,因此,她棕色的裙下摆我的衣服。
我们周围的去清理医生戴的帽子和鞋套、无菌的植物生产的一些高纯度的铝。 看看我的眼角的老夫妇和近身体上感觉到动物恐怖的一个人谁是要"采取臂"。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我自己的眼睛。
我毫无准备的,不知道如何作出反应。 疯狂地想了解存在这种休闲妇女不可以。 我的想象力和大脑拒绝以试试皮肤上的一个猎人。 它闻起来太可怕了,粘灰色的恐惧、痛苦、失望和痛苦。 "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ябоюсь busabusss的..."。
怎么长这种酷刑的?
突然从后面的门进来的女人的医生。 与一个混合的厌恶和可惜看来,在老年妇女,读她的方向,并说他们需要转到另一个房间。 男人匆忙捡起来,找医生在眼睛,然后东西滴下,拿起他的妻子,并导致出口。
女医生,请和具有明显的救济,看着我,采取的方向,快速读和导致进入一个房间里有白色的长方形单元提供关闭,锁定了我的手机,包和衣服的安全。 习惯性的运动使我长的、紧张的管MRI,锁的脖子和肩膀上。
记得白色的光滑的塑料的上限,并听取了刺耳的声音的振的,因为如果困扰着一些巨大的电子网络的史前动物。
我很害怕。
关闭空间和阶段,不出来的头部。 "Busabusss..."戒指在我的耳朵。
我觉得一分钟,我将复盖一个波动的恐慌。 闭上眼睛,试着冷静你的呼吸,想象一下,一个偏僻的小屋高在山区,长满了青苔的、黄色的草地上,美化,添加在画面上的雨滴的分支机构和太阳。
几乎平静下来。
最后这一切结束。 我滚出的管,我要除去的塑料保持领。 微笑着淡淡的,试图对眼睛的医生读的诊断。
她回答说,支吾感兴趣的名称和地方的工作,我的医生,初步的诊断和完成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有没有被诊断患有MS?
我的回答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母的组合,从她,不会,我没有。 她看着我难以置信,再次感兴趣的症状,然后摇他的头部和滴:
等待。 一旦结果已经准备好,会打电话给你。 我再次落在同一张沙发的。 一段时间后,有来自另一个科比片。 她看起来心不在焉地周围,并询问是否有与我的家庭。
已经认识到这狗屎打击了风扇,我看着她的眼微笑着问
—没有,什么?
她叹息,隐藏她的眼睛,并请你进入办公室。
内阁是更喜欢一个任务控制中心,在阴影里神秘的pomigivayut一些蓝色的灯泡,并按钮。 房间里有几台电脑后面他们坐四个白色,像个机器人烦恼的。
女医生邀请我去接近表,去洗手。
也许她有一个病干净的手,记得她厌恶看到的老人,我想。
过来这里,并邀请第二位医生和我的方法照亮玻璃墙上挂图片的我的内脏。
我不认为许多人不得不看到你的大脑和脊柱方面:)应该注意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
医生开始,一个沉闷的声音,以决定一个描述的我的照片pechatalsya学生的实习生...多个病变的白色物质的大脑局部的水平。径...囊肿...分区...在同一时间像在演讲厅,我和我的实习生展示所有这一切都在照片我的名字在角落里。
受训人惊讶的是,和狂躁仔细地看着我,作为一个生活津贴。 我在这个时刻,正在奇怪的边界条件,如果它是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我的睡眠。 我看到了整个现场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我们自己,如三维投影、固定中心的所有细节发生了什么事、声音、气味的空气流动和白色的懒汉坐在旁边一个的女孩。
最后仔细清单和记录所有的独特特征,而事实证明,我漂亮的花了的蛾大脑她沉默的每个人都看着我。 我觉得更多一点,从我的眼睛泼的眼泪。 停止。
微笑着,慢慢说:
—所以...现在告诉我人类的语言,这意味着什么吗?
让你解释这个通过你的医生,我不能给你一个诊断,她说,有些挑衅,如果在自卫。
—不过,你有私人的想法? 分享。
—最可能的是,它是多发性硬化症—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逐步残疾并最终死亡的患者。
–不可治愈的疾病,她说,严重后暂停。
—也就是说,这是什么? 不治疗? 可以在国外?
在这个阶段的发展现代医学的有效的药物可以极大地改变病人的位置在这种疾病,没有找到。
但是你不用担心,你是非常幸运的是,你已经发现了该疾病的早期阶段,说谢谢你的医生,而且,现在有许多方法可以延长一个全人类的生存在这个疾病,...
—一些患者甚至居住的10-15年来的热情的一个学生增加了实习生从房间的角落里.
医生看起来不以为然。 我已经不要听他们的...转动的图片,并离开办公室...听到的轨道。
—你很幸运...10年前你绝不会有一个机会,现在,科学正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步伐...
哦,幸运的男人—我听到我的头,我自己的声音。
地铁并且继续处于休克状态,虽然我的眼睛都是干想法,围绕在我的头令人震惊的速度,然后冻结在发呆,同时,我继续以惊人的清晰度捕获、周围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在我的前面,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女孩。 看起来大约18,大大的蓝眼睛、光线长长的棕色卷发现头发,哈巴狗鼻子的雀斑,在她的手持一束矢和无法哄停哭泣...滚滚的泪水从她的眼睛。 年轻人的微笑和一些东西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以某种方式安慰她。
抑郁症。
我随后对话的有丹尼斯,被中断时与我的眼泪和鼻涕,因为我非常熟悉互联网,并参加到已经收集信息有关这个神秘的疾病。
然而,之间擦拭我的鼻子,并呼吁平静下来,他仍然能插入一些肯定生命的短语zabavchik我说:
- 它不是致命的。 虽然当然如果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发炎是在呼吸中心和医生没有时间,那么这是重症护理单元,因此没有。
- 街道上是下降的砖头。
- "治愈"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意味着官方药品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这一疾病,因此不能够治疗。 这并不意味着处理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存在孤立的情况下自发的恢复。 我有没有运气有一个解决方案,和人们从事其职业,并应处理、尚未了解到它的结束。
- 老年痴呆症的判断结果的MRI因此我没有威胁,至少现在。
我的态度是我必须说,在连接诊断,在这两个星期大大改变。 如果直到最近未来,我看到糖果冻的颜色是引起悲伤和不愿意生活,现在是改变其相对的,而大约有相同的结果。
现在的生活我不想由于过度"、"即将到来的未来。
在晚上,我开始克服噩梦,我醒来想到的死亡的权利。 丹尼斯说,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力和恐惧,都给这种现象的一个响亮的名字的"恐慌症",并鼓励喝酊的一个牡丹。
Onaya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主要是味道,就像白兰地,而不是特别有帮助的。
我真的在那一刻,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活下去,直到新的一年。

研究所的神经。
在该研究所的神经在我很快作出一张卡片,并发送给等候在候诊室、医生与洪亮的名字。
由于诊断成为我非常关心的迹象和我自己的直觉。 也许,即使这种虚幻的和短暂的邻的死刺激它的发展。 而现在,步行通过呼应的走廊这个机构,我认为这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我出现在这里。 然后推一切:墙、灰色油布、医生、技术车。 这整个的身体产生的灰可怕和令人沮丧的。 这似乎是说,你甚至一个时刻,放松警惕,他peresevat,不会是缓慢的吞咽和消化你在她的尘土飞扬的子宫。
即使花在这个地方看到的疯狂和痛苦的游客。 他们留下一种痛苦的印象是残酷的自卑感和丑陋。
在医生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实例。 惊人的小花,serissa他那厚厚的白色源,荆棘和小革光绿叶。 他就像是一个纠结的厚的棘手电缆、贪婪地伸越过栅栏的窗户累射线设置秋天的太阳。
我是快速审查,并迅速确认了第二诊断丹尼斯,在基础研究他自己的记录,指出我的好运气。 和他提供了一个快速发表声明的免费的研究正在进行的研究所,一个有希望的海外的药物称为Rebif,一个课程,其费用几千美元。 再次很快被驱逐回家,而没有进入细节,并承诺呼吁在未来几个月。
离开建立的,我看见一个男孩的约十四、拐旁边他妈的步态的一个喝醉了,拄着拐杖。 这次有益的和准备信息从一个医学参考书、想象力允许的想象自己在他的地方。
今年第一次。
第一年RAM,或者说在过去的5个月我在做的主要事实,不断哭泣在晚上在枕头上,访问因为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工作,并没有出卖他们的内心状态对其他人。 有关的疾病只知道我丈夫和我的父母。 总结情绪的背景的平衡的这一年,开始与一个繁忙的婚礼、婚礼和蜜月,所有被诊断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固不间断的,甚至一个时刻抑郁症。
我的身体状况的努力丹尼斯和储备金的力量在我的身体逐渐回到基线。 事实上,没有什么在我的生活没有改变,除了明确的信念,即我会活不长的、坏的和在结束时,在10-15年将死亡。
这种知识可能由我来"唤醒"一些在其他人之前,要问的问题,开始报警许多人在结束...
为什么实际上这一切呢? 为什么是我给出这样的生活? 什么是它的意义? 我们的目标吗?
前景是,由于我的东正教教育,分别与道德的评估提交的自身是由支配的基督教价值观和规范的现代正统的道德。
我相当积极参加了该研究的东正教教堂。 我的参考书籍,在这一时期是法律上帝的福音,新的和旧约,祈祷书和生命的圣人。 我参加了正统的互联网资源,论坛收集信息有关的一切,是与意识形态概念的正统,它是该疾病的理解,并与东正教的医学。
忏悔,祈祷已经成为我的医药。 他们的信贷相当有效,这是唯一带来了道义救济,并没有最后陷入绝望。
此外,由于取得儿童的概念的信念,允许创造奇迹,我是很容易地适应新的痛苦现实比其他许多人没有经验的信仰。
单词"genuflection":"后的"、"耶稣祈祷","忏悔",一个奇怪的声音在现代世界的办事处,广告和金钱。 尽管如此,我随后能够结合这些概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
庆祝活动的2002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 首先我发现我是活着的,二,并可以承受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磁铁"生存",并脑再次填充的,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传统医学、神秘主义、灵修、世界宗教、替代医学。 不再是提前知道的未来,僵局的句子理性的医生。 在相反的许多狭窄的绕路跑在我前面在不同的方向。
伟大的命武士"纪念品"仍然不理解的,但似乎没有我只是一个美丽的语和幽灵的死亡与我经常在夜晚用湿冷的恐怖的恐慌。
我停止做梦。 完全停止。 上帝沉默,而每天晚上,我悄悄地沉浸在黑暗中,无法找到在我的记忆到早上有什么,但空虚。出版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加入我们在Facebook,脸谱了,语音
资料来源:www.free-apple.ru/index.php/myworks/multiple-sclerosis-2/37-individual-experi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