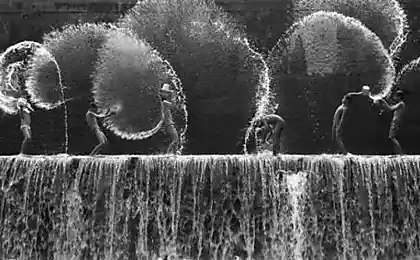508
教育的儿童在家庭帝国

记忆的大公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关于他童年。 纪律、军事演习,没有娱乐和软相当一个斯巴达的养育,规范实际上的君主的欧洲。
以下在他父亲的脚步,皇尼古拉斯,我,一个人的特殊的直线度和硬度的意见,我的父亲认为有必要,他的孩子们带到了一个军事精神,严格的纪律和职责的意识。 监察长的俄罗斯大炮和总督丰富的高加索地区,团结对二十个不同的族裔群体和交战部落,并没有分享现代化的原则的温和养育子女。 我的母亲结婚前,公主的塞西莉亚*巴登、成长起来的日子时,俾斯麦是德国能通过血液和铁。
所以,毫不奇怪的乐趣无忧无虑的童年突然结束对我的那一天,当我七岁。 其中许多礼物,podnebesnykh我在此之际,我发现统一的一个上校73克里米亚步兵团和剑。 我捧腹如想象那现在将删除他自己的衣服,其中包括短,粉红色的,丝质衬衫,宽长裤和靴红摩洛哥,并穿上军装。
我的父亲微笑和握着他的头部。 当然,有时我会如果我会听话穿上这个优秀的形式。 但是首先我必须赢得的荣誉穿她的尽职调查和年份的工作。
我的脸下降,但最糟糕的是,尚未到来。
—明天—已经宣布我的父亲你从幼儿园。 你会住在一起的兄弟迈克尔和乔治。 学习和遵守你的老师。
永别了,我的保姆,我的童话故事! 再见无忧无虑的梦想! 所有的夜晚我哭到我的枕头,不听到的令人鼓舞的话我的好老哥萨克舍甫琴科。 在结束时,看到他答应我每个星期天不会使我成为一个正确的印象,他开始语焦急地:
这将是一个耻辱,如果他的皇帝陛下将看到这一点,并得到了军队,他的侄子,亚历山大王子,不命令73克里米亚团,因为哭得像个小女孩。
听到这个,我从床上跳下来冲洗。 我被吓坏了,这几乎毁了我们全家的眼里的皇帝和俄罗斯。
从这一天,直至十五岁时我成长是喜欢的通道的军事服务团。 我的兄弟的尼古拉斯,迈克尔,乔伊,乔治和我住在兵营。 我们睡在狭窄的铁床铺着薄薄的床垫放在一个木板上。 我记得的是,许多年后,我的婚姻,我不能获得用于豪华大床和双人床垫和床单单和要求回到我的旧折叠床上。
我们唤醒在早上六点. 我们不得不跳在作为一个谁想"睡五分钟,"惩罚最严格。
我们阅读祈祷,站在一排在她的膝盖前的图标,那么采取了一个冷水澡。 我们的早晨早餐包括茶叶、面包和黄油。 其他的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所以不习惯于我们的奢侈品。
然后来到教训的操和围栏。 特别注意实际类的火炮,为此,我们的花园很小的火炮。 很多父亲没有警告来到我们的类别,严格遵守一个教训以火炮。 在十岁我可以把部分的炸弹的一个大城市。
上午8时至11日和2日至6我们不得不学习。 在传统的大公爵不能了解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私立学校,但由于我们被包围了整个团队的辅导者。 我们的课程被划分为八年期间,包括吸取的经验教法神,历史的东正教教堂,比历史上其他的供词,俄罗斯的语法和文学、历史的外国文学,历史俄罗斯、欧洲、美洲和亚洲,地理学、数学(体现算术,代数、几何形状和三角)、语文法语、英语和德语,以及音乐。 此外,我们被教导使用火器,也能,击剑,刺刀攻击。 我哥哥尼古拉斯和迈克尔还研究了拉丁美洲和希腊、美国、初中,摆脱了这种酷刑。
行使不是难为我和我的兄弟,但是过度严格的导师们留下的所有残的苦头。 它是安全来说,慈爱的父母反对,如果他们的孩子提出的定义在俄罗斯帝国大家庭的时代,我的童年。
小的失误在德国的话我们被剥夺了甜的。 错误,在计算速度的两个碰撞车—一个任务就是对数学教师特别提款吸引力,在他身后站在他的膝盖鼻子的墙壁上的一个个小时。
有一次,当我们带来眼泪通过一些不公正的教师和试图表示抗议,随后通过一份报告父亲的名称的煽动者,和我们受到严厉惩罚。
我将永远无法理解如何这样的压迫性体系的教育迟钝我们的思想和不引起的仇恨,所有这些主题,我们被教导的童年。
应该的,但是,添加所有的君主的欧洲,似乎来到默示协议,即他们的儿子应该带来的恐惧上帝对于正确了解的未来的责任的国家。 许多年以后,共享他们的记忆,与德国皇帝威廉,我的理解比较柔软的我们的第比利斯的教师。 他的继承人,德国王储,嫁给一个我的侄女,干巴巴的加入,该数量的惩罚,接收儿童的父亲-君主的减轻了审判径,这是他的儿子。
早餐和午餐,所以甜蜜生活中的每一个家庭,并没有作多样性的严格程序的我们的成长。
总督的高加索地区被认为是一个代表皇帝在处理数以百万计的忠实的臣民生活在俄罗斯南部,并在我们的桌子上坐着每天至少30或40人的官员来到高加索地区的从圣彼得堡,东部的统治者将被提交给国王,军事指挥官服从于总督的省份和地区,公众人物以及他们的妻子,人员的随从和女士们本庭, 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我们的导师所享有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应用各种主张在第比利斯的宫殿。
我们的儿童在早餐和午餐,真正照顾自己,而不是开始讨论,直到我们被要求的。 多频繁,燃烧着的愿望告诉我的父亲约什么一个美好的堡垒,建立在山顶或者什么的日本花卉种植通过我们的园丁,我们举行后,沉默并听取的重要的一般人咆哮有关荒谬的最新政治计划迪斯雷利的。
如果我们被要求的任何问题,这当然,是做出来的一种屈从前总督的陛下,我们必须回答的框架内,我们订严格的礼仪。 当一夫人,一个体弱多病的甜美的笑容,她的嘴唇上,问我关于什么的我想是的,她知道这个大公爵亚历山大*无法想要既不是一名消防员也不是一个工程师,以便不招致不满的大公爵的父亲。 选择我的职业生涯的故事是非常有限:它奠定之间的骑兵,这是命令我的叔叔,伟大的王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老年人,大炮,这是由我的父亲,海军,这是我其他的叔叔—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
像你这样的男孩'他说笑的女人是最好要跟随你的皇室的父亲。
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干掉一个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个时候十二双眼睛我的导师看着我,想让我一个体面的答案?
兄弟乔治胆怯的表示希望成为一个肖像画家。 他的话是会晤了不祥的沉默的所有现有的和乔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能当室-走狗,abrasivi客人的甜点是复盆子的冰淇淋他设备。
分配的席位在桌上排除了为我们的孩子们,任何机会来嘲笑那些或其他奇怪的客人,或是耳语之间的自己。 我们从来没有允许坐在一起,并放之间的成年人。 我们解释说,我们应该行为对我们的邻国,作为会表现我们的父亲。 我们必须微笑的时候糟糕的笑话我们的客人,并采取特殊兴趣的政治新闻。
此外,我们必须始终记得有一天你会骑到俄罗斯,其范围之外高加索山脉。 在那里,距离我们的皇叔叔告诉我们,我们感激地记得我们的导师,我们向他欠我们的所有良好的举止。 否则,我们的兄弟将他们的手指在我们并呼叫"狂野的白种人"!
越来越从表,我们能够发挥父亲的房间一个小时内早餐后二十分钟后吃午饭。 在整整九,我们不得不去到我们的卧室,穿上白色的长夜衬衫(睡衣是还不知道在俄罗斯),立即躺下睡着了。 但在床上我们是在严格的监督。 至少五次夜班的教练进入房间以及铸造一个可疑的床,其根据涵盖的是卷曲的五个男孩。
午夜我们醒来叮当作响的刺,听到来的父亲。 在请求我的母亲来唤醒我们,我的父亲回答说,未来的士兵需要学会睡眠,尽管任何噪音。
—他们会做什么,然后,他说,当他们夺走几小时的休息时间,在听炮火?
眼中的我们的父母和看护人,我们都是健康、正常的儿童,但现代的老师会找到我们不满意的渴望更多的爱和感情。 我们遭遇的灵魂从孤独。 我们的特殊情况之间的距离我们和孩子们我们的时代。 我们没有任何人交谈,我们每个人太骄傲分享他们的思想与其他人。
一个主意来和父亲打扰他模模糊糊的对话没有特殊的目的,只是似乎疯狂。 我们的母亲,为其一部分,作出一切努力来摧毁我们丝毫的外在表现感情的温柔。 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学校的斯巴达的教育精神的时在德国,并归咎于她。
...记住他的童年和严谨的教育和治疗的我们,我必须说,所有这有一个最有益的影响上所有随后的生活。 我必须补充的是,所有国君艾佛利似乎已经来到默示协定,儿童应在trasvase的恐惧上帝对于正确了解的未来的责任的国家。
источник:psychologos.ru
资料来源:/用户/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