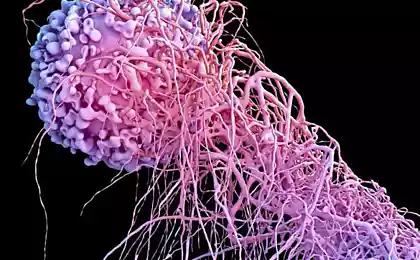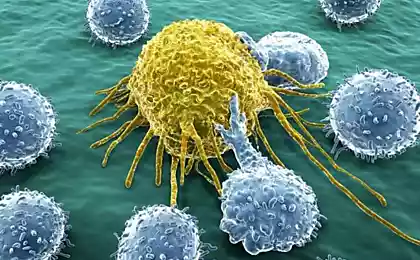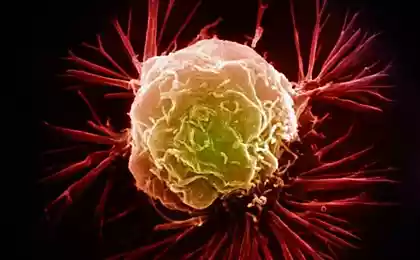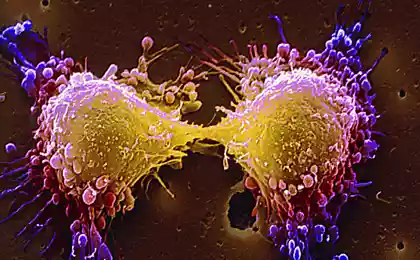589
喀秋莎Remizov。 关于癌症、谦虚和宽恕
喀秋莎Remizov离开耶和华至29岁的时候,在晚上八月1日,2015年的四年中,她打了癌症,幸存下来的五的手术,八轮化疗。 她非常勇敢地经受了疾病、不断交流,在最近几个月–每一天。
请求休止的神的仆人凯瑟琳! 殡葬服务将举行上午9时30分在3月,在圣殿的所有仁慈的救主。
当这种疾病已经进入终端阶段,喀秋莎决定,这是重要的是要分享我的经验通过和住宿的疾病,解释在心理上和情绪上的变化造成的癌症。
记录塔玛拉Amelina:
在2014年秋季我来到她家在Ramenskoye,和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14个小时的一天。 回家工作Katia的丈夫,安德鲁,从幼儿园五岁的儿子Zachary的。 我们有舒适的居住在客厅里,喝茶用凯特的熟苹果馅饼,仅打破了窗口时开始的黎明。 我认为有人这个故事将有助于使自己的疾病,并且有人只是学会了它是如何成为癌症患者。
说什么–我最喜欢谈论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疾病。 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开始治疗,我再看到它并且记住它是多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的疾病,生活在一个框架。
事实上,这种疾病提供一个很好的经验,我想和大家分享。 虽然通常试图告诉你关于癌症和它成为一个教训。 或历史中的这种疾病在医疗感枚举的操作,医生、其他详细信息。 并且我已经注意到许多倍,如果一个人不需要知道的东西,他不会听到它。 这发生了几次不同的人在我的故事只是睡着了,即使如果你不想睡觉! 我现在往往作为帮助台–很多人当他们了解的朋友、亲戚那里是这样的诊断。
–问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的,这是正确的。 或祈祷,我叫到一个有病的人,只是和他谈谈。 它并不总是有必要解释下一步该怎么做,有时你只需要倾听、支持、分享这些困难的情绪。 经常对话的发展。
这一切如何开始的第一严重疾病的迹象,其中包括出血,来到我在十八岁。 我认为压力与他的家人从塔什莫斯科,与气候变化,入学的大学都不是徒劳的。 我和怀孕期间都令人不安的迹象。 上帝只保持婴儿。 通常人们不想认为任何不好的想法,我没有。
当我还是25,我是一个哺乳的母亲,Zahara六岁那年,我有一肚子疼,开始一个奇怪的症状。 我觉得抓住了在某些不可避免的磨盘,情况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 我试图联系有些医生做一些事情,什么都没有。 即,医生、救护车没有来,亲属不采取这种情况严重。
我们坐下来与我的丈夫,和我说,"你知道吗,安德鲁,我没有力量生活。 你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个俏皮话,这是不是某种操纵的,我告诉你实话说:我没有力气呼吸,行走。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所有给出巨大的努力。"
我甚至随后写道:如果你的人开始抱怨的疲劳,如果他有任何不寻常的症状,试图说服他去看医生。 人类自己帮助自己不能,目前它是内部的情况。 和这个短语,"拯救溺水是该企业的溺水",是根本错误的。 因为人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欣赏它来自外部。 它似乎他,他是所有权利。 如果一个人依良心拒服,然后使事情更糟的是他觉得他是罪魁祸首。
我去地区医院,每个人都认为我有阑尾炎。 医生不能把握为什么这个女孩,白痴只是尖叫血腥谋杀。 我去的工作表在各种各样的保证的工作人员:"你这样的疾病"。 然后医生们把我和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肿瘤,传播通过的腹腔脓。 医生们吓坏了,他们出来告诉我的家人,做最坏的打算,最有可能,就会很快死亡,她有癌症...
在这里,在所有这trashaway情况下,我去医院,试图与世界互动和理解,我有一个真正的阿富汗综合症,当时有和平,我有,我觉得我在玻璃后面,分开。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享受生活的时候有这样的痛苦和这种恐怖。
我跑进一个朋友在商店和她问我:"你好吗?"这样的责任问题,我想说的是,事情很糟,她说,"腹膜炎吗? 我妈妈有腹膜炎,没什么,没什么。" 和一切是如此的响应。 你们在隔离的,因为我不能忍受这种痛苦倒和措施,从这个痛苦没有一个人不能理解。
然后我遇见一个朋友,谁失去了她的丈夫。 我们遇到了她的看法,我看到,我明白了。 人们曾经历的严重的痛苦不会通过由另一人的痛苦。 现在我已经拥有一个相当大的一群人与他们沟通,而且我们不需要彼此的解释什么,长长的单词是不必要的。 它就像一个穿成一个秘密俱乐部,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无话。
治疗。 医生。 天使–约Kashirku说:"所有好有设备和工作人员。 他们有一个问题–病人。" 这样一个百分之百。 你知道,像挽歌:人们微弱的队列,去最后,他们的圈子里的地狱举行许多许多倍。 许多人存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不属于外科手术或治疗。 有这样一个系统,一个人可以坐在办公室,医生(他们入口的走廊和出口的另一边已经长了去了-去了-去了...病人坐在和将仍然坐了整整一年。
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 当我来到你研究所roentgenology和放射学,我认为这是天堂。 安德鲁在第一次会议上外科医生说:"我已经准备好给你任何金钱"。 和外科医生,他说:"你疯了吗? 你有妻子死了,而你是一种浪费时间。 让我们快速地在这里。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操作的明天"。
我是家里死去,我有一个很长的嘲笑对Kashirke的。 我期待的最坏的,你知道吗? 我是在医疗部门的癌症中心,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地,看着它,并认为:也许这里的人们刚刚离窗户的白鲑。
–就像其他的一切都在德国!
–我明白,我受伤了吗? 我们有同样的事情和在欧洲诊所,这在研究所。 没有人相信我。 大家都说,"什么,你在俄国? 是的,你在撒谎!"的。 我们被送到不同的欧洲诊所的文件,以及所有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医生治疗的绝对正确的。 唯一的问题在俄罗斯就是康复。
后第五手术,她去后立即第四,我不能醒来的痛苦,有一些雾。 我听到的声音和我不能打开我的眼睛。 在重症监护天使的工作,这是重要的,给你醒了过来。 我似乎是清醒但无法打开他的眼睛,只听到他们的呻吟声。
我来到麻醉师说,"凯特,现在你要弯曲,我会放一个硬膜外麻醉的,你有耐心的,我亲爱的,我会确保你不会伤害"。 我立刻更加容易。 但是,由于胃管在鼻子我不能呼吸,我遭受可怕的,我的医生说,"你是我的阳光,我的快乐,哦,等等一点点。" 我开始它的所有自己的轻轻地。 我有泪水,鼻涕,流口水。 "对不起,亲爱的,不该以任何方式"。 我有呕吐。 他容忍,轻抚我的头说:"你怎么样,我的穷人,遭受"的。
我已经一周没有工作的结肠。 但是,如果结肠不会开始,然后缝合他的嘴里,生活在没有食物。 瘫痪的肠道,它是死亡。 医生试图说服我说:"卡佳,这是必要喝矿物油"。 不仅仅是矿物油,但最苦苦的世界氧化镁。 和喝酒应该不是一个勺子,和一个大大的老高西研究中。 我看着他的诚实诚实的眼睛说"医生,对于你任何东西! 对你的健康!" 喝一口! 他说,"好,很强的母亲!"
这是另一个级别的关系。 这个医生救了我一次,两次、三次。 我涂抹鼻涕,"所有将不会被处理过了。 你他妈的! 我会杀了你所有的教工休息室!" 和他平息它。 配置的。 诱惑的。
他叫我的丈夫说,"一切权利。 一个奇迹发生了"。 说,虽然他们是人,不是信徒。
当我出来的研究所roentgenology和放射学、思考该如何感谢医生? 钱可以不给,好了,给了一个"一束"的水果,冰淇淋,西瓜。 和麻醉师我不得不一个字母。 我写道,"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你,因为你不是人,你是天使! 是啊,天使不需要说他们是天使,但我不能说的..."。 复苏是困难和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他们很少感谢。 有人会记住,有人是无意识的。
然后有一个复发。 眼外科医生看不到最小。 化学我是很好忍受的,和辐射通过的树桩-甲板上。 在有些情况下,辐照导致了倒退。
难的是如何保持的"可见度"是一个非常困难和痛苦的认识到,在某一点上打破了你的"自助",有时逐字在下降的一个"奇瓦瓦州"要求的人的帮助...
健康的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而可以控制自己,可以创建一个特定的图像,可以做好的事情与任何人不要吵架。 可以长到创造这样的可见性。 但是生病的时候,这个整体的"自我"大幅度崩溃。
但现在特别困难的时期。 我有一个角色,我很高兴见到新朋友,感觉。 但是,我们最近去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我意识到,现在我在一个种类的激情。 一方面,甚至在病,我已经学会了保持外观,一切都很好。 我笑,微笑,高兴,但我现在,尽管药物,总是存在的痛苦。 我有这个功能,比我更糟糕的是,越激烈,我笑不开玩笑。 现在往往意识到,我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没有刹车。
有时候当我问我的朋友把我宠坏了一种疾病。 非常艰巨的体验! 很多有听到您的帐户。
开始与一些亲近的人告诉我这种疾病改变了我的最好的方向。 这些发言的朋友是一个时间,我把它们。 当然,这并不容易,我哭了一个月,然后关闭它的许多记录在社会网络,某些时间在所有它是很难与人沟通。 我的丈夫说,"你问这人的文章的主题。" 这是真的,我问它。
这是一个时刻非常复杂,与两个朋友我甚至恶化的关系,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实话他们怎么想。 我的牧师在这个时刻说:"留住这些人。"
–留下来吗?
他告诉我,"你们谈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油腻的东西,但也有几个人,他们会告诉你真相。" 现在我有点解冻,我意识到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同,仍然继续聊天
当你问的有关面包,需要你的骄傲到克服,以忍受和等待。 在某些时刻已经开始恶作剧。 我的想法总是有很多,我gush,并开始说:"现在我们都将一起做些什么的..."。 我开始决定其他人是这样的一个良好的陷阱的疾病。 我的家人关于这让我开始做。 和牧师对我说:"卡佳,一切。 把自己的手中。 或者你自己做的,或者你只是放弃–放下想法,例如...很显然,水的玻璃你问。 但对于一些舒缓的切,不应变,并决定为其他人"。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意见。
通过这种方式,在板。 对我来说,他们是这么多给! 全陌生的人,熟人写的完全不同。 有人开始的羞辱我,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生病了,我建议在精神"是的,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我不生气我有的一切权利。 像你一样都归咎于他的病情。 我在某一点上所述有关这个神父,他说:"耶和华是你,是你,卡秋莎..."
在第一个我很生气,从技巧,用于治疗癌症的系统是不同的,正式的、非正式的。 并在某些时候打我的头–但是因为人们想要帮我! 不管是什么他们建议,最初的冲动是帮助我。
关于谦卑–所有这些日常发现从"卑鄙的我"。 现在我经常看到的表现他的坏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缺乏能力控制,而所有最不愉快的方面性质是显露出来。 当你做出评论,它伤害,因为即使最讨厌的人,你想要得到一个拥抱-对不起...
我认为在患病期间,我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它需要一些时间,并认识到,不仅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这一切的时候站在的网站上。 我们甚至在该日记有条目:"我终于学会了没有问太多问题的医生。" 在一年的时标上:"永远不得知它似乎"的。
和我的理解是,最好的,我可以有时候做的就是尽量保持沉默。 有时在这种情况有助于仅仅的思想谦卑。 我认为我问了–所以请谦卑自己! 在某些时候我开始害怕要求谦卑,因为我意识到,他可能会通过的痛苦。 我怕的痛苦。 但现在我意识到,它的伤害,但是恐惧是不知怎的消失了...
最困难的是当赞扬。 尤其是如果这是:"哦,你的烈士们,哦,我们几乎都为你祈祷" 它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我真的了解事实真相的是什么情况发生,人们正在试图想象的东西猜想。 在某些时刻,我不认为人们总是写。 也许他们想要的快乐,感到遗憾...有时候一些看似很好的词,这是非常难以接受。
在疾病非常惯例,灰色的,没什么优秀的天,他们错了听到赞扬。 但另一方面,有时的情况非常孤独的,真正独自一人,以至于甚至亲不在身边,他们需要休息。 生活有一个病人是非常困难的。
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不明白。 我们甚至玩笑。 例如,可以安德鲁说他不会回答的电话立刻:"如果你会迟到了我的葬礼,不要生气,但后来得到一个为期三天的周末"。 人,甚至我的教父在恐怖,他说:"凯特,我不该开玩笑的"。 但我通常认为的。 死亡的主题或非常严重的,或是在开玩笑。 另一个选择–没办法。 只是永远不会说话的一次。
证明–我读了抄本讲座的父亲丹尼尔大公当使用"说明不朽的"。 他说你应该觉得男人谁知道他会很快死亡。 对我来说这本书有助于排序。
–有提示吗?
–是的,有权指令。 一年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人,朋友们,大家的友好的话,精神上所述,我的告别。 我和一般的供认,一个非常详细的、非常严重的,牧师说:"现在我自己就会觉得太久,因为我有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拆卸货架上。" 我爱干净,并从这谈我的感觉的一个清洁房间。 我不想这种感觉到的损失,它似乎对我那么,我是死的。
然后我打开电脑,并看到有一个消息有关的死亡阿纳托利*丹尼洛夫。 我已经在这个时刻恰好是歇斯底里...
很显然,我总是认为有关死,但我最后一次准备死亡故意写了一些会。 和那里去的人昨天有个喜欢的。 我甚至不知道阿纳托利读组有关帮我在Facebook的。 "Pravmir",发表我的信在论坛上,阿纳托利写道:"我们非常良好的部件,需要帮助。" 我认为一些nevezuchiy男人! 然后砰! 我愚蠢写遗嘱,然后将该人不知道,不要猜测:他有一个小孩、一个老婆...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打击。 我祈祷了很多第40天...
原谅我觉得癌症可以表现的不满、不信任、绝对和总不喜欢他。 我很想做出的权利要求他们的父母。 心理学家读了很多,我认为,在他们所有的错误和突然这个想法:"停止! 我25岁和我在试图责怪我妈妈我现在不好吗? 是甚至确定了吗?!"
我不得不重新评估的关系与亲戚,而且很严重。 我把玫瑰色的眼镜有关的事实,我现在将有所帮助,所有挤的。 因为在任何时候,可以是一个情况,帮助一些不会。 任何人可能不够,可能会背叛,但它并不因为他是个混蛋,但因为他只是一个男人。
我意识到如何努力,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父母。 我是这么认为:安德鲁,一个成年人将能生存,但不知怎么应付这种情况。 Zahara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安德鲁也是必要的要求首先,他认为男性。 关于我的父母还认为,成年人以某种方式需要生存。 当然,我看见我妈妈很难在某些时刻,但是仍然的情况是显然低估的。 把自己放在地方的父母,我理解它是如何努力,以及陷入这样的恐怖! 我是一个妈妈!
这是不容易原谅你自己。 这事发生在密集的护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愿望,我觉得之前开始。 记得我怎么进口电梯时,我看镜子,看着我是绝对不是我的眼睛,一些陌生人,非常强烈的...看到我。 我看见我自己,如果从外面,听内心的声音:我只是...
关于帮助如果你问的帮助,你应该做好准备,这将是困难的。 可能帮助不会有什么你期待开始。 人们并不像你想象的。 但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需要说"谢谢你"。
我没有写在Facebook"不要祈求我的健康。" 如果对健康的是,它将没有那些的话。 但是我意识到我是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我问你祈祷救赎痛苦和苦难,以避免的考验。
P.S.并记住,只要改变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www.pravmir.ru/katyusha-remizova-o-rake-smirenii-i-proshhenii/
请求休止的神的仆人凯瑟琳! 殡葬服务将举行上午9时30分在3月,在圣殿的所有仁慈的救主。
当这种疾病已经进入终端阶段,喀秋莎决定,这是重要的是要分享我的经验通过和住宿的疾病,解释在心理上和情绪上的变化造成的癌症。
记录塔玛拉Amelina:
在2014年秋季我来到她家在Ramenskoye,和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14个小时的一天。 回家工作Katia的丈夫,安德鲁,从幼儿园五岁的儿子Zachary的。 我们有舒适的居住在客厅里,喝茶用凯特的熟苹果馅饼,仅打破了窗口时开始的黎明。 我认为有人这个故事将有助于使自己的疾病,并且有人只是学会了它是如何成为癌症患者。
说什么–我最喜欢谈论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疾病。 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开始治疗,我再看到它并且记住它是多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的疾病,生活在一个框架。
事实上,这种疾病提供一个很好的经验,我想和大家分享。 虽然通常试图告诉你关于癌症和它成为一个教训。 或历史中的这种疾病在医疗感枚举的操作,医生、其他详细信息。 并且我已经注意到许多倍,如果一个人不需要知道的东西,他不会听到它。 这发生了几次不同的人在我的故事只是睡着了,即使如果你不想睡觉! 我现在往往作为帮助台–很多人当他们了解的朋友、亲戚那里是这样的诊断。
–问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的,这是正确的。 或祈祷,我叫到一个有病的人,只是和他谈谈。 它并不总是有必要解释下一步该怎么做,有时你只需要倾听、支持、分享这些困难的情绪。 经常对话的发展。
这一切如何开始的第一严重疾病的迹象,其中包括出血,来到我在十八岁。 我认为压力与他的家人从塔什莫斯科,与气候变化,入学的大学都不是徒劳的。 我和怀孕期间都令人不安的迹象。 上帝只保持婴儿。 通常人们不想认为任何不好的想法,我没有。
当我还是25,我是一个哺乳的母亲,Zahara六岁那年,我有一肚子疼,开始一个奇怪的症状。 我觉得抓住了在某些不可避免的磨盘,情况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 我试图联系有些医生做一些事情,什么都没有。 即,医生、救护车没有来,亲属不采取这种情况严重。
我们坐下来与我的丈夫,和我说,"你知道吗,安德鲁,我没有力量生活。 你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个俏皮话,这是不是某种操纵的,我告诉你实话说:我没有力气呼吸,行走。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所有给出巨大的努力。"
我甚至随后写道:如果你的人开始抱怨的疲劳,如果他有任何不寻常的症状,试图说服他去看医生。 人类自己帮助自己不能,目前它是内部的情况。 和这个短语,"拯救溺水是该企业的溺水",是根本错误的。 因为人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欣赏它来自外部。 它似乎他,他是所有权利。 如果一个人依良心拒服,然后使事情更糟的是他觉得他是罪魁祸首。
我去地区医院,每个人都认为我有阑尾炎。 医生不能把握为什么这个女孩,白痴只是尖叫血腥谋杀。 我去的工作表在各种各样的保证的工作人员:"你这样的疾病"。 然后医生们把我和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肿瘤,传播通过的腹腔脓。 医生们吓坏了,他们出来告诉我的家人,做最坏的打算,最有可能,就会很快死亡,她有癌症...
在这里,在所有这trashaway情况下,我去医院,试图与世界互动和理解,我有一个真正的阿富汗综合症,当时有和平,我有,我觉得我在玻璃后面,分开。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享受生活的时候有这样的痛苦和这种恐怖。
我跑进一个朋友在商店和她问我:"你好吗?"这样的责任问题,我想说的是,事情很糟,她说,"腹膜炎吗? 我妈妈有腹膜炎,没什么,没什么。" 和一切是如此的响应。 你们在隔离的,因为我不能忍受这种痛苦倒和措施,从这个痛苦没有一个人不能理解。
然后我遇见一个朋友,谁失去了她的丈夫。 我们遇到了她的看法,我看到,我明白了。 人们曾经历的严重的痛苦不会通过由另一人的痛苦。 现在我已经拥有一个相当大的一群人与他们沟通,而且我们不需要彼此的解释什么,长长的单词是不必要的。 它就像一个穿成一个秘密俱乐部,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无话。
治疗。 医生。 天使–约Kashirku说:"所有好有设备和工作人员。 他们有一个问题–病人。" 这样一个百分之百。 你知道,像挽歌:人们微弱的队列,去最后,他们的圈子里的地狱举行许多许多倍。 许多人存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不属于外科手术或治疗。 有这样一个系统,一个人可以坐在办公室,医生(他们入口的走廊和出口的另一边已经长了去了-去了-去了...病人坐在和将仍然坐了整整一年。
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 当我来到你研究所roentgenology和放射学,我认为这是天堂。 安德鲁在第一次会议上外科医生说:"我已经准备好给你任何金钱"。 和外科医生,他说:"你疯了吗? 你有妻子死了,而你是一种浪费时间。 让我们快速地在这里。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操作的明天"。
我是家里死去,我有一个很长的嘲笑对Kashirke的。 我期待的最坏的,你知道吗? 我是在医疗部门的癌症中心,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地,看着它,并认为:也许这里的人们刚刚离窗户的白鲑。
–就像其他的一切都在德国!
–我明白,我受伤了吗? 我们有同样的事情和在欧洲诊所,这在研究所。 没有人相信我。 大家都说,"什么,你在俄国? 是的,你在撒谎!"的。 我们被送到不同的欧洲诊所的文件,以及所有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医生治疗的绝对正确的。 唯一的问题在俄罗斯就是康复。
后第五手术,她去后立即第四,我不能醒来的痛苦,有一些雾。 我听到的声音和我不能打开我的眼睛。 在重症监护天使的工作,这是重要的,给你醒了过来。 我似乎是清醒但无法打开他的眼睛,只听到他们的呻吟声。
我来到麻醉师说,"凯特,现在你要弯曲,我会放一个硬膜外麻醉的,你有耐心的,我亲爱的,我会确保你不会伤害"。 我立刻更加容易。 但是,由于胃管在鼻子我不能呼吸,我遭受可怕的,我的医生说,"你是我的阳光,我的快乐,哦,等等一点点。" 我开始它的所有自己的轻轻地。 我有泪水,鼻涕,流口水。 "对不起,亲爱的,不该以任何方式"。 我有呕吐。 他容忍,轻抚我的头说:"你怎么样,我的穷人,遭受"的。
我已经一周没有工作的结肠。 但是,如果结肠不会开始,然后缝合他的嘴里,生活在没有食物。 瘫痪的肠道,它是死亡。 医生试图说服我说:"卡佳,这是必要喝矿物油"。 不仅仅是矿物油,但最苦苦的世界氧化镁。 和喝酒应该不是一个勺子,和一个大大的老高西研究中。 我看着他的诚实诚实的眼睛说"医生,对于你任何东西! 对你的健康!" 喝一口! 他说,"好,很强的母亲!"
这是另一个级别的关系。 这个医生救了我一次,两次、三次。 我涂抹鼻涕,"所有将不会被处理过了。 你他妈的! 我会杀了你所有的教工休息室!" 和他平息它。 配置的。 诱惑的。
他叫我的丈夫说,"一切权利。 一个奇迹发生了"。 说,虽然他们是人,不是信徒。
当我出来的研究所roentgenology和放射学、思考该如何感谢医生? 钱可以不给,好了,给了一个"一束"的水果,冰淇淋,西瓜。 和麻醉师我不得不一个字母。 我写道,"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你,因为你不是人,你是天使! 是啊,天使不需要说他们是天使,但我不能说的..."。 复苏是困难和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他们很少感谢。 有人会记住,有人是无意识的。
然后有一个复发。 眼外科医生看不到最小。 化学我是很好忍受的,和辐射通过的树桩-甲板上。 在有些情况下,辐照导致了倒退。
难的是如何保持的"可见度"是一个非常困难和痛苦的认识到,在某一点上打破了你的"自助",有时逐字在下降的一个"奇瓦瓦州"要求的人的帮助...
健康的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而可以控制自己,可以创建一个特定的图像,可以做好的事情与任何人不要吵架。 可以长到创造这样的可见性。 但是生病的时候,这个整体的"自我"大幅度崩溃。
但现在特别困难的时期。 我有一个角色,我很高兴见到新朋友,感觉。 但是,我们最近去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我意识到,现在我在一个种类的激情。 一方面,甚至在病,我已经学会了保持外观,一切都很好。 我笑,微笑,高兴,但我现在,尽管药物,总是存在的痛苦。 我有这个功能,比我更糟糕的是,越激烈,我笑不开玩笑。 现在往往意识到,我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没有刹车。
有时候当我问我的朋友把我宠坏了一种疾病。 非常艰巨的体验! 很多有听到您的帐户。
开始与一些亲近的人告诉我这种疾病改变了我的最好的方向。 这些发言的朋友是一个时间,我把它们。 当然,这并不容易,我哭了一个月,然后关闭它的许多记录在社会网络,某些时间在所有它是很难与人沟通。 我的丈夫说,"你问这人的文章的主题。" 这是真的,我问它。
这是一个时刻非常复杂,与两个朋友我甚至恶化的关系,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实话他们怎么想。 我的牧师在这个时刻说:"留住这些人。"
–留下来吗?
他告诉我,"你们谈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油腻的东西,但也有几个人,他们会告诉你真相。" 现在我有点解冻,我意识到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同,仍然继续聊天
当你问的有关面包,需要你的骄傲到克服,以忍受和等待。 在某些时刻已经开始恶作剧。 我的想法总是有很多,我gush,并开始说:"现在我们都将一起做些什么的..."。 我开始决定其他人是这样的一个良好的陷阱的疾病。 我的家人关于这让我开始做。 和牧师对我说:"卡佳,一切。 把自己的手中。 或者你自己做的,或者你只是放弃–放下想法,例如...很显然,水的玻璃你问。 但对于一些舒缓的切,不应变,并决定为其他人"。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意见。
通过这种方式,在板。 对我来说,他们是这么多给! 全陌生的人,熟人写的完全不同。 有人开始的羞辱我,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生病了,我建议在精神"是的,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我不生气我有的一切权利。 像你一样都归咎于他的病情。 我在某一点上所述有关这个神父,他说:"耶和华是你,是你,卡秋莎..."
在第一个我很生气,从技巧,用于治疗癌症的系统是不同的,正式的、非正式的。 并在某些时候打我的头–但是因为人们想要帮我! 不管是什么他们建议,最初的冲动是帮助我。
关于谦卑–所有这些日常发现从"卑鄙的我"。 现在我经常看到的表现他的坏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缺乏能力控制,而所有最不愉快的方面性质是显露出来。 当你做出评论,它伤害,因为即使最讨厌的人,你想要得到一个拥抱-对不起...
我认为在患病期间,我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它需要一些时间,并认识到,不仅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这一切的时候站在的网站上。 我们甚至在该日记有条目:"我终于学会了没有问太多问题的医生。" 在一年的时标上:"永远不得知它似乎"的。
和我的理解是,最好的,我可以有时候做的就是尽量保持沉默。 有时在这种情况有助于仅仅的思想谦卑。 我认为我问了–所以请谦卑自己! 在某些时候我开始害怕要求谦卑,因为我意识到,他可能会通过的痛苦。 我怕的痛苦。 但现在我意识到,它的伤害,但是恐惧是不知怎的消失了...
最困难的是当赞扬。 尤其是如果这是:"哦,你的烈士们,哦,我们几乎都为你祈祷" 它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我真的了解事实真相的是什么情况发生,人们正在试图想象的东西猜想。 在某些时刻,我不认为人们总是写。 也许他们想要的快乐,感到遗憾...有时候一些看似很好的词,这是非常难以接受。
在疾病非常惯例,灰色的,没什么优秀的天,他们错了听到赞扬。 但另一方面,有时的情况非常孤独的,真正独自一人,以至于甚至亲不在身边,他们需要休息。 生活有一个病人是非常困难的。
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不明白。 我们甚至玩笑。 例如,可以安德鲁说他不会回答的电话立刻:"如果你会迟到了我的葬礼,不要生气,但后来得到一个为期三天的周末"。 人,甚至我的教父在恐怖,他说:"凯特,我不该开玩笑的"。 但我通常认为的。 死亡的主题或非常严重的,或是在开玩笑。 另一个选择–没办法。 只是永远不会说话的一次。
证明–我读了抄本讲座的父亲丹尼尔大公当使用"说明不朽的"。 他说你应该觉得男人谁知道他会很快死亡。 对我来说这本书有助于排序。
–有提示吗?
–是的,有权指令。 一年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人,朋友们,大家的友好的话,精神上所述,我的告别。 我和一般的供认,一个非常详细的、非常严重的,牧师说:"现在我自己就会觉得太久,因为我有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拆卸货架上。" 我爱干净,并从这谈我的感觉的一个清洁房间。 我不想这种感觉到的损失,它似乎对我那么,我是死的。
然后我打开电脑,并看到有一个消息有关的死亡阿纳托利*丹尼洛夫。 我已经在这个时刻恰好是歇斯底里...
很显然,我总是认为有关死,但我最后一次准备死亡故意写了一些会。 和那里去的人昨天有个喜欢的。 我甚至不知道阿纳托利读组有关帮我在Facebook的。 "Pravmir",发表我的信在论坛上,阿纳托利写道:"我们非常良好的部件,需要帮助。" 我认为一些nevezuchiy男人! 然后砰! 我愚蠢写遗嘱,然后将该人不知道,不要猜测:他有一个小孩、一个老婆...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打击。 我祈祷了很多第40天...
原谅我觉得癌症可以表现的不满、不信任、绝对和总不喜欢他。 我很想做出的权利要求他们的父母。 心理学家读了很多,我认为,在他们所有的错误和突然这个想法:"停止! 我25岁和我在试图责怪我妈妈我现在不好吗? 是甚至确定了吗?!"
我不得不重新评估的关系与亲戚,而且很严重。 我把玫瑰色的眼镜有关的事实,我现在将有所帮助,所有挤的。 因为在任何时候,可以是一个情况,帮助一些不会。 任何人可能不够,可能会背叛,但它并不因为他是个混蛋,但因为他只是一个男人。
我意识到如何努力,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父母。 我是这么认为:安德鲁,一个成年人将能生存,但不知怎么应付这种情况。 Zahara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安德鲁也是必要的要求首先,他认为男性。 关于我的父母还认为,成年人以某种方式需要生存。 当然,我看见我妈妈很难在某些时刻,但是仍然的情况是显然低估的。 把自己放在地方的父母,我理解它是如何努力,以及陷入这样的恐怖! 我是一个妈妈!
这是不容易原谅你自己。 这事发生在密集的护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愿望,我觉得之前开始。 记得我怎么进口电梯时,我看镜子,看着我是绝对不是我的眼睛,一些陌生人,非常强烈的...看到我。 我看见我自己,如果从外面,听内心的声音:我只是...
关于帮助如果你问的帮助,你应该做好准备,这将是困难的。 可能帮助不会有什么你期待开始。 人们并不像你想象的。 但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需要说"谢谢你"。
我没有写在Facebook"不要祈求我的健康。" 如果对健康的是,它将没有那些的话。 但是我意识到我是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我问你祈祷救赎痛苦和苦难,以避免的考验。
P.S.并记住,只要改变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www.pravmir.ru/katyusha-remizova-o-rake-smirenii-i-proshhen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