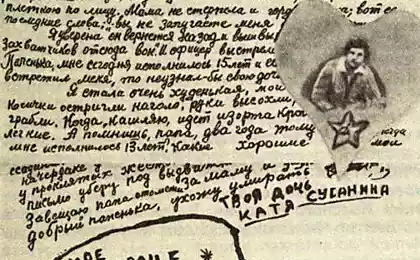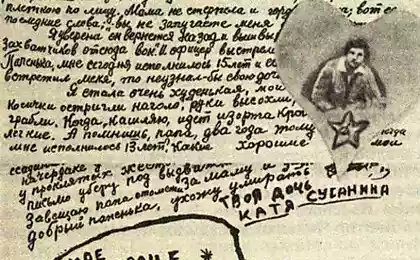981
最后一封信给他母亲的儿子
27052774
«这封信是不易折断,它 - 我的最后一次与你交谈,并穿越信,我终于离开你“.Ekaterina Savelievna葡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1941年母亲他写信给他,他被编入新的“生活与命运”维克多Shtrum的母亲的最后消息的告别信。
每个人都应该看它。这是母爱,刚毅的纪念碑和面对法西斯的恐怖。
- 维克多,我敢肯定,我的信会找到你,虽然我背后的前线和犹太人居住区的铁丝网后面。你的回答,我将永远不会,我不会。我想让你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容易,我要离开这个生活最后的日子。
人,维克多,是很难理解真的...七月十七德国人进了城。在城市公园电台播出新闻节目。我从医院去考虑生病后停下来听。阅读关于打击乌克兰的文章播音员。我听到远处的枪声,然后穿过花园的人跑了。我去的房子和所有想知道它是如何错过了空袭警报。突然,我看到一辆坦克,有人喊道:“不要撒慌”!“德国人突破了。”我说,前一天我来到了市议会的秘书,问他要离开。他很生气:“这是言之尚早,我们甚至没有列出”......总之,这是德国人。整个晚上,邻居相互访问,安静都有年幼的孩子和我。我决定 - 这是所有这将是我的。起初我很害怕,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你,我渴望再次见到你,亲吻你的额头,眼睛。然后我想 - 毕竟,你是安全的幸福
。
在早上,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感到了极度的悲痛。我在他的房间里,在他的床上,但感觉就像国外,少了一个。今天早上,我想起了被遗忘在岁月苏维埃政权,我是犹太人。德国人开着车,大声喊道:«!Juden kaputt»然后,我想起了这方面的一些我的邻居。看门人的妻子站在下我的窗口,并告诉邻居:“感谢上帝,犹太人结束”这是哪里?她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人,老妇人去看望她的儿子,告诉我她的孙子。矿山,一个寡妇,在6年的她的小女孩的邻居,Alyonushka,蓝色,美丽的眼睛,我会写它时,事情来找我,说:“安娜·谢苗诺夫娜,问你晚上来澄清事实,我得到了你的房间” 。 “好吧,那我就搬到你的” - 我说。她回答说,“不,你将进入衣柜了厨房。”我拒绝了:没有窗户,没有炉子。我去了诊所,当我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大门,我的房间爆发,在衣柜里我的东西堆。一位邻居告诉我:“我一直在沙发上,他仍然不会适合你的新的小房间里。”出人意料的是,她已经大学毕业,和她已故的丈夫是一个很好的和安静的人,在Ukopspilke会计师。 “你是一个非法的,” - 她的语气说,如果她是很赚钱的。而她的女儿Alyonushka整夜坐在我,我告诉她的故事。这是我的新家,她不想睡觉,母亲带着她在她的怀里。然后,Vitenka,我们的诊所重新开放,我和另外一个犹太医生辞退。我问钱工作的月份,但新的头对我说:“让你的斯大林支付你在苏联时期赢得了在莫斯科写” Maroussia护士轻轻抱住我,哭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愿意,你们会......”而特卡乔夫博士握着我的手。我不知道,这很难:幸灾乐祸,或怜悯的眼神看的模具,癞皮狗猫。我不认为我将不得不经历这一切。
很多人让我吃惊。而且不只是黑暗,愤怒,文盲。那老教师,退休了,这75年里,他总是问你,请转达问候,说你:“他是我们的骄傲。”而这几天你诅咒,已经见了我,说,你好,看向别处。然后,我被告知,他有一个会议的司令官的办公室说:“空气很干净,无异味大蒜。”为什么他 - 他的掠物中其实,这句话。而在对犹太人同一次会议上的诽谤是...但Vitenka,当然,不是所有的开会去了。许多人拒绝。而且,你知道,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沙皇时代反犹太主义与从人民的侵略主义相关的“天使长米迦勒的联盟。”在这里,我看到了 - 那些哭的犹太人从俄国,羞辱了德国人面前的救助,卑屈的可怜,准备出售俄罗斯三十块钱给德国。从郊区一个黑暗的人去抢劫,抓住公寓,毛毯,衣服;他们很可能是在霍乱暴乱杀害了医生。而且还有人精神萎靡,他们同意给整坏,只要他们不怀疑不同意当局。对我来说,不断使出熟悉的消息,所有的目光都为之疯狂,让人神志不清。有一个奇怪的表情 - “。perepryatyvat的事情”看来,一位邻居可靠。事情隐瞒想起比赛的我。不久,我们宣布犹太人的移民获准参加的东西15公斤。在墙壁上挂着zhёltenkieobyavlenitsa - “每个人都被邀请重新安置犹太人在旧城区不得迟于晚上1941年7月15日六点钟。外籍 - 出手»
。
好吧,Vitenka,和我收集的。我把枕头一个小床单,一个杯子,你也曾经给,勺子,刀,两个板块。多少钱你需要一个人吗?她拍了几张医疗器械。我把你的信,照片,死者的母亲和叔叔大卫,和一个你和爸爸拍摄,普希金的量,«Lettres日星期一红磨坊»,莫泊桑的体积与«一争»,词汇,把契诃夫,其中“一个无聊的故事”和“主教”。也就是说,原来,我充满了我的整个篮子里。我是这个屋檐下,你写信,好几个小时的夜晚怎么哭了,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寂寞。只是一个房子,花园,树下坐了几分钟,只是一个邻居。奇怪的安排了一些人。两个邻居,当我开始争论谁需要一把椅子,是谁写的表,并开始告别他们,无论是哭了。询问邻居Basanko如果战争结束后,你会知道关于我的,让他告诉我更多,我当时答应了。我摸着我的狗,杂种托比,昨晚不知何故特别恩待我。如果你来,你给她一个良好的心态老犹太女人。当我去的旅程,并认为,因为我拖车的老城区,突然来到我的病人Schukin阴郁,因为我认为,冷酷无情的人。他承诺会承担我的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这将是一周一次,使我食物的围栏。他在一家印刷厂,前面并没有采取眼病。战前,他对我,如果我必须列出人响应,纯洁的灵魂, - 我称之为几十个名字,而不是他。知道Vitenka,在他回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谁对我意味着不仅是一个院子里的狗可能受到人道对待。他告诉我,这个城市印刷厂印刷,犹太人被禁止走在人行道的顺序。他们都戴上了黄色的土地增值税在六五角星的形式。他们没有使用交通工具,浴场,参加门诊诊所,看电影,禁止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类,所有的蔬菜,不包括土豆权利。在市场购物是允许做的,晚上(当农民从市场中离开)刚过六时。老城区是封闭铁丝网,并且禁止线的输出,你只能押送强迫劳动。如果你发现一个犹太人在俄罗斯房子的主人 - 拍摄作为避难所的游击队。父亲休金,一个老农民谁来自附近的城镇Chudnova,看到自己的眼睛,所有当地犹太人赶进了树林中的节点和树干,从全天听到枪声和尖叫声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回来了。但是,德国人,谁是在公寓婆婆,来到深夜 - 喝醉了,还在喝酒,直到凌晨,当老人唱歌,胸针,戒指,手链之间共享。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随机的或任意预兆的命运等待着我们呢?
多么可悲是我的路,我的儿子,在中世纪的犹太人区。我走在城市附近,她在那里工作了20年。首先我们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蜡烛。但是,当我们去圣尼古拉斯,我看到几百人去这该死的贫民窟。这条街是白色的枕头的节点。患者在怀里。马古利斯博士的瘫痪父亲进行了毯子。一位年轻男子携带在他的怀里老女人,而他身后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加载的节点。杂货店的经理戈登,厚,呼吸急促,他就同一个毛领大衣,脸上的汗水流淌。他惊讶我一个年轻人,他就去了,没有东西往上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在他的面前,用傲慢和冷静的人。但是,如何接近是疯了,充满了恐惧。我们沿着人行道走着,站在人行道上,人们观看。有一次我去马古利斯,并听取了同情的叹息女性。而随着戈登在冬季大衣笑了,不过,相信我,这是可怕的,不好笑。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微微点头我说再见,其他人拒之门外。在我看来,在这个人群不是冷漠的眼睛;我们很好奇,是无情的,但几次我看到她泪痕的眼睛。
我看了看 - 两个人群,犹太人在一个大衣,帽子,女人温暖披肩,和第二的人群对穿着夏天的人行道上。薄外套,男人不夹克,有的在乌克兰绣花衬衫。在我看来,犹太人走在大街上,太阳已经拒绝闪耀,他们之间冰冷的十二月夜晚。在入口处的贫民窟,我告别了我的合作伙伴,他给我的铁丝网,在那里我们将满足的地方。知道Vitenka我经历过,一旦电线?我以为我感觉很糟糕。但是想象一下畜栏我才松了口气。我不认为,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奴隶的灵魂。第第在我的周围都是同样命运的人,而且在贫民窟,我不应该像一匹马,走在人行道上,并且在眼里无恶,熟悉的人看着我的眼睛,切忌不要跟我会面。这饲养场都打印出来,纳粹交付给我们,所以没有那么灼伤我的灵魂这印记。在这里,我不能感到无能为力牛和不幸的人。从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
我住在一位同事,斯珀林博士治疗师Mazanov房子两个小房间。斯珀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儿子,十二个男孩。我看他细长的脸和大眼睛伤心。他的名字是尤里,我两次打电话给他父亲和我,他纠正说:“我是汝拉,没有胜者”如何不同人物的人!斯珀林在他58年岁,是充满活力的。他拉住了床垫,煤油,柴草的车。到了晚上,有一个房子一袋面粉和豆类的半麻袋。他喜欢每一个他的成功作为一个新婚。昨天,他挂地毯。没事,没事,一切都会生存下来 - 他重复 - 最重要的是,囤积粮食和柴火。他告诉我,在贫民窟必须安排学校。他甚至还建议我给由良法的经验教训,并支付一节课碗汤。我答应了。斯珀林的妻子芬妮二厚,叹了一口气:“一切都失去了,我们都将丢失。”但在同一时间,它确保了她的大女儿柳芭,亲切和迷人的生物,没有给任何人一把豆子和面包片。而最年轻的,他的母亲,阿丽亚的最爱 - 一个真正的恶魔:霸气,多疑,小气。她尖叫她的父亲,她的妹妹。战前,她来看望莫斯科和坚持。我的上帝,有什么需要各地!如果这些话语财富的犹太人是谁,而且他们总是一直在积累,以备不时之需,看看我们的老城区。于是,他来了,下雨天,油墨不会发生。事实上,在老城区,不仅安置到15公斤行李,工匠们一直住在这里的老人,工作人员,护士。他们生活和生活多么可怕的痛苦。如何吃!你应该看到这些破旧不堪,挖洞进入地球小屋。 Vitenka,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穷人 - 贪婪,懦弱,狡猾,甚至准备出卖。有一个可怕的人,爱泼斯坦向我们走来了一个波兰小镇。他穿着他的袖子绷带,并且去与德国的搜索,参与审讯,醉与乌克兰警察,他们送他回家勒索伏特加,金钱,食物。我看见他好几次 - 高大英俊,穿着一身漂亮的奶油,甚至是黄色的徽章缝到他的夹克,看起来像一个黄色的菊花
。
但我想告诉你另一个。我从来不觉得犹太人。从小,我长大了其中的俄罗斯朋友,我喜欢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和发挥,这是我所有的观众席喊道以来,俄罗斯乡村医生的国会超过了所有的诗人,是“万尼亚舅舅”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一次,Vitenka当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我们一家人聚移民到南美。我告诉我的父亲:“不要从俄罗斯去任何地方,而淹没自己。”而没有离开。但是,在我的心脏这些可怕的日子充满了母性的感情犹太人民。之前,我不知道爱。她让我想起你,我亲爱的儿子爱我。我去生病在家。在一个小房间挤着数十人:半盲老人,婴儿,孕妇。我以前看的人类疾病症状的眼睛 - 青光眼,白内障。我现在让我无法直视人们的目光 - 在眼里,我看到了灵魂的唯一的一种体现。良好的灵魂Vitenka!悲伤和好,笑容和注定要失败的,击败了暴力,同时胜利结束暴力。强,维克多,灵魂!如果您听说过,有一些注意老人和妇女问我关于你的。如何热情地安慰我的人就是我不管什么不要抱怨,人的情况是可怕的我的。我有时想,我没有去的病人,反之亦然,国家好医生把我的灵魂。如何感人递给我一块面包进行治疗,洋葱,一把豆子。相信我,Vitenka是不收费的光临!当一个旧职员摇着我的手,把她的钱包两个或三个土豆,说道:“好了好了,医生,我求求你,”我的眼泪就他的眼睛。东西是一个纯粹的,慈父,很好,语言无法传达给你。我不想安慰你,很容易活这一次。你想知道我的心脏并没有从痛苦中爆炸。但是,不要劳动带来,我被饿死的思想,我为所有的时间都从来没饿。然而 - 我并不感到孤独。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别人,维克多?人们给我带来惊喜,有好有坏。他们是非常不同的,虽然所有人都经历着同样的命运。但想象一下,如果,在风暴期间,大部分尝试从雨躲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从雨以自己的方式隐藏...斯珀林博士确保犹太人的迫害临时直到战争。比如,因为它是很多,我看到,在人们更加乐观,所以他们心胸狭窄,自私的。如果你来在午餐有人奥亚和芬尼B.立即隐藏的食物。对我来说,斯珀林都不错,尤其是因为我吃了一点并把产品比他们消耗。但我决定离开他们,他们是不愉快的给我。我找了一个角落。在男人越悲伤,少他希望生存下去,所以它是更广泛,亲切,美好。穷人,锡匠,portnyagi,注定要死亡,这是更高尚,更广泛,更聪明谁比那些设法囤积一些食物。一位年轻的教师,曲柄,老教师和国际象棋斯皮尔伯格,安静的图书馆员,工程师Reivyčiai那无助的孩子,但是想武装贫民窟自制手雷 - 什么是美好的,不切实际的,可爱的,悲伤的,善良的人。在这里,我看到的希望几乎从未与心灵有关,它是 - 毫无意义,我认为它生下的本能。人,维克托,生活仿佛未来的岁月里。你可以不明白这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就是这个样子。我服从这一规律。在这里,两个女人就出城,并告诉同样的事情,我告诉我的朋友。德国在该地区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放过儿童,老人。谁推动了德国和警察,并采取了几十人在现场工作,他们挖壕沟,然后两三天内德国迫害犹太人口在这些沟渠和拍摄的所有投票。到处都在围绕我市农村种植这些犹太人的坟堆。在接下来的房子住来自波兰的女孩。她说,不断有杀害犹太人的切出每个人,和犹太人生存只有少数贫民窟 - 华沙,罗兹,拉多姆。
通过<一href="http://www.liveinternet.ru/users/670716/post273601218/">www.liveinternet.ru/users/670716/post273601218/
«这封信是不易折断,它 - 我的最后一次与你交谈,并穿越信,我终于离开你“.Ekaterina Savelievna葡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1941年母亲他写信给他,他被编入新的“生活与命运”维克多Shtrum的母亲的最后消息的告别信。
每个人都应该看它。这是母爱,刚毅的纪念碑和面对法西斯的恐怖。
- 维克多,我敢肯定,我的信会找到你,虽然我背后的前线和犹太人居住区的铁丝网后面。你的回答,我将永远不会,我不会。我想让你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容易,我要离开这个生活最后的日子。
人,维克多,是很难理解真的...七月十七德国人进了城。在城市公园电台播出新闻节目。我从医院去考虑生病后停下来听。阅读关于打击乌克兰的文章播音员。我听到远处的枪声,然后穿过花园的人跑了。我去的房子和所有想知道它是如何错过了空袭警报。突然,我看到一辆坦克,有人喊道:“不要撒慌”!“德国人突破了。”我说,前一天我来到了市议会的秘书,问他要离开。他很生气:“这是言之尚早,我们甚至没有列出”......总之,这是德国人。整个晚上,邻居相互访问,安静都有年幼的孩子和我。我决定 - 这是所有这将是我的。起初我很害怕,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你,我渴望再次见到你,亲吻你的额头,眼睛。然后我想 - 毕竟,你是安全的幸福
。
在早上,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感到了极度的悲痛。我在他的房间里,在他的床上,但感觉就像国外,少了一个。今天早上,我想起了被遗忘在岁月苏维埃政权,我是犹太人。德国人开着车,大声喊道:«!Juden kaputt»然后,我想起了这方面的一些我的邻居。看门人的妻子站在下我的窗口,并告诉邻居:“感谢上帝,犹太人结束”这是哪里?她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人,老妇人去看望她的儿子,告诉我她的孙子。矿山,一个寡妇,在6年的她的小女孩的邻居,Alyonushka,蓝色,美丽的眼睛,我会写它时,事情来找我,说:“安娜·谢苗诺夫娜,问你晚上来澄清事实,我得到了你的房间” 。 “好吧,那我就搬到你的” - 我说。她回答说,“不,你将进入衣柜了厨房。”我拒绝了:没有窗户,没有炉子。我去了诊所,当我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大门,我的房间爆发,在衣柜里我的东西堆。一位邻居告诉我:“我一直在沙发上,他仍然不会适合你的新的小房间里。”出人意料的是,她已经大学毕业,和她已故的丈夫是一个很好的和安静的人,在Ukopspilke会计师。 “你是一个非法的,” - 她的语气说,如果她是很赚钱的。而她的女儿Alyonushka整夜坐在我,我告诉她的故事。这是我的新家,她不想睡觉,母亲带着她在她的怀里。然后,Vitenka,我们的诊所重新开放,我和另外一个犹太医生辞退。我问钱工作的月份,但新的头对我说:“让你的斯大林支付你在苏联时期赢得了在莫斯科写” Maroussia护士轻轻抱住我,哭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愿意,你们会......”而特卡乔夫博士握着我的手。我不知道,这很难:幸灾乐祸,或怜悯的眼神看的模具,癞皮狗猫。我不认为我将不得不经历这一切。
很多人让我吃惊。而且不只是黑暗,愤怒,文盲。那老教师,退休了,这75年里,他总是问你,请转达问候,说你:“他是我们的骄傲。”而这几天你诅咒,已经见了我,说,你好,看向别处。然后,我被告知,他有一个会议的司令官的办公室说:“空气很干净,无异味大蒜。”为什么他 - 他的掠物中其实,这句话。而在对犹太人同一次会议上的诽谤是...但Vitenka,当然,不是所有的开会去了。许多人拒绝。而且,你知道,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沙皇时代反犹太主义与从人民的侵略主义相关的“天使长米迦勒的联盟。”在这里,我看到了 - 那些哭的犹太人从俄国,羞辱了德国人面前的救助,卑屈的可怜,准备出售俄罗斯三十块钱给德国。从郊区一个黑暗的人去抢劫,抓住公寓,毛毯,衣服;他们很可能是在霍乱暴乱杀害了医生。而且还有人精神萎靡,他们同意给整坏,只要他们不怀疑不同意当局。对我来说,不断使出熟悉的消息,所有的目光都为之疯狂,让人神志不清。有一个奇怪的表情 - “。perepryatyvat的事情”看来,一位邻居可靠。事情隐瞒想起比赛的我。不久,我们宣布犹太人的移民获准参加的东西15公斤。在墙壁上挂着zhёltenkieobyavlenitsa - “每个人都被邀请重新安置犹太人在旧城区不得迟于晚上1941年7月15日六点钟。外籍 - 出手»
。
好吧,Vitenka,和我收集的。我把枕头一个小床单,一个杯子,你也曾经给,勺子,刀,两个板块。多少钱你需要一个人吗?她拍了几张医疗器械。我把你的信,照片,死者的母亲和叔叔大卫,和一个你和爸爸拍摄,普希金的量,«Lettres日星期一红磨坊»,莫泊桑的体积与«一争»,词汇,把契诃夫,其中“一个无聊的故事”和“主教”。也就是说,原来,我充满了我的整个篮子里。我是这个屋檐下,你写信,好几个小时的夜晚怎么哭了,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寂寞。只是一个房子,花园,树下坐了几分钟,只是一个邻居。奇怪的安排了一些人。两个邻居,当我开始争论谁需要一把椅子,是谁写的表,并开始告别他们,无论是哭了。询问邻居Basanko如果战争结束后,你会知道关于我的,让他告诉我更多,我当时答应了。我摸着我的狗,杂种托比,昨晚不知何故特别恩待我。如果你来,你给她一个良好的心态老犹太女人。当我去的旅程,并认为,因为我拖车的老城区,突然来到我的病人Schukin阴郁,因为我认为,冷酷无情的人。他承诺会承担我的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这将是一周一次,使我食物的围栏。他在一家印刷厂,前面并没有采取眼病。战前,他对我,如果我必须列出人响应,纯洁的灵魂, - 我称之为几十个名字,而不是他。知道Vitenka,在他回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谁对我意味着不仅是一个院子里的狗可能受到人道对待。他告诉我,这个城市印刷厂印刷,犹太人被禁止走在人行道的顺序。他们都戴上了黄色的土地增值税在六五角星的形式。他们没有使用交通工具,浴场,参加门诊诊所,看电影,禁止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类,所有的蔬菜,不包括土豆权利。在市场购物是允许做的,晚上(当农民从市场中离开)刚过六时。老城区是封闭铁丝网,并且禁止线的输出,你只能押送强迫劳动。如果你发现一个犹太人在俄罗斯房子的主人 - 拍摄作为避难所的游击队。父亲休金,一个老农民谁来自附近的城镇Chudnova,看到自己的眼睛,所有当地犹太人赶进了树林中的节点和树干,从全天听到枪声和尖叫声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回来了。但是,德国人,谁是在公寓婆婆,来到深夜 - 喝醉了,还在喝酒,直到凌晨,当老人唱歌,胸针,戒指,手链之间共享。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随机的或任意预兆的命运等待着我们呢?
多么可悲是我的路,我的儿子,在中世纪的犹太人区。我走在城市附近,她在那里工作了20年。首先我们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蜡烛。但是,当我们去圣尼古拉斯,我看到几百人去这该死的贫民窟。这条街是白色的枕头的节点。患者在怀里。马古利斯博士的瘫痪父亲进行了毯子。一位年轻男子携带在他的怀里老女人,而他身后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加载的节点。杂货店的经理戈登,厚,呼吸急促,他就同一个毛领大衣,脸上的汗水流淌。他惊讶我一个年轻人,他就去了,没有东西往上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在他的面前,用傲慢和冷静的人。但是,如何接近是疯了,充满了恐惧。我们沿着人行道走着,站在人行道上,人们观看。有一次我去马古利斯,并听取了同情的叹息女性。而随着戈登在冬季大衣笑了,不过,相信我,这是可怕的,不好笑。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微微点头我说再见,其他人拒之门外。在我看来,在这个人群不是冷漠的眼睛;我们很好奇,是无情的,但几次我看到她泪痕的眼睛。
我看了看 - 两个人群,犹太人在一个大衣,帽子,女人温暖披肩,和第二的人群对穿着夏天的人行道上。薄外套,男人不夹克,有的在乌克兰绣花衬衫。在我看来,犹太人走在大街上,太阳已经拒绝闪耀,他们之间冰冷的十二月夜晚。在入口处的贫民窟,我告别了我的合作伙伴,他给我的铁丝网,在那里我们将满足的地方。知道Vitenka我经历过,一旦电线?我以为我感觉很糟糕。但是想象一下畜栏我才松了口气。我不认为,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奴隶的灵魂。第第在我的周围都是同样命运的人,而且在贫民窟,我不应该像一匹马,走在人行道上,并且在眼里无恶,熟悉的人看着我的眼睛,切忌不要跟我会面。这饲养场都打印出来,纳粹交付给我们,所以没有那么灼伤我的灵魂这印记。在这里,我不能感到无能为力牛和不幸的人。从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
我住在一位同事,斯珀林博士治疗师Mazanov房子两个小房间。斯珀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儿子,十二个男孩。我看他细长的脸和大眼睛伤心。他的名字是尤里,我两次打电话给他父亲和我,他纠正说:“我是汝拉,没有胜者”如何不同人物的人!斯珀林在他58年岁,是充满活力的。他拉住了床垫,煤油,柴草的车。到了晚上,有一个房子一袋面粉和豆类的半麻袋。他喜欢每一个他的成功作为一个新婚。昨天,他挂地毯。没事,没事,一切都会生存下来 - 他重复 - 最重要的是,囤积粮食和柴火。他告诉我,在贫民窟必须安排学校。他甚至还建议我给由良法的经验教训,并支付一节课碗汤。我答应了。斯珀林的妻子芬妮二厚,叹了一口气:“一切都失去了,我们都将丢失。”但在同一时间,它确保了她的大女儿柳芭,亲切和迷人的生物,没有给任何人一把豆子和面包片。而最年轻的,他的母亲,阿丽亚的最爱 - 一个真正的恶魔:霸气,多疑,小气。她尖叫她的父亲,她的妹妹。战前,她来看望莫斯科和坚持。我的上帝,有什么需要各地!如果这些话语财富的犹太人是谁,而且他们总是一直在积累,以备不时之需,看看我们的老城区。于是,他来了,下雨天,油墨不会发生。事实上,在老城区,不仅安置到15公斤行李,工匠们一直住在这里的老人,工作人员,护士。他们生活和生活多么可怕的痛苦。如何吃!你应该看到这些破旧不堪,挖洞进入地球小屋。 Vitenka,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穷人 - 贪婪,懦弱,狡猾,甚至准备出卖。有一个可怕的人,爱泼斯坦向我们走来了一个波兰小镇。他穿着他的袖子绷带,并且去与德国的搜索,参与审讯,醉与乌克兰警察,他们送他回家勒索伏特加,金钱,食物。我看见他好几次 - 高大英俊,穿着一身漂亮的奶油,甚至是黄色的徽章缝到他的夹克,看起来像一个黄色的菊花
。
但我想告诉你另一个。我从来不觉得犹太人。从小,我长大了其中的俄罗斯朋友,我喜欢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和发挥,这是我所有的观众席喊道以来,俄罗斯乡村医生的国会超过了所有的诗人,是“万尼亚舅舅”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一次,Vitenka当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我们一家人聚移民到南美。我告诉我的父亲:“不要从俄罗斯去任何地方,而淹没自己。”而没有离开。但是,在我的心脏这些可怕的日子充满了母性的感情犹太人民。之前,我不知道爱。她让我想起你,我亲爱的儿子爱我。我去生病在家。在一个小房间挤着数十人:半盲老人,婴儿,孕妇。我以前看的人类疾病症状的眼睛 - 青光眼,白内障。我现在让我无法直视人们的目光 - 在眼里,我看到了灵魂的唯一的一种体现。良好的灵魂Vitenka!悲伤和好,笑容和注定要失败的,击败了暴力,同时胜利结束暴力。强,维克多,灵魂!如果您听说过,有一些注意老人和妇女问我关于你的。如何热情地安慰我的人就是我不管什么不要抱怨,人的情况是可怕的我的。我有时想,我没有去的病人,反之亦然,国家好医生把我的灵魂。如何感人递给我一块面包进行治疗,洋葱,一把豆子。相信我,Vitenka是不收费的光临!当一个旧职员摇着我的手,把她的钱包两个或三个土豆,说道:“好了好了,医生,我求求你,”我的眼泪就他的眼睛。东西是一个纯粹的,慈父,很好,语言无法传达给你。我不想安慰你,很容易活这一次。你想知道我的心脏并没有从痛苦中爆炸。但是,不要劳动带来,我被饿死的思想,我为所有的时间都从来没饿。然而 - 我并不感到孤独。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别人,维克多?人们给我带来惊喜,有好有坏。他们是非常不同的,虽然所有人都经历着同样的命运。但想象一下,如果,在风暴期间,大部分尝试从雨躲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从雨以自己的方式隐藏...斯珀林博士确保犹太人的迫害临时直到战争。比如,因为它是很多,我看到,在人们更加乐观,所以他们心胸狭窄,自私的。如果你来在午餐有人奥亚和芬尼B.立即隐藏的食物。对我来说,斯珀林都不错,尤其是因为我吃了一点并把产品比他们消耗。但我决定离开他们,他们是不愉快的给我。我找了一个角落。在男人越悲伤,少他希望生存下去,所以它是更广泛,亲切,美好。穷人,锡匠,portnyagi,注定要死亡,这是更高尚,更广泛,更聪明谁比那些设法囤积一些食物。一位年轻的教师,曲柄,老教师和国际象棋斯皮尔伯格,安静的图书馆员,工程师Reivyčiai那无助的孩子,但是想武装贫民窟自制手雷 - 什么是美好的,不切实际的,可爱的,悲伤的,善良的人。在这里,我看到的希望几乎从未与心灵有关,它是 - 毫无意义,我认为它生下的本能。人,维克托,生活仿佛未来的岁月里。你可以不明白这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就是这个样子。我服从这一规律。在这里,两个女人就出城,并告诉同样的事情,我告诉我的朋友。德国在该地区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放过儿童,老人。谁推动了德国和警察,并采取了几十人在现场工作,他们挖壕沟,然后两三天内德国迫害犹太人口在这些沟渠和拍摄的所有投票。到处都在围绕我市农村种植这些犹太人的坟堆。在接下来的房子住来自波兰的女孩。她说,不断有杀害犹太人的切出每个人,和犹太人生存只有少数贫民窟 - 华沙,罗兹,拉多姆。
通过<一href="http://www.liveinternet.ru/users/670716/post273601218/">www.liveinternet.ru/users/670716/post2736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