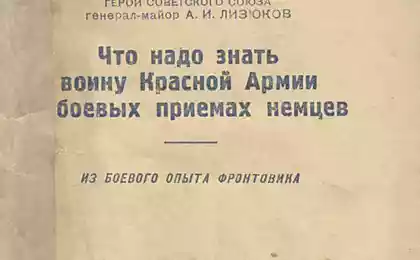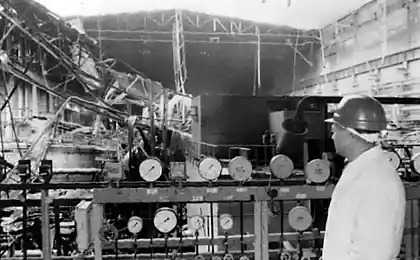998
德军在苏联囚禁
原谅的能力是独特的俄罗斯。然而,如何属性影响的灵魂 - 尤其是当你从昨天的敌人嘴唇听到它...
快报战争前德国战俘。
我属于那种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在1943年7月,我成为了国防军的士兵,但由于长期的训练只有在1945年1月,这在当时举行了东普鲁士的领土来到德苏前面。随后德国军队不得不在抵抗苏联军队没有机会。 1945年3月26日我在苏联囚禁。我在科里 - Jarve爱沙尼亚营地,在维诺格拉多夫在莫斯科,他在一家煤矿Stalinogorsk(今 - 新莫斯科斯克)。
下切续...

我们总是被当作人对待。我们能够休闲中心,医疗服务是提供给我们。 1949年11月2日,经过4,5年来囚禁,我被释放,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释放。我知道,不像我在苏联囚禁的经验,在德国的苏联战俘,过着非常不同。希特勒对待广大苏联战俘是非常残酷的。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如既往地是德国,有这么多著名诗人,作曲家和学者,这样的待遇是不人道的,可耻的行为。回国后,战争的许多前苏联的囚犯等待来自德国的赔偿,但没有等到。这是特别离谱!我希望我的微薄捐赠我发来缓解这种精神伤害一个小的贡献。
汉斯Moezer
五十年前,于21 1945年4月,在激烈的战斗在柏林,我陷入了苏军俘虏。此日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情况是为最为重要的我后来的生活。如今,半个世纪后,我回头看,现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主题已经自己
。
由我囚禁的日子,我刚刚度过了自己十七岁生日。通过劳工阵线,我们被召集到国防军,并名列第12军,即所谓的“军鬼”。 4月16日之后,1945年苏联红军发起了“操作”柏林“,”我们是从字面上抛向前方。
捕获对我来说,我的青年同志的强烈震撼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完全措手不及。而任何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种震荡也是因为如此沉重,只有一次为苏联前线,我们实现了我们小组所遭受的损失的严重程度。出百人加入了战斗在早上,中午前,死亡人数超过一半。这些经验是我生命中的痛苦回忆。
其次,形成列车战俘,谁把我们 - 与众多的中间站 - 深入到苏联,伏尔加河上。该国需要在劳动力德军俘虏,因为是处于非活动状态在战争植株恢复工作。在萨拉托夫,美丽的城市伏尔加高的银行,又赚了一个锯木厂,并在“水泥城”沃尔斯基也坐落在河的大银行,我用了一年多。
我们劳教所属于水泥厂“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工作一直对我来说,未受过训练的18年高中生,异常严重。德国“kamerady”因此并不总是帮助。人们只是需要生存,活到被遣送回国。在这一努力在营德军俘虏都开发了自己,往往残酷规律。
1947年2月,我有一个意外的采石场,在这之后我不再能工作。半年后,我回到家里在德国禁止。
这种情况下的唯一的外侧。期间,他在萨拉托夫和沃利斯克逗留然后条件非常困难。这些条件往往是在苏联的战争的德国战俘的出版物中所描述:饥饿和工作。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作用也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在夏天,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异常炎热,我不得不从炽热的炉渣铲水泥厂;在冬天,当它是非常冷的,我是工作在夜班采石场。
我想,你把我留在苏联阵营,在此之前描述的股票仍是一些经验丰富圈养。而且有许多的印象。我只举其中的几个。
首先 - 这是自然,雄伟的伏尔加沿着这是我们从训练营到工厂游行的每一天。这个庞大的河流印象,俄罗斯河流的妈妈都很难形容。有一年夏天,当大潮后江被广泛地推出自己的海域,我们的俄罗斯后卫让我们跳进河里洗了水泥粉尘。当然,“官员”采取行动打击的同时规则;但他们也都是人,我们交换了香烟,他们比我大一点。
十月份,我们开始了冬季风暴,并月中瘫痪河冰覆盖。在冰冻的河柏油路,连车也可以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然后,在四月中旬,囚禁半年后,冰,伏尔加自由再传捷报:可怕的轰鸣声打破了僵局,河水回到它的老渠道。我们的俄罗斯侍卫们喜出望外:“这条河再流!”过年的时候开始
。
回忆第二部分 - 与苏联人的关系。我已经描述为人性化是我们的警卫。我每天早上可以给你怜悯的其他例子,例如,在激烈的寒冷一名护士,站在营地的大门。谁没有足够的衣服守护使冬季留在营地,尽管营当局的抗议。或者一个犹太医生救了一个以上的德国人的生活,虽然他们来为敌人的医院。最后,在在沃利斯克站午休一老妇谁,羞涩地给我们从他的桶泡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盛宴。后来,再移动,她去了,越过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罗斯 - 妈妈,我遇到了斯大林后期,1946年,在伏尔加河。
当今天,我捕捉五十年后,我试着总结一下,我们发现,圈养把我完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方向,并定义了我的职业生涯。
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男子在俄罗斯的经历不会让我和他返回德国之后。我有一个选择 - 从内存中偷了我的青春打跑,并不会想到苏联,或分析所有的经验,从而带来一定的传记平衡。我选的第二个,无比艰难的道路,至少不是在我的博士工作保罗·约翰森的上司的影响。
正如在一开始,这种艰辛的道路我看现在。我思考所取得的成就,并说明如下:几十年来在我的讲座我想传达给我的学生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经验给予了热烈的回应。最近的弟子,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合格的博士后工作和考试。最后,我系着俄罗斯的同事们,尤其是在圣彼得堡,长期接触,最终成长为一个持久的友谊。
克劳斯·梅耶
1945年5月8日投降的德国第18军在库尔兰大锅在拉脱维亚的残余。这是期待已久的一天。我们的小100瓦登发射器被设计在投降条款与红军谈判。所有的武器,装备,交通运输,radioavtomobili自己radostantsii是,根据普鲁士精心组装在一个地方,在被松树环绕的地方。这两天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随后而来的苏联军官,并带着我们在二层楼房。我们花了一晚上在狭小的空间上的草垫。早在5月11日上午,我们是建立在数以百计,考虑如何岁,他们的公司的分布情况。它开始徒步行军到圈养。
红军战士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因此,我们走在里加编写的红军巨大的预制营地的方向。有官员从普通士兵分开。卫队搜查采取的东西。我们被允许离开了一些内衣,袜子,毛毯,陶器和餐具折叠。仅此而已。
从里加我们走直到一天是无尽的游行到东部,到前苏联拉脱维亚边境的方向Dunaburg。每年三月后,我们到达了下一个营地。仪式重复:搜索个人物品,食品,夜间睡眠的分布。在抵达Dunaburg我们被装入货车车厢。食物是很好的:面包和美国肉类罐头«咸牛肉»。我们去了东南。这些筝认为,我们要回家了,很惊讶。过了多日,我们来到了莫斯科的波罗的海车站。 Sotya卡车,我们proezali的城市。天已经黑了。食物是我们中的一个能够做一些记录。
远离城市靠近村庄,由一座三层的木制房屋,有一个大的组装阵营如此之大,它的郊区丢失在地平线上。帐篷和囚犯......通过具有良好的夏季天气,俄罗斯和美国的罐头面包一个星期。经过150至200名囚犯一上午电话与其余分离。我们坐在卡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在西北部的路径所在。我们驱车经过大坝一白桦林最后公里。两小时一趟的地方(或更长?)后,我们的目标。
森林营由三个或四个木制的营房,部分位于地面上的水平。门是位于几个步骤下来的水平低。在他住在东普鲁士的德国营地指挥官最后的小屋是裁缝和鞋匠,医生的办公室,并为患者单独兵营的前提。整个面积仅比一个足球场大,被围栏用铁丝网。旨在保护多一点舒适的木制营房。在境内也有一个展台,观看和一个小厨房。这个地方是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成为我们新的家园。在提示符下返回家园这是不可能的。
在barakak沿着中央走道拉伸两排木制双层铺位。在完成注册手续困难(我们没有与我们的士兵的书有)完成后,我们放在装满稻草床垫的长凳。位于顶层可以得到幸运。他能看出来到玻璃窗大小像25×25厘米。
正是在6:00是呈上升趋势。然后,所有跑到洗脸盆。在约1海拔70仪器从锡排水沟,smotrirovanny木支持。水位下降约肚子。在当时没有霜冻的几个月里,上水库就满了水。用于洗涤不得不把一个简单的阀门,之后将水倒入或滴在他的头部和上身。完成此过程重复操场上每天点名。在完全7:00,我们走到周围的营地登录无尽的白桦林。我不记得我不得不削减一些其他的树,除了桦木。
在现场,我们都在等待我们的“老板”,民间平民监督员。他们分发工具:锯和斧头。创建三个组:两名囚犯砍伐树木,第三收集树叶和不必要的分支机构一大堆,然后烧掉。特别是在潮湿的天气,这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当然,每个囚犯较轻。随着勺子,它可能是人工饲养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只有小时的努力后,使用由火石,灯芯一块铁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象可能点燃从雨树烂往往是。木材焚烧适用于每天的房费。该规范本身包括了砍伐木材两米堆成一堆。每个木残端必须是两米长和至少10厘米的直径。有了这样原始的工具,如钝锯和斧头,往往仅由几个常见的铁件焊接在一起,几乎无法履行的规范。
工作堆爬上树后,“酋长”,并装载到敞篷卡车。在下午的工作被迫中断半小时。我们得到了水样白菜汤。这些谁可以执行正常的晚上,除了200克湿面包,不过口感好,糖和Zhmenya烟草一汤匙通常比获得,甚至粥直(由于勤奋和营养不良的成功只是一点点)以覆盖锅。一个“平静”:我们守卫的力量也好不到哪去
。
冬季1945/46两年。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棉花衣服和靴子沃兹停止了。我们砍伐树木,把他们在一个短的时刻,当温度不低于零下20度左右。如果天气变冷,所有的犯人都在营地。
一个月一两次已经觉醒在夜间进行。我们从草垫子站起来,开着车到车站,到了10公里左右。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林。这是我们倒下的树木。木有有盖的货车被加载并发送图什诺莫斯科附近。山林激励我们以抑郁和恐惧的状态。我们只好把山上移动。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是持币观望?如何它会持续多久?这一夜,似乎没有尽头给我们。而当这一天车都满载。这项工作是单调乏味的。两名男子在六英尺长的树干肩膀抬到车上,然后就推它,而不在车内的开门电梯。两个特别强的囚犯在大宗木材堆放在车内。这款车充满。未来汽车的转向。我们覆盖在一个高杆的焦点。它是一种超现实:树干的阴影和爬行像一些梦幻般的翅膀的生物囚犯。如果坠落到地面太阳的第一缕曙光,我们走回了营地。这一天对我们来说这个周末。
一月份晚上在1946年我特别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弗罗斯特是如此强烈,在手术后无法启动车辆的发动机。我们必须走在冰10或从营地12公里。满月照亮我们。 A组50-60囚犯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彼此移开。我无法辨别眼前这个人。我认为这是结束。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我还是设法到达营地。
Lesopoval。日复一日。无尽寒冬。越来越多的犯人感到精神压抑。拯救被记录在“之旅。”因此,我们呼吁在附近的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工作。锄头和铁锹,我们挑选出的冻土土豆或甜菜。许多无法收集。但还是收集演变成一个锅加热。代替水使用的融雪。我们的后卫在吃煮熟的我们。没有什么是扔掉。清洁云集秘密从督察的入口处,营地席卷领土和获得在军营晚上面包和糖pozharivalis上的两个烧红的铁炉子后。这是一种在黑暗中“狂欢节”的食品。大多数当时的囚犯已经睡着了。而我们坐,浸泡疲惫的身体就像一个温暖甜蜜的糖浆。
当我看到从过去几年的高度所经过的时间,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和行不通的,在苏联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东西作为德国人的仇恨任何地方。它是惊人的。毕竟,我们是德军俘虏的人,谁好几个世纪两次陷入俄罗斯陷入战争的代表。第二次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暴力,恐怖和犯罪方面。如果有任何收费的迹象,他们从来没有被“集体”,给所有的德国人民。
1946年5月上旬,我在农场的一个工作组中的战争30名囚犯从我们的营地。龙强,近来成长树干,用于住房建设对货车熟加载。然后它发生了。树干进行的肩膀上。我是在“错误”的一面。当装载桶到卡车后面,我的头两个箱子之间的挤压。我昏迷倒卧在机器的背面。从耳,口和鼻出血。卡车把我带回到了营地。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拒绝。这时,我想起什么。
该营地的医生,奥地利,是纳粹。这都知道。他没有必要的药品和包扎材料。他唯一的工具是指甲剪。医生马上说:“颅底骨折。
资料来源:
快报战争前德国战俘。
我属于那种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在1943年7月,我成为了国防军的士兵,但由于长期的训练只有在1945年1月,这在当时举行了东普鲁士的领土来到德苏前面。随后德国军队不得不在抵抗苏联军队没有机会。 1945年3月26日我在苏联囚禁。我在科里 - Jarve爱沙尼亚营地,在维诺格拉多夫在莫斯科,他在一家煤矿Stalinogorsk(今 - 新莫斯科斯克)。
下切续...

我们总是被当作人对待。我们能够休闲中心,医疗服务是提供给我们。 1949年11月2日,经过4,5年来囚禁,我被释放,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释放。我知道,不像我在苏联囚禁的经验,在德国的苏联战俘,过着非常不同。希特勒对待广大苏联战俘是非常残酷的。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如既往地是德国,有这么多著名诗人,作曲家和学者,这样的待遇是不人道的,可耻的行为。回国后,战争的许多前苏联的囚犯等待来自德国的赔偿,但没有等到。这是特别离谱!我希望我的微薄捐赠我发来缓解这种精神伤害一个小的贡献。
汉斯Moezer
五十年前,于21 1945年4月,在激烈的战斗在柏林,我陷入了苏军俘虏。此日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情况是为最为重要的我后来的生活。如今,半个世纪后,我回头看,现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主题已经自己
。
由我囚禁的日子,我刚刚度过了自己十七岁生日。通过劳工阵线,我们被召集到国防军,并名列第12军,即所谓的“军鬼”。 4月16日之后,1945年苏联红军发起了“操作”柏林“,”我们是从字面上抛向前方。
捕获对我来说,我的青年同志的强烈震撼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完全措手不及。而任何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种震荡也是因为如此沉重,只有一次为苏联前线,我们实现了我们小组所遭受的损失的严重程度。出百人加入了战斗在早上,中午前,死亡人数超过一半。这些经验是我生命中的痛苦回忆。
其次,形成列车战俘,谁把我们 - 与众多的中间站 - 深入到苏联,伏尔加河上。该国需要在劳动力德军俘虏,因为是处于非活动状态在战争植株恢复工作。在萨拉托夫,美丽的城市伏尔加高的银行,又赚了一个锯木厂,并在“水泥城”沃尔斯基也坐落在河的大银行,我用了一年多。
我们劳教所属于水泥厂“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工作一直对我来说,未受过训练的18年高中生,异常严重。德国“kamerady”因此并不总是帮助。人们只是需要生存,活到被遣送回国。在这一努力在营德军俘虏都开发了自己,往往残酷规律。
1947年2月,我有一个意外的采石场,在这之后我不再能工作。半年后,我回到家里在德国禁止。
这种情况下的唯一的外侧。期间,他在萨拉托夫和沃利斯克逗留然后条件非常困难。这些条件往往是在苏联的战争的德国战俘的出版物中所描述:饥饿和工作。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作用也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在夏天,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异常炎热,我不得不从炽热的炉渣铲水泥厂;在冬天,当它是非常冷的,我是工作在夜班采石场。
我想,你把我留在苏联阵营,在此之前描述的股票仍是一些经验丰富圈养。而且有许多的印象。我只举其中的几个。
首先 - 这是自然,雄伟的伏尔加沿着这是我们从训练营到工厂游行的每一天。这个庞大的河流印象,俄罗斯河流的妈妈都很难形容。有一年夏天,当大潮后江被广泛地推出自己的海域,我们的俄罗斯后卫让我们跳进河里洗了水泥粉尘。当然,“官员”采取行动打击的同时规则;但他们也都是人,我们交换了香烟,他们比我大一点。
十月份,我们开始了冬季风暴,并月中瘫痪河冰覆盖。在冰冻的河柏油路,连车也可以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然后,在四月中旬,囚禁半年后,冰,伏尔加自由再传捷报:可怕的轰鸣声打破了僵局,河水回到它的老渠道。我们的俄罗斯侍卫们喜出望外:“这条河再流!”过年的时候开始
。
回忆第二部分 - 与苏联人的关系。我已经描述为人性化是我们的警卫。我每天早上可以给你怜悯的其他例子,例如,在激烈的寒冷一名护士,站在营地的大门。谁没有足够的衣服守护使冬季留在营地,尽管营当局的抗议。或者一个犹太医生救了一个以上的德国人的生活,虽然他们来为敌人的医院。最后,在在沃利斯克站午休一老妇谁,羞涩地给我们从他的桶泡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盛宴。后来,再移动,她去了,越过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罗斯 - 妈妈,我遇到了斯大林后期,1946年,在伏尔加河。
当今天,我捕捉五十年后,我试着总结一下,我们发现,圈养把我完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方向,并定义了我的职业生涯。
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男子在俄罗斯的经历不会让我和他返回德国之后。我有一个选择 - 从内存中偷了我的青春打跑,并不会想到苏联,或分析所有的经验,从而带来一定的传记平衡。我选的第二个,无比艰难的道路,至少不是在我的博士工作保罗·约翰森的上司的影响。
正如在一开始,这种艰辛的道路我看现在。我思考所取得的成就,并说明如下:几十年来在我的讲座我想传达给我的学生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经验给予了热烈的回应。最近的弟子,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合格的博士后工作和考试。最后,我系着俄罗斯的同事们,尤其是在圣彼得堡,长期接触,最终成长为一个持久的友谊。
克劳斯·梅耶
1945年5月8日投降的德国第18军在库尔兰大锅在拉脱维亚的残余。这是期待已久的一天。我们的小100瓦登发射器被设计在投降条款与红军谈判。所有的武器,装备,交通运输,radioavtomobili自己radostantsii是,根据普鲁士精心组装在一个地方,在被松树环绕的地方。这两天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随后而来的苏联军官,并带着我们在二层楼房。我们花了一晚上在狭小的空间上的草垫。早在5月11日上午,我们是建立在数以百计,考虑如何岁,他们的公司的分布情况。它开始徒步行军到圈养。
红军战士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因此,我们走在里加编写的红军巨大的预制营地的方向。有官员从普通士兵分开。卫队搜查采取的东西。我们被允许离开了一些内衣,袜子,毛毯,陶器和餐具折叠。仅此而已。
从里加我们走直到一天是无尽的游行到东部,到前苏联拉脱维亚边境的方向Dunaburg。每年三月后,我们到达了下一个营地。仪式重复:搜索个人物品,食品,夜间睡眠的分布。在抵达Dunaburg我们被装入货车车厢。食物是很好的:面包和美国肉类罐头«咸牛肉»。我们去了东南。这些筝认为,我们要回家了,很惊讶。过了多日,我们来到了莫斯科的波罗的海车站。 Sotya卡车,我们proezali的城市。天已经黑了。食物是我们中的一个能够做一些记录。
远离城市靠近村庄,由一座三层的木制房屋,有一个大的组装阵营如此之大,它的郊区丢失在地平线上。帐篷和囚犯......通过具有良好的夏季天气,俄罗斯和美国的罐头面包一个星期。经过150至200名囚犯一上午电话与其余分离。我们坐在卡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在西北部的路径所在。我们驱车经过大坝一白桦林最后公里。两小时一趟的地方(或更长?)后,我们的目标。
森林营由三个或四个木制的营房,部分位于地面上的水平。门是位于几个步骤下来的水平低。在他住在东普鲁士的德国营地指挥官最后的小屋是裁缝和鞋匠,医生的办公室,并为患者单独兵营的前提。整个面积仅比一个足球场大,被围栏用铁丝网。旨在保护多一点舒适的木制营房。在境内也有一个展台,观看和一个小厨房。这个地方是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成为我们新的家园。在提示符下返回家园这是不可能的。
在barakak沿着中央走道拉伸两排木制双层铺位。在完成注册手续困难(我们没有与我们的士兵的书有)完成后,我们放在装满稻草床垫的长凳。位于顶层可以得到幸运。他能看出来到玻璃窗大小像25×25厘米。
正是在6:00是呈上升趋势。然后,所有跑到洗脸盆。在约1海拔70仪器从锡排水沟,smotrirovanny木支持。水位下降约肚子。在当时没有霜冻的几个月里,上水库就满了水。用于洗涤不得不把一个简单的阀门,之后将水倒入或滴在他的头部和上身。完成此过程重复操场上每天点名。在完全7:00,我们走到周围的营地登录无尽的白桦林。我不记得我不得不削减一些其他的树,除了桦木。
在现场,我们都在等待我们的“老板”,民间平民监督员。他们分发工具:锯和斧头。创建三个组:两名囚犯砍伐树木,第三收集树叶和不必要的分支机构一大堆,然后烧掉。特别是在潮湿的天气,这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当然,每个囚犯较轻。随着勺子,它可能是人工饲养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只有小时的努力后,使用由火石,灯芯一块铁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象可能点燃从雨树烂往往是。木材焚烧适用于每天的房费。该规范本身包括了砍伐木材两米堆成一堆。每个木残端必须是两米长和至少10厘米的直径。有了这样原始的工具,如钝锯和斧头,往往仅由几个常见的铁件焊接在一起,几乎无法履行的规范。
工作堆爬上树后,“酋长”,并装载到敞篷卡车。在下午的工作被迫中断半小时。我们得到了水样白菜汤。这些谁可以执行正常的晚上,除了200克湿面包,不过口感好,糖和Zhmenya烟草一汤匙通常比获得,甚至粥直(由于勤奋和营养不良的成功只是一点点)以覆盖锅。一个“平静”:我们守卫的力量也好不到哪去
。
冬季1945/46两年。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棉花衣服和靴子沃兹停止了。我们砍伐树木,把他们在一个短的时刻,当温度不低于零下20度左右。如果天气变冷,所有的犯人都在营地。
一个月一两次已经觉醒在夜间进行。我们从草垫子站起来,开着车到车站,到了10公里左右。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林。这是我们倒下的树木。木有有盖的货车被加载并发送图什诺莫斯科附近。山林激励我们以抑郁和恐惧的状态。我们只好把山上移动。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是持币观望?如何它会持续多久?这一夜,似乎没有尽头给我们。而当这一天车都满载。这项工作是单调乏味的。两名男子在六英尺长的树干肩膀抬到车上,然后就推它,而不在车内的开门电梯。两个特别强的囚犯在大宗木材堆放在车内。这款车充满。未来汽车的转向。我们覆盖在一个高杆的焦点。它是一种超现实:树干的阴影和爬行像一些梦幻般的翅膀的生物囚犯。如果坠落到地面太阳的第一缕曙光,我们走回了营地。这一天对我们来说这个周末。
一月份晚上在1946年我特别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弗罗斯特是如此强烈,在手术后无法启动车辆的发动机。我们必须走在冰10或从营地12公里。满月照亮我们。 A组50-60囚犯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彼此移开。我无法辨别眼前这个人。我认为这是结束。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我还是设法到达营地。
Lesopoval。日复一日。无尽寒冬。越来越多的犯人感到精神压抑。拯救被记录在“之旅。”因此,我们呼吁在附近的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工作。锄头和铁锹,我们挑选出的冻土土豆或甜菜。许多无法收集。但还是收集演变成一个锅加热。代替水使用的融雪。我们的后卫在吃煮熟的我们。没有什么是扔掉。清洁云集秘密从督察的入口处,营地席卷领土和获得在军营晚上面包和糖pozharivalis上的两个烧红的铁炉子后。这是一种在黑暗中“狂欢节”的食品。大多数当时的囚犯已经睡着了。而我们坐,浸泡疲惫的身体就像一个温暖甜蜜的糖浆。
当我看到从过去几年的高度所经过的时间,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和行不通的,在苏联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东西作为德国人的仇恨任何地方。它是惊人的。毕竟,我们是德军俘虏的人,谁好几个世纪两次陷入俄罗斯陷入战争的代表。第二次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暴力,恐怖和犯罪方面。如果有任何收费的迹象,他们从来没有被“集体”,给所有的德国人民。
1946年5月上旬,我在农场的一个工作组中的战争30名囚犯从我们的营地。龙强,近来成长树干,用于住房建设对货车熟加载。然后它发生了。树干进行的肩膀上。我是在“错误”的一面。当装载桶到卡车后面,我的头两个箱子之间的挤压。我昏迷倒卧在机器的背面。从耳,口和鼻出血。卡车把我带回到了营地。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拒绝。这时,我想起什么。
该营地的医生,奥地利,是纳粹。这都知道。他没有必要的药品和包扎材料。他唯一的工具是指甲剪。医生马上说:“颅底骨折。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