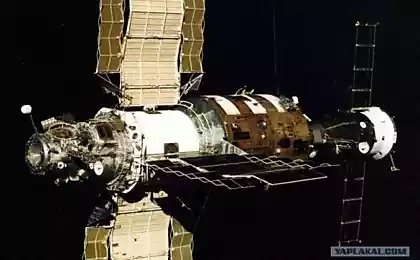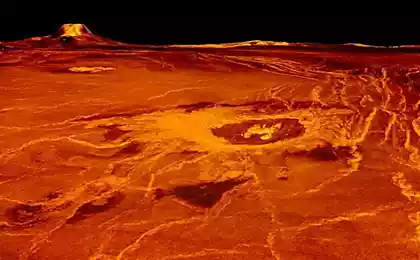703
下面我正在朝着地球
我下面的地面上移动
春天伊琳娜Suvorova Efimovna好运气。其中前护士疗养院火车站谢尔加奇住自1978年以来的房子,有一个新的屋顶。现在,他是在列宁大街最明显。众议院Suvorova看起来还是聪明的,像9月1日的学生。修复了程序,提高铁路工人的生活条件下,由高尔基铁路 - 战争的成员和退伍军人
虽然这已过期快一年了,伊琳娜Efimovna都不能平静下来。几乎没有,他回忆自己的幸福。然后,他开始感谢。女人在一个新的屋顶由“有罪”的名字的详细列表。在这里,一切从耶和华神对高尔基路雷川,谁亲自祝贺苏沃洛夫胜利日的首领。
在这个女人的记忆令人羡慕。她清楚地记得四分之三通过它走了一个世纪的可怕细节。例如,前40几分钟后我们的会议,她告诉我怎么她的儿子去看望义务兵1977年10月3日。什么模式是Polotenchik在士兵的食堂。他们洗过的杯子她的女儿。而他们带来了他们的好东西 - 对待同胞的儿子。而如何将其他的“聪明绝顶”的父母试图进行在塑料袋伏特加境内瞒着警惕检查,但没有工作...
但是,当伊琳娜Efimovna回忆松针,桤木耳环配方煎液,并告诉如何有吸桦叶求生布痕瓦尔德,有人则增长到椅子上,不再明白为什么外界这么安静下雪,靠近文化之家的灯安详地漂浮在暮光之城,走出去。
[下一页]
在1941年8月,她十二岁。然后,她住在一起,她的母亲和姐姐在白俄罗斯,Rechitsa区。哥哥 - 远东,姐姐 - 在利沃夫。这是很难想象德国人第一次,她只看到了第二个春天42。在此之前,村里Kuzmino它们不会出现。没有必要,而在春季和秋季kuzmintsy住在岛上,切断与外界盆满钵满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的支流。在夏季,通过沼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传球,冬季雪到他的腰部。人们躲到了船,切断所有的狗,以免发出响声,住谣言。德国人的居民,焚烧,毒害井射击村地区,共同提高。最后,在5月达成和库兹明。
- 我们去了房子的两名军官走了一圈房间里,我的姐姐也没注意, - 伊琳娜Efimovna说。 - 认为他的上司找到一个公寓,但房子太小
。 - ?你怎么理解这个
- 德国知道
。 - 在哪里?
在村里,我们有两个人从德国俘虏的德国妇女,妻子第一次战争结束后归还,他们的子女讲的语言。在学校里,我们教给德国犹太人。我简单易学......他们去了,和德国之后扔。他们从房子漫游到的房子,花了一切,甚至衣服。牛削减和左 - 沉默...
我们的董事长说,这是一次对我们在森林里。我们开始离开。主席 - 游击队司令。而我们的森林Kerbitsky知道吗?在这里,您将进入 - 刚出门沃罗涅日。孩子们给了主席的叛徒,他们被射中的目标,妻子疯了前面,流浪街头和嚎叫,他回到村里,并死在那里。他是个好人。我们实际上是父亲留下的房子卖了,开走了到乌拉尔“二十五Thousander”集体组织,而主席,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房子...
而我与游击队。我去调查。他的穿着乞丐 - 和乡村施舍。有时几周村与村,和Holmichi和Rechitsa和布拉金。甚至在乌克兰。小男孩和我一起发布的,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们要求面包和条件看,听,但被安排作为一个德国人,什么号码以及如何最好地接近他。我们花了一晚上就在shalashika党派点的森林。一个Khomich等城市,我们有在那里连接的公寓。我们从来不写任何东西,一切都只是一个信物。之后,我们和桥梁破坏和破坏火车开动起来......
很多事情看到的。对于Holmichami5公里 - 深谷。我们只是回到通过它和背部 - 不了解,不认识的地方。没有山沟。一个场。来吧,和地底下的摇摆我们。我说 - 地震了!在精神跑到森林,吓人,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但是,在山沟里的东西不见了?!指挥官告诉我他:
- 嘿,伙计们,在犹太人的山沟德国人活埋。而由于土地被移动在山沟转身。
我提供的伏特加喝一杯,在来了,而我却没有。三天也就不会......
然后,我被送到了乌克兰。两个坐了下来之前,我可以传达信息,并在RAID三分命中。没办法了,狗领着我们到卢茨克,然后装到卡车,送往德国。所有的犹太人都还在路上某处波兰下降的。和其他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孩子们住在独立的军营。每天早晨,那些谁不上升到他的脚下,他可以在卡车上被带走并烧毁。但我们有一个小的犹太人保存。他是一个德国人,因为我们得到的,目前尚不清楚。而这对他的护士长没有出现,我们有他的头洗桦树叶子煎服。于是他就成了黑头发的花斑。
巴拉克站在森林和森林就像家里给我靠近。我搜集各种草药 - Lungwort,蓍草,与桤木耳环,松针,酿造,和我们喝。但是,他们的胃抢救和存活。
我有点相信活着。还有人跟我一样,Zdorovenki,12人。房间就在眼前,我们没有把拍摄他们的士兵二百克,喂糖水补血。我相信,才能生存下来。然后在轰炸开始。一天早晨,早在4月45,护士长自己放我们走。他们说去,无论你想。所以,去没有人能 - 已扩散在不同方向tarakanchiki
。
我看到在一个草垛谷仓山农场抓取和手表 - 狗。闻我,他走了过来,坐了下来。不象我们在训练营:不要急于和看守,所以我也没有出来。到了晚上,主人回来,德语。我以为他是我的投降,并在框中他自己的外套,并把我扔进率领的房子。有情妇说,在这里,他们说,你带那个女孩那里。她询问是否有人看到。没有人。他下令将水加热洗我。她坐在我的低谷,洗净,她哭:
- !我的天,做了什么,不敢去碰
我就像一个比赛我她所有的衣服是穿在股权。
- 面包多,她没来, - 师傅说 - 再死。给她黄瓜和白菜略有下降。
我住多久,主人带我到城市Pettsnik,还有我们收集了所有的幸存者。我们被装在机器上,并采取布雷斯劳,在那里证书实行了,找亲戚,再由火车排序 - 家
在RAVA俄央求我把下了火车,我知道他的地址,打算徒步回家。医疗上校,列车的头,对我说:
- 我们离开你,只有你,devonka,不要告诉任何人去了游击队。大约班德拉知道 - 当场毙命
。 于是,我来到了卢茨克,还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并通过她的电子邮件地址在利沃夫,在那里我的中间姐姐工作的经验教训。它去了。她没认出我马上,他对她说,我被枪杀。我所有的时间住在车站,其中一个姐姐是在铁路住宅工作。在这里,我们来了,我姐姐睡,妈妈洗洗衣服,给我留下的大厅里,我听到他们在说:
- ?妈妈,你去教堂,你Irinka纪念
- 为了健康, - 母亲回应。 - 我把它连做梦也没有见到死者。而这些日子的梦想一直是:三鹅飞,一去低低,走近我。我醒了......
- 等待,妈妈, - 姐姐说 - 那滴饮...活着的我们Irinka ...
并打开门。我阈值:
- 妈妈
而她:
- 这是我的鹅来了! - 而晕倒
。 我就去了,滋养。我去工作作为传染病诊所的护士,学校毕业,实验室在医学院。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党派去调查。即使她的丈夫第一个十年的一句话。
他利沃夫大学毕业的火,我们必须传染性满足。在第56届,他分给阿尔扎马斯,然后在谢尔加奇。他是足够老上校。我跟着他来到这里。在线性医院,她担任在行进莫塔医疗助理,并在第79变成了疗养院“银泉”。我们有一年的这个房子是给,但也有生活,我告诉你,和我老公吵架他的上级不知道怎么的邻居...
而在同样的语调和细节一个小时,我听到一个关于新公寓的故事,一个字母复述长子从服务中,如何苍蝇建立了一个新的pozharku因为生病,意外死亡,如告诉三天死亡前几小时细节关于女儿的烦恼,并从儿童感冒的食谱孙女。当然,一个美好的新的屋顶。二十次看着与前者运行深色条纹天花板。天花板不再流淌。
而外面还在下雪,城市谢尔加奇躺在冬季暮色的底部。从房子的窗户点燃的底部。所有的网吧走去庆祝婚礼和葬礼,因为它是星期六。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城市唯一的浴缸洗澡的一天结束了,从最后的力气伸出的烟囱冒烟,好像zatushennoy蜡烛。
伊琳娜Efimovna我送到大门口。我漫无目的的走着。和所有的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步步为营,和其他任何晚上我是不是感激和感谢叹了口气。
©马克西姆Kungas

资料来源:
春天伊琳娜Suvorova Efimovna好运气。其中前护士疗养院火车站谢尔加奇住自1978年以来的房子,有一个新的屋顶。现在,他是在列宁大街最明显。众议院Suvorova看起来还是聪明的,像9月1日的学生。修复了程序,提高铁路工人的生活条件下,由高尔基铁路 - 战争的成员和退伍军人
虽然这已过期快一年了,伊琳娜Efimovna都不能平静下来。几乎没有,他回忆自己的幸福。然后,他开始感谢。女人在一个新的屋顶由“有罪”的名字的详细列表。在这里,一切从耶和华神对高尔基路雷川,谁亲自祝贺苏沃洛夫胜利日的首领。
在这个女人的记忆令人羡慕。她清楚地记得四分之三通过它走了一个世纪的可怕细节。例如,前40几分钟后我们的会议,她告诉我怎么她的儿子去看望义务兵1977年10月3日。什么模式是Polotenchik在士兵的食堂。他们洗过的杯子她的女儿。而他们带来了他们的好东西 - 对待同胞的儿子。而如何将其他的“聪明绝顶”的父母试图进行在塑料袋伏特加境内瞒着警惕检查,但没有工作...
但是,当伊琳娜Efimovna回忆松针,桤木耳环配方煎液,并告诉如何有吸桦叶求生布痕瓦尔德,有人则增长到椅子上,不再明白为什么外界这么安静下雪,靠近文化之家的灯安详地漂浮在暮光之城,走出去。
[下一页]
在1941年8月,她十二岁。然后,她住在一起,她的母亲和姐姐在白俄罗斯,Rechitsa区。哥哥 - 远东,姐姐 - 在利沃夫。这是很难想象德国人第一次,她只看到了第二个春天42。在此之前,村里Kuzmino它们不会出现。没有必要,而在春季和秋季kuzmintsy住在岛上,切断与外界盆满钵满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的支流。在夏季,通过沼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传球,冬季雪到他的腰部。人们躲到了船,切断所有的狗,以免发出响声,住谣言。德国人的居民,焚烧,毒害井射击村地区,共同提高。最后,在5月达成和库兹明。
- 我们去了房子的两名军官走了一圈房间里,我的姐姐也没注意, - 伊琳娜Efimovna说。 - 认为他的上司找到一个公寓,但房子太小
。 - ?你怎么理解这个
- 德国知道
。 - 在哪里?
在村里,我们有两个人从德国俘虏的德国妇女,妻子第一次战争结束后归还,他们的子女讲的语言。在学校里,我们教给德国犹太人。我简单易学......他们去了,和德国之后扔。他们从房子漫游到的房子,花了一切,甚至衣服。牛削减和左 - 沉默...
我们的董事长说,这是一次对我们在森林里。我们开始离开。主席 - 游击队司令。而我们的森林Kerbitsky知道吗?在这里,您将进入 - 刚出门沃罗涅日。孩子们给了主席的叛徒,他们被射中的目标,妻子疯了前面,流浪街头和嚎叫,他回到村里,并死在那里。他是个好人。我们实际上是父亲留下的房子卖了,开走了到乌拉尔“二十五Thousander”集体组织,而主席,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房子...
而我与游击队。我去调查。他的穿着乞丐 - 和乡村施舍。有时几周村与村,和Holmichi和Rechitsa和布拉金。甚至在乌克兰。小男孩和我一起发布的,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们要求面包和条件看,听,但被安排作为一个德国人,什么号码以及如何最好地接近他。我们花了一晚上就在shalashika党派点的森林。一个Khomich等城市,我们有在那里连接的公寓。我们从来不写任何东西,一切都只是一个信物。之后,我们和桥梁破坏和破坏火车开动起来......
很多事情看到的。对于Holmichami5公里 - 深谷。我们只是回到通过它和背部 - 不了解,不认识的地方。没有山沟。一个场。来吧,和地底下的摇摆我们。我说 - 地震了!在精神跑到森林,吓人,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但是,在山沟里的东西不见了?!指挥官告诉我他:
- 嘿,伙计们,在犹太人的山沟德国人活埋。而由于土地被移动在山沟转身。
我提供的伏特加喝一杯,在来了,而我却没有。三天也就不会......
然后,我被送到了乌克兰。两个坐了下来之前,我可以传达信息,并在RAID三分命中。没办法了,狗领着我们到卢茨克,然后装到卡车,送往德国。所有的犹太人都还在路上某处波兰下降的。和其他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孩子们住在独立的军营。每天早晨,那些谁不上升到他的脚下,他可以在卡车上被带走并烧毁。但我们有一个小的犹太人保存。他是一个德国人,因为我们得到的,目前尚不清楚。而这对他的护士长没有出现,我们有他的头洗桦树叶子煎服。于是他就成了黑头发的花斑。
巴拉克站在森林和森林就像家里给我靠近。我搜集各种草药 - Lungwort,蓍草,与桤木耳环,松针,酿造,和我们喝。但是,他们的胃抢救和存活。
我有点相信活着。还有人跟我一样,Zdorovenki,12人。房间就在眼前,我们没有把拍摄他们的士兵二百克,喂糖水补血。我相信,才能生存下来。然后在轰炸开始。一天早晨,早在4月45,护士长自己放我们走。他们说去,无论你想。所以,去没有人能 - 已扩散在不同方向tarakanchiki
。
我看到在一个草垛谷仓山农场抓取和手表 - 狗。闻我,他走了过来,坐了下来。不象我们在训练营:不要急于和看守,所以我也没有出来。到了晚上,主人回来,德语。我以为他是我的投降,并在框中他自己的外套,并把我扔进率领的房子。有情妇说,在这里,他们说,你带那个女孩那里。她询问是否有人看到。没有人。他下令将水加热洗我。她坐在我的低谷,洗净,她哭:
- !我的天,做了什么,不敢去碰
我就像一个比赛我她所有的衣服是穿在股权。
- 面包多,她没来, - 师傅说 - 再死。给她黄瓜和白菜略有下降。
我住多久,主人带我到城市Pettsnik,还有我们收集了所有的幸存者。我们被装在机器上,并采取布雷斯劳,在那里证书实行了,找亲戚,再由火车排序 - 家
在RAVA俄央求我把下了火车,我知道他的地址,打算徒步回家。医疗上校,列车的头,对我说:
- 我们离开你,只有你,devonka,不要告诉任何人去了游击队。大约班德拉知道 - 当场毙命
。 于是,我来到了卢茨克,还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并通过她的电子邮件地址在利沃夫,在那里我的中间姐姐工作的经验教训。它去了。她没认出我马上,他对她说,我被枪杀。我所有的时间住在车站,其中一个姐姐是在铁路住宅工作。在这里,我们来了,我姐姐睡,妈妈洗洗衣服,给我留下的大厅里,我听到他们在说:
- ?妈妈,你去教堂,你Irinka纪念
- 为了健康, - 母亲回应。 - 我把它连做梦也没有见到死者。而这些日子的梦想一直是:三鹅飞,一去低低,走近我。我醒了......
- 等待,妈妈, - 姐姐说 - 那滴饮...活着的我们Irinka ...
并打开门。我阈值:
- 妈妈
而她:
- 这是我的鹅来了! - 而晕倒
。 我就去了,滋养。我去工作作为传染病诊所的护士,学校毕业,实验室在医学院。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党派去调查。即使她的丈夫第一个十年的一句话。
他利沃夫大学毕业的火,我们必须传染性满足。在第56届,他分给阿尔扎马斯,然后在谢尔加奇。他是足够老上校。我跟着他来到这里。在线性医院,她担任在行进莫塔医疗助理,并在第79变成了疗养院“银泉”。我们有一年的这个房子是给,但也有生活,我告诉你,和我老公吵架他的上级不知道怎么的邻居...
而在同样的语调和细节一个小时,我听到一个关于新公寓的故事,一个字母复述长子从服务中,如何苍蝇建立了一个新的pozharku因为生病,意外死亡,如告诉三天死亡前几小时细节关于女儿的烦恼,并从儿童感冒的食谱孙女。当然,一个美好的新的屋顶。二十次看着与前者运行深色条纹天花板。天花板不再流淌。
而外面还在下雪,城市谢尔加奇躺在冬季暮色的底部。从房子的窗户点燃的底部。所有的网吧走去庆祝婚礼和葬礼,因为它是星期六。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城市唯一的浴缸洗澡的一天结束了,从最后的力气伸出的烟囱冒烟,好像zatushennoy蜡烛。
伊琳娜Efimovna我送到大门口。我漫无目的的走着。和所有的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步步为营,和其他任何晚上我是不是感激和感谢叹了口气。
©马克西姆Kungas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