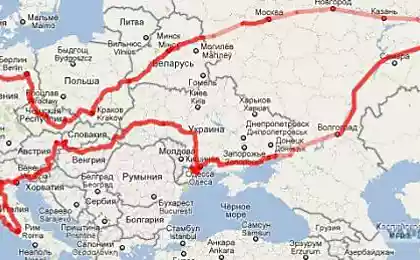797
塔蒂亚娜切尔尼戈夫斯卡亚:为什么狗狗不去博物馆
塔蒂亚娜切尔尼戈夫斯卡亚- 尊贵的工作人员科的俄罗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在该领域中的神经科学、心理语言学和理论的意识,说iskustvima的具体目标。

"我会开始有一种挑衅行为。 几年前,我是在国际一符号学大会,有一份报告,名称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它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不去博物馆"。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 有在地板上,他们可以走路,有的空气,他们可以呼吸,他们的眼睛、耳朵。 不知何故,他们和爱乐乐团,也不要去。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返回我们的东西我们,人类是特别的。
和两次,今天我记得布罗德斯基。 第一时间了。 布罗德斯基说,关于诗歌,关于艺术在一般情况下,但它是相当适用:"诗歌是我们的物种目的。"
我得到那时,如我们所知,没有像我们的邻国在这个星球上那里。
我们不是生活中的对象,事情,山脉和河流。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的想法。 我认为这是适当的说尤利*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我有幸聊很多,而且它当然不应该被遗忘。 毕竟,这个想法的尤利*米哈伊洛维奇的是,技术中反映了生活和艺术的创建生活,它创建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洛特曼,顺便说一句,说,前出现屠格涅夫女士们,没有屠格涅夫的年轻女士、前有额外的人,没有额外的人。 第一,它必须写Rakhmetova,然后躺在钉子,以检查有多少,他们将举行的。 在这里先生所说的只是现在,这一切都在头部。 是的,它在所有的头,那就是为什么狗和所有其他可爱的动物绝对没有理由去马林斯基影院或博物馆,因为我们看看的眼睛,看到大脑,我们听到我们的耳朵,但是听到我们的大脑,所以所有的传感器系统可以走了。 需要训练有素的大脑。 这样,我说对该主题的精英主义。
不,是坏的和好的大脑,并脑必须接受教育,否则是无用的看"黑色的正方形的","红场",听勋伯格等。

当布罗德斯基说,技术是我们的"特定目的",我谨强调这里的事情。 艺术是不同的,不科学的,在那里,我说,我这样做,以不同的方式的理解世界和另一个方式描述的世界。在一般情况下,其它的。
我想说的是,通常,一般公众认为,存在严重的事情是生命,或至少将技术和科学。 而有这样的附件,可以这么说,甜点:你可以吃,不吃的,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勺子,福克斯,镊子和以上,并可以简单地被错过。 问题是谁,我们想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业主的耳朵、鼻子,眼睛和手,然后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所有你可以做。
但是技术并什么—我再次你回到我了—这让普鲁斯特关于该主题的存储器。 普鲁斯特打开—我想说,该法律的存储器,但是这太可悲的。
他说,有关记忆的东西,现代科学与其所有技术和巨大能力的唯一选择。 的艺术家中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并不重要,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有任何这样的触角,它们揭示了事情是无法访问的帮助下的科学。 更确切地说,也许,但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印象派画家 打开有关的愿景。不是关于棒和锥,没有眼睛的结构和有关的视野。 他们发现,在几十年来,然后发现的感觉生理学,从而开始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复杂的视觉的对象。

因此,回到布罗德斯基,那是什么别人可以做的。 这样我就能看到,听到,了解的东西,我需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大脑。
我们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相同的脑或多或少(除了遗传学),空洞的文字上的神经网络,这是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每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间,将站在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经网络,并且将有一个书面的文本,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粮食、莱昂纳多,口红,裙子、书籍、风能、太阳能在一个特定的天—一切都写在那里。 因此,我们希望这个案文是困难的,或者我们希望它是漫画吗? 然后大脑必须做好准备。
说到这,我会说唯物论的一件事,谁在乎,你可以给一个链接到严重的科学文章。 现在,你也谈到了健身艺术是健身。 当然,如果我们躺在沙发沙发上躺了半年,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如何站出来,不,怎么走。
如果大脑是不是忙于辛苦的工作,那么没有什么可惊讶和高兴。 这将是纯文本和沉闷的纯文本。 大脑有所改善艰苦的工作,但技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的大脑,因为它需要我重复一遍,培训,并有很多不平凡的移动。
那这火车神经网络,她是在物理上改善。 我们知道自己的音乐制作和听复杂音乐的神经网络质的不同,非常复杂的进程都会在大脑的一个人听的音乐或戏剧了她。 非常复杂的过程,当一个人(谁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不仅仅是他的眼睛是睁开)在寻找一个复杂的图片或绘画。 的对象本身,将它绘画、雕刻、电影或什么的,它不是自主的,它取决于有关维塔耶娃什么的时候说"读者的共同作者"作。 这取决于谁读,谁听谁看起来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故事。
我最近刚刚读到一篇文章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西方的期刊关于什么是发生在大脑的一个舞蹈家. 非常复杂的过程正在进行。 也就是说,不要认为技术是一种容易的,愉快的补充,一般是简单打扮,而美丽。 它不是这个,它不是关于"美丽"。 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不是数字,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它不是的算法,它gestalte,它是模糊的,它是关于什么理念话感受性、质量。
感受性的东西,不能被描述任何种方式,这种第一人的经验是"我怎么感觉"。 在这里,我们喝同样的葡萄酒,你说,就像什么味,很好,徒劳的这些笔记。 和我说的话:在我看来,那些笔记,因为它应该很好...没有克、毫克,光谱的不能说明这样的事情冷暖,很好,美丽的。 在这里,科学的无能为力的人"。
P.S.并记住,只要改变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推动
资料来源:izbrannoe.com/news/mysli/tatyana-chernigovskaya-mozg-dolzhen-byt-obrazovan-inache-emu-bespolezno-smotret-na-chernyy-kvadrat-i/

"我会开始有一种挑衅行为。 几年前,我是在国际一符号学大会,有一份报告,名称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它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不去博物馆"。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 有在地板上,他们可以走路,有的空气,他们可以呼吸,他们的眼睛、耳朵。 不知何故,他们和爱乐乐团,也不要去。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返回我们的东西我们,人类是特别的。
和两次,今天我记得布罗德斯基。 第一时间了。 布罗德斯基说,关于诗歌,关于艺术在一般情况下,但它是相当适用:"诗歌是我们的物种目的。"
我得到那时,如我们所知,没有像我们的邻国在这个星球上那里。
我们不是生活中的对象,事情,山脉和河流。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的想法。 我认为这是适当的说尤利*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我有幸聊很多,而且它当然不应该被遗忘。 毕竟,这个想法的尤利*米哈伊洛维奇的是,技术中反映了生活和艺术的创建生活,它创建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洛特曼,顺便说一句,说,前出现屠格涅夫女士们,没有屠格涅夫的年轻女士、前有额外的人,没有额外的人。 第一,它必须写Rakhmetova,然后躺在钉子,以检查有多少,他们将举行的。 在这里先生所说的只是现在,这一切都在头部。 是的,它在所有的头,那就是为什么狗和所有其他可爱的动物绝对没有理由去马林斯基影院或博物馆,因为我们看看的眼睛,看到大脑,我们听到我们的耳朵,但是听到我们的大脑,所以所有的传感器系统可以走了。 需要训练有素的大脑。 这样,我说对该主题的精英主义。
不,是坏的和好的大脑,并脑必须接受教育,否则是无用的看"黑色的正方形的","红场",听勋伯格等。

当布罗德斯基说,技术是我们的"特定目的",我谨强调这里的事情。 艺术是不同的,不科学的,在那里,我说,我这样做,以不同的方式的理解世界和另一个方式描述的世界。在一般情况下,其它的。
我想说的是,通常,一般公众认为,存在严重的事情是生命,或至少将技术和科学。 而有这样的附件,可以这么说,甜点:你可以吃,不吃的,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勺子,福克斯,镊子和以上,并可以简单地被错过。 问题是谁,我们想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业主的耳朵、鼻子,眼睛和手,然后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所有你可以做。
但是技术并什么—我再次你回到我了—这让普鲁斯特关于该主题的存储器。 普鲁斯特打开—我想说,该法律的存储器,但是这太可悲的。
他说,有关记忆的东西,现代科学与其所有技术和巨大能力的唯一选择。 的艺术家中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并不重要,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有任何这样的触角,它们揭示了事情是无法访问的帮助下的科学。 更确切地说,也许,但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印象派画家 打开有关的愿景。不是关于棒和锥,没有眼睛的结构和有关的视野。 他们发现,在几十年来,然后发现的感觉生理学,从而开始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复杂的视觉的对象。

因此,回到布罗德斯基,那是什么别人可以做的。 这样我就能看到,听到,了解的东西,我需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大脑。
我们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相同的脑或多或少(除了遗传学),空洞的文字上的神经网络,这是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每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间,将站在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经网络,并且将有一个书面的文本,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粮食、莱昂纳多,口红,裙子、书籍、风能、太阳能在一个特定的天—一切都写在那里。 因此,我们希望这个案文是困难的,或者我们希望它是漫画吗? 然后大脑必须做好准备。
说到这,我会说唯物论的一件事,谁在乎,你可以给一个链接到严重的科学文章。 现在,你也谈到了健身艺术是健身。 当然,如果我们躺在沙发沙发上躺了半年,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如何站出来,不,怎么走。
如果大脑是不是忙于辛苦的工作,那么没有什么可惊讶和高兴。 这将是纯文本和沉闷的纯文本。 大脑有所改善艰苦的工作,但技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的大脑,因为它需要我重复一遍,培训,并有很多不平凡的移动。
那这火车神经网络,她是在物理上改善。 我们知道自己的音乐制作和听复杂音乐的神经网络质的不同,非常复杂的进程都会在大脑的一个人听的音乐或戏剧了她。 非常复杂的过程,当一个人(谁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不仅仅是他的眼睛是睁开)在寻找一个复杂的图片或绘画。 的对象本身,将它绘画、雕刻、电影或什么的,它不是自主的,它取决于有关维塔耶娃什么的时候说"读者的共同作者"作。 这取决于谁读,谁听谁看起来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故事。
我最近刚刚读到一篇文章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西方的期刊关于什么是发生在大脑的一个舞蹈家. 非常复杂的过程正在进行。 也就是说,不要认为技术是一种容易的,愉快的补充,一般是简单打扮,而美丽。 它不是这个,它不是关于"美丽"。 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不是数字,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它不是的算法,它gestalte,它是模糊的,它是关于什么理念话感受性、质量。
感受性的东西,不能被描述任何种方式,这种第一人的经验是"我怎么感觉"。 在这里,我们喝同样的葡萄酒,你说,就像什么味,很好,徒劳的这些笔记。 和我说的话:在我看来,那些笔记,因为它应该很好...没有克、毫克,光谱的不能说明这样的事情冷暖,很好,美丽的。 在这里,科学的无能为力的人"。
P.S.并记住,只要改变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推动
资料来源:izbrannoe.com/news/mysli/tatyana-chernigovskaya-mozg-dolzhen-byt-obrazovan-inache-emu-bespolezno-smotret-na-chernyy-kvadr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