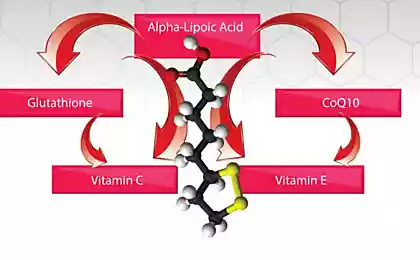414
代"叔叔费奥多尔"—渴望的控制父母的世界
当我们谈论阿尔法的复杂儿童,通常我们都在谈论这样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本能的愿望,以控制家长和世界,需要控制一切的命令,一种倾向,暴政和积极的表现形式在一个孩子。 同时,α-复杂的是一个不同的和非常有吸引力的脸是giperatidnyi,hypersonically的孩子。 关于这孩子我想和你谈谈.
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并从经验中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多少我记得我自己—我记得我母亲的一句话:"安娜,看你的弟弟!"

我看着,我并不需要两次要求,我这样做是很自愿和热情。 我的第一个的回忆:我的父母不在家,需要改变兄弟的尿布。 这是一个严重挑战对我们两个兄弟蠕动,打破免费的,但我不知怎的管理。 鉴于锅我们被教导在一个半年,我是在那一刻,大约3年。 关切非常活泼又淘气的哥哥是个麻烦的业务。 有背带,把他拉出第比利斯和彼得夏喷泉说服跳伞从四楼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抓住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后空翻房子在游乐场上,以让它走不饱甜,不要吃东西他是过敏。 我朋友的母亲很多次,然后与情感说:坐的面包屑,小面包屑表示不同的菜在表和有关每个问:"安娜,怎么了?" 大宝宝说,你不能。
有,我承认,时刻,当我累了担心年轻人和我的仁慈蒸发。 然后,而不是照顾我一样多受虐待的兄弟,例如,假装死了,享受什么,他认为,担心,我恳求上升。 享受他的认罪,我很快就"复活",并说"笑话! 你真的相信吗?!" 这种公然的欺凌谈到的事实,我也不总是容易的。
我母亲工作的两个工作岗位,爸爸三个,我的工作是跟随的兄弟。 在一般情况下,肌肉负责照顾的年轻化,受过训练我不好然后很多时间一直担任我在生活的一个良好的服务和仍然的。 我的护士的所有护士,一切都过去了海滩戴太阳帽和所有抹防晒霜。 本能的愿望,即使需要承担责任,照顾和保护的传播然后溢出列宁格勒的小猫和鸽子的,哭着,晚上儿童在营地,在朋友和同学们,并最终我的母亲。
十四年,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感觉,我实际上是一个母亲我的妈妈。

爱丽丝*米勒"戏剧的天才儿童"的儿童习惯于敏感地轨道的精神状态对他们的母亲和承担责任,这些国家制定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线"捕捉动作的另一个灵魂,不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儿童然后成长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工作者。 许多这些专业人员的前儿童的alpha复杂。 我也是,默认情况下,是支持和帮助的活动。
我所有的积极素质和努力,已经把我的赞美,爱和承认,但除了一个巨大的责任,我感到非常关切和焦虑。 我是不是能够做坏事,我不能让任何人失望。 在二年级时我多达3个晚上一次重新编写了这本书,直到老茧在他的手指被改写,父母两人相信我要吐口水,睡觉,但这是不可能的,神经官能症被迫一次又一次改写,直到它的美丽。 它仍然很难停止和不重写150时间已经和正常的文本。 完美主义的根源是焦虑,但是有其它的、较可取的症状:恐惧、焦虑、恐惧、恐慌症发作—所有的年轻人的先锋。 在我的朋友在我的一代--我们有许多的这些。
代叔叔费奥多尔,在apt字德米拉Petranovskoj是我们,这是我的。 我–Dyadya费奥多尔。
和西奥多叔叔是好的:你用了一个免费的、独立的、决定如何以及如何生活,但你可以不依赖于任何人,你不要有人依赖的,你们负责的一切—你害怕。 甚至如果没有人在附近的人,你可以依靠不再工作,也没有习惯这感觉很奇怪和非常脆弱。
叔叔陀是非常困难的照顾他需要严重疼痛,来到这件事情。
这种情况与giperatidnyi的儿童被卡在了主导地位和具有习惯的照顾。
他们承担的巨大负荷,tasaciones负担,他们承担由于内部资源,可以去游戏,形成、成熟、大脑的成熟。
相反,资源是花上一辈子的斗争的焦虑,以及如果你知道有多少吃的恐惧和多少只是碰巧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愚蠢的恐惧。
在一般情况下,道德,一如既往,是简单的:一方面,就是这样,而对于什么是良好的,谢谢你,是这样,而不是更糟。 但另一方面—让我们的儿童是儿童,并让一切都是在它的时间,弱者的心理应受到保护,过多的问题。 如说我的祖母:"不是我的菜,宝贝,让我洗,将namesse!" 她不知道的是,发明了洗碗机。 出版
提交人:Anna Gasinska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alpha-parenting.ru/2016/12/08/anna-sledi-za-bratom/
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并从经验中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多少我记得我自己—我记得我母亲的一句话:"安娜,看你的弟弟!"

我看着,我并不需要两次要求,我这样做是很自愿和热情。 我的第一个的回忆:我的父母不在家,需要改变兄弟的尿布。 这是一个严重挑战对我们两个兄弟蠕动,打破免费的,但我不知怎的管理。 鉴于锅我们被教导在一个半年,我是在那一刻,大约3年。 关切非常活泼又淘气的哥哥是个麻烦的业务。 有背带,把他拉出第比利斯和彼得夏喷泉说服跳伞从四楼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抓住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后空翻房子在游乐场上,以让它走不饱甜,不要吃东西他是过敏。 我朋友的母亲很多次,然后与情感说:坐的面包屑,小面包屑表示不同的菜在表和有关每个问:"安娜,怎么了?" 大宝宝说,你不能。
有,我承认,时刻,当我累了担心年轻人和我的仁慈蒸发。 然后,而不是照顾我一样多受虐待的兄弟,例如,假装死了,享受什么,他认为,担心,我恳求上升。 享受他的认罪,我很快就"复活",并说"笑话! 你真的相信吗?!" 这种公然的欺凌谈到的事实,我也不总是容易的。
我母亲工作的两个工作岗位,爸爸三个,我的工作是跟随的兄弟。 在一般情况下,肌肉负责照顾的年轻化,受过训练我不好然后很多时间一直担任我在生活的一个良好的服务和仍然的。 我的护士的所有护士,一切都过去了海滩戴太阳帽和所有抹防晒霜。 本能的愿望,即使需要承担责任,照顾和保护的传播然后溢出列宁格勒的小猫和鸽子的,哭着,晚上儿童在营地,在朋友和同学们,并最终我的母亲。
十四年,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感觉,我实际上是一个母亲我的妈妈。

爱丽丝*米勒"戏剧的天才儿童"的儿童习惯于敏感地轨道的精神状态对他们的母亲和承担责任,这些国家制定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线"捕捉动作的另一个灵魂,不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儿童然后成长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工作者。 许多这些专业人员的前儿童的alpha复杂。 我也是,默认情况下,是支持和帮助的活动。
我所有的积极素质和努力,已经把我的赞美,爱和承认,但除了一个巨大的责任,我感到非常关切和焦虑。 我是不是能够做坏事,我不能让任何人失望。 在二年级时我多达3个晚上一次重新编写了这本书,直到老茧在他的手指被改写,父母两人相信我要吐口水,睡觉,但这是不可能的,神经官能症被迫一次又一次改写,直到它的美丽。 它仍然很难停止和不重写150时间已经和正常的文本。 完美主义的根源是焦虑,但是有其它的、较可取的症状:恐惧、焦虑、恐惧、恐慌症发作—所有的年轻人的先锋。 在我的朋友在我的一代--我们有许多的这些。
代叔叔费奥多尔,在apt字德米拉Petranovskoj是我们,这是我的。 我–Dyadya费奥多尔。
和西奥多叔叔是好的:你用了一个免费的、独立的、决定如何以及如何生活,但你可以不依赖于任何人,你不要有人依赖的,你们负责的一切—你害怕。 甚至如果没有人在附近的人,你可以依靠不再工作,也没有习惯这感觉很奇怪和非常脆弱。
叔叔陀是非常困难的照顾他需要严重疼痛,来到这件事情。
这种情况与giperatidnyi的儿童被卡在了主导地位和具有习惯的照顾。
他们承担的巨大负荷,tasaciones负担,他们承担由于内部资源,可以去游戏,形成、成熟、大脑的成熟。
相反,资源是花上一辈子的斗争的焦虑,以及如果你知道有多少吃的恐惧和多少只是碰巧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愚蠢的恐惧。
在一般情况下,道德,一如既往,是简单的:一方面,就是这样,而对于什么是良好的,谢谢你,是这样,而不是更糟。 但另一方面—让我们的儿童是儿童,并让一切都是在它的时间,弱者的心理应受到保护,过多的问题。 如说我的祖母:"不是我的菜,宝贝,让我洗,将namesse!" 她不知道的是,发明了洗碗机。 出版
提交人:Anna Gasinska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alpha-parenting.ru/2016/12/08/anna-sledi-za-br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