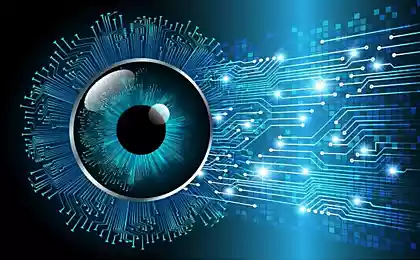796
可怕的故事
" ......我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女人 - 她的名字是芭芭拉 - 每个人都认为是傻瓜祝福。性格孤僻又丑它,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多大了 - 她的皮肤很光滑,但这样的景象,仿佛一切都在世界上早已厌倦了。但是,芭芭拉很少它注重别人的脸 - 她太封闭,沟通甚至眼神。最奇怪的是,没有人会记得它是如何出现在村里。
战争结束后,在一片混乱中消失了,许多人来说,外星人,相比之下,来了,一定是好的。也许,正是这些朝圣者在寻求更好的命运之一。她采取了最极端的空置房在林中,很老的和小的,并为十年,二十年开车把他送到总荒凉的状态。有时候,富有同情心的邻居修理她的屋顶,然后在染胡须喃喃自语:没有,好,谢谢,她雨水大声滴在取代骨盆,我做到了,它是干的,而野蛮人是不够的“谢谢”也不说,所以甚至没有看的脸。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活,他吃什么。她总是去了同样的衣服deryuzhki其下摆重与干泥。在相同的 - 但它的气味不厚麝香人类排泄物,这是不从皮肤洗涤,地下和模具。
后来有一天,在六十年代初期,当地的球员之一,有感动伏特加,他闯入她的家 - 无论podnachil谁,无论是抽象的女性气质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象并不重要。这是在五月份,安静的,明确的,满月的夜晚,朵朵草药和蟋蟀唤醒了密集的香味 - 以及整个村前庆祝胜利,发挥了手风琴,冶炼馅饼,喝,吃了,走了。男子名叫费多尔,这是二十五年。 [下一页]
他闯入瓦尔瓦拉的房子,已经有一次,在大厅里,比如他感到不安。房子是一种奇怪的气味 - 空虚和衰减。就连村里的酒鬼叔叔谢尔盖在家里闻到完全不同,虽然丙基灵魂早在那些日子里,当宝宝是费多尔。谢尔盖的叔叔闻到温暖的烤箱,再强悍,脏脚,酸奶,腐烂门垫 - 这是令人厌恶的,但在恶臭气味的不协调感觉让几乎沦落成的存在,但仍然有生命。和芭芭拉闻,仿佛房子就没有来了几十年 - 潮湿的地下室,尘土飞扬的窗帘和模具。陀突然很想转身走上自己的高跟鞋,但不知何故,他说服自己,这是不是“男人”。他向前移动 - 触摸,因为房子很黑 - 帘子的窗户在一些碎布月光。
捅露出双臂向前门 - 她屈服于一个安静,吱嘎开启。费奥多尔小心翼翼走了进去,稍微碰了头了吧 - 芭芭拉涨幅不大,门的房子 - 它匹配。房间中,他发现自己,是为暗费多尔很快就失去了方向的空间,但突然有人在角落里轻轻搅拌,动物的恐惧,从而导致大多数人的黑暗加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他的战士突然惊醒和野蛮。随着费奥多尔短一声,他冲上前去。
- 去 - 语音芭芭拉,安静和平淡,和费多尔敢发誓,他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许多人相信,在所有的偏心的最后一栋房子麻木,甚至在战争年代,却再也没醒过来。
她伸出手的地方,拉开窗帘,和费多尔终于见到了她 - 在蓝色灯光的月亮似乎平息死者的丑恶嘴脸。
- 这里还有一个! - 他试图声音欢快,而是因为所谓的兴奋“的一声公鸡”,并在自己的愤怒的,他流下了悲观的瓦尔瓦拉,戳他的拳头在她毫无生气的脸, - 来吧,来吧......我快。
她没有反抗,并给了他心灵的力量。 “也许她梦想着它,很高兴到死,不相信自己的幸福, - 他认为 - 一个人的东西,我想,二十年她,如果不是更多。
芭芭拉都包裹在一些碎布,像寿衣。他一样,顶部敞着外套,羊毛,但它原来是一种地幔,甚至更深层次的 - 东西,看起来像尼龙,滑,爽的感觉。最终,愤怒的,他拉抹布,而那些破解,几乎在他手中分崩离析。瓦尔瓦拉以及所有躺在寂静,伸展双臂在身体两侧,为死者,谁是准备洗澡。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和他心中的角落里,陀突然说,他们不发光。马特的眼睛,像个洋娃娃。
但是,他的血已经沸腾的熔岩希望倒出来,从火中释放他,他几乎是,谁将会解锁口 - 无论是女人温暖,poslyunyavlenny拳头还是这个灰色娃娃。
胸部芭芭拉就像一块空白的画布麻袋,其中费奥多尔的母亲把这坚果,它们聚集在树林里。它既不完备,也不乳房柔软度,和她的乳头就像木香菇,又粗又黑,触摸他们不想。那一刻仿佛想起西奥多岔 - 人们常常不明白,你怎么能要求它褪色蜡体是可怕的,恶心的相同,另 - 仿佛着了魔,只是一种盲目的意志,冲动和激情,因为它是。膝盖,他传播她的大腿 - 同样的冷静和灰如蜡和扳手插入她 - 西奥多的一部分,这是可怕的,令人厌恶的,它似乎是他的肉包括不是女人,但在投手与冷发酵出炉。里面芭芭拉是宽松,凉爽和潮湿。而现在,在她的种子壶嘴,费多尔离开,纠结于裤子的道路上。他觉得,如果他是春耕整天砍伐森林,但注销了这个弱点和头晕伏特加。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没有脱衣服,躺下来睡觉。
整个晚上,他做恶梦。他梦见自己走在村里的墓地,墓穴之间,并在各方面给他伸起双手沾满了地上。尽量把握裤腿,和手指有冰冷和坚硬。他的耳朵嗡嗡声站 - 缺乏果汁生命的声音哀求道:“而且我......和我......请......和我...»
在这里,在他面前的赛道上有一个女孩 - 她站在他的背后,脆弱,低,长麦头发散乱在肩上。她穿着婚纱。陀冲到她作为一个救世主女神,但她慢慢地转身,很明显 - 也死了。苍白的脸绿点去了一次丰满的上嘴唇半otgnila,牙齿露出,他的眼睛不亮。
- 我... - 她呆呆地重复 - 来吧......我故意埋在婚礼......我等了你...
费奥多尔从什么她的母亲泼他在冰水中的勺子面对醒。 “很opoloumel醉了!我沐浴到魔鬼和喊叫整夜,就好像我有铁的意志!»
它花了几个星期。起初陀无法摆脱痛苦的感觉,就好像它伸出了沉重的翅膀,它关闭了阳光。食欲,欲望笑,去工作,去呼吸。但渐渐地,他莫名其妙地恢复,苏醒,又开始问他的母亲早上煎饼,扫视着最美丽的处女村庄尤利娅长粗的辫子,并在他眼中的魔鬼。与芭芭拉,他尽量不见面 - 但是,这并不困难,她很少离开他的房子和花园,如果他们出去到村里的街道,然后蜷缩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尘土飞扬的套鞋,而不是冲突的人。渐渐的,奇怪的夜晚从内存中消失了 - 和费多尔甚至不是很确定,这是一个现实。他的心似乎雪球蒙蔽 - 真正的事实和相应的噩梦,甚至不明白 - 真相,那 - 一个可怕的形象,制造内部的黑暗。
冬天来了。
冬天的夜晚费奥多尔通常木工 - 手艺教给他的父亲,两个有金色的手。随着访问的市中心 - 谁把一个餐桌,有人来修理围栏,给谁,附着在房子的露台。
并于11月下旬,有一天,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 敲门声不停,就好像它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当陀打开 - 在街上空无一人。人打扰晚上安静的家庭一样溶解冰随地吐痰雨夹雪空间。只有在地板上,牵制潮湿的石头是白色信封。里面的钱 - 放眼望去,费多尔抱着他,看着里面,更惊讶。不是数百万,但巨额赔偿 - 所以他只是问了一个夏天的阳台建设。村里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件不寻常的 - 邻居肯定没有饿死,但为了节省钱不是在哪里,但对于所有的首选工作分期付款。加上从信封票据有附注。 “我问你做棺材,长度 - 1米材料 - 橡木或松木。拿钱马上,但是对于工作,我会做好准备的第一次机会。“
不容易受惊是费多尔,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内在的东西他去冷的时候读完。长度 - 1米。原来,棺材 - 孩子。为什么是他愿意付出这么多?如果客户问他价钱,费多尔称之为一笔二十次小,也不会认为自己得罪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奇怪的方式进行预约?这样的悲伤,从别人的厌恶?但事实证明,他甚至不是一个选择离开 - 给谁钱回来了?你当然可以,并让他们在信封,当客户将,门槛摆在你的脸上。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孩子死亡。而且,人们会来的,并没有什么准备。毛巾把他埋了还是怎么的?
这是辛苦费多尔的灵魂,但他仍然执行的工作。对于两个晚上议会。最好的主板了,试过好像棺材为帝王珍宝一样。即使雕刻装饰盖 - 做一些事情还是冬天的夜晚没有什么。
一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又接着开始了第三,但工作,所以没有人来了。小棺材站在已狭窄的通道和代理都紧张。走过了他,父亲费奥多尔严肃地说:“etit ......”,和他的母亲,他的绊脚石机械打腿残之一,于是来到她的感觉,坐在阶梯并简要哭了。
现在,在新的一年一次出色的晚上,当西奥多离开家独自一人。父母和妹妹去附近的村庄探亲,并打算在那里过夜。
夜是黑暗和暴风雪 - 茂密的冰雪披肩地球,也不是天上不会看到
。 突然,敲门声 - 同一个持久急忙敲费奥多尔马上签下他,而他的心脏蓬勃发展 - 仿佛带着无限冰冷的山。
小心找上门来,他问 - 谁,但是,他没有回答。为什么,然后传给自己,他打开门 - 在门廊上是一个小女人,裹着一件夹克和一个大的羊毛披肩。他甚至不承认它瓦尔瓦拉 - 当它看到灰脸无表情,退缩了。
- 你想要什么?为什么priperlas? - 在故意无礼,他试图汲取力量。
- 现在是时候 - 平淡,她说,走了进去过去他 - 我想了几个星期穿,但现在我看到有。它的时间。
- 什么是你讲的东西durischa?去otkudova priperlas。
然后芭芭拉提出了她的脸,他走了几步,他的眼睛飞奔到前庭无奈,直到埋在一个小斧头,这是他和他的父亲切芯片照明炉子。 “布拉德一些。所以我不会在她的,女人弱,用斧头......我是她的手指pereshibit可以说,她做一些事情,惨......”女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像斑点冰水坑。同样的沉闷和木偶一样的那个晚上,他这几个月试图忘记。
芭芭拉笑了笑 - 仍然没有感情。
- 你是什么,陀思porazvlecheshsya并没有回答。带上水和抹布,我生下。
- 你他妈的...... - 然后才在她敞着上衣巨大的圆腹看到
- 任何分钟,现在开始,你还等什么的
。 她一点也不像你所关心的关于女人的第一个出生的外观。无血平静的面容,干裂的嘴唇,即使是很小的声音。
- 再说,我付出。所有诚实的。做了什么,我问?我管理的?
费多尔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当他意识到突然觉得小和手无寸铁的。由于在那些日子里,当他的父亲把他吓得leshim和班尼科夫,和陀那么整个晚上试图平息气息 - 这一切想象中的噪音和哒,一些其他的,隐藏的成人生活,开始在家里的时候都去睡觉了。我想冲上去他的母亲,呼吸舒缓温暖,但耻辱阻止。
- 为什么要你......棺材? - 几乎是耳语的最后一句话,他呼吸面对野蛮人。
- 嗯,当然 - 她笑了 - 地方,因为他想睡觉。 Mertvenky事实上诞生了 - 和抚摸着他的绷紧的胃。
费多尔生病。
- 水正在成为, - 指挥瓦尔瓦拉 - 阻力和破布。开始。
作为一个梦想,他来到了烤箱,她拿着一个水壶,然后爬进后备箱的母亲发现了一些旧床单。一切,是发生在他身上似乎愚蠢的笑话。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村白痴,真理会生出他的门廊,他将不得不参与其中。而该死的钱,棺材。 “Mertvenky出生,因为...”
当西奥多回到了门口,他正躺在地板上,用他的裙子和分开不流血的腿,她的背部拱起,仿佛女子被雷电击中,但人依然没有表示任何畏惧,无痛苦,无期待。
西奥多姐姐,也出生在家里 - 突然回合开始,这是冬天也一样,他们没有时间开车去乡村医院。他想起了母亲,她的子宫喊的满脸通红,满身是汗的脸,更像是一个野性的咆哮,记起摊开她的沾有汗液,头发,什么气味在房间枕头 - 一热,密室内,他怎么也没有本身 - 但后来又有恐惧,有一定的永恒的规律存在的恐惧。母亲接着问喝,然后把她的额头上一把雪,然后在打开的窗口,然后将其关闭。然后,他听到了一声闷响小妹妹,她和她父亲喝了饮料,高兴之余,她的母亲看起来很开心,尽管所有的被子都湿透了她的血。
芭芭拉默默的,他的牙齿,生出了新的生活,她在她的臀部和背部 - 巧妙,像蛇一样,也是充满异味的树冠 - 泥炭沼泽,堆肥,湿树根,雨蠕虫。突然出来的匆忙,好像阀门被打开 - 一个绿褐色,为停滞的池塘水。费多尔不得不跳 - 水是臭烘烘的,以至于在走廊整个地板被水淹没。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泔水从她的子宫选择到的光的小家伙,一个婴儿,一个灰色的,毫无生气的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村,他的手背擦了擦额头,离开地面的婴儿 - 他懒洋洋地提出他的手。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戴了面纱像一个白色薄膜。费多尔扭过头去 - 看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不愉快的,什么不是。他甚至哭了,但转过头,明显是想看看周围。
- 你站在 - 严肃地叫芭芭拉 - 你需要剪断脐带。阿里没有读过书。
- 我不知道 - 从疲惫和厌恶,几乎昏厥,他喃喃自语
。 - 还有什么能。还有斧头是 - 他们砍伤。
- 你在说什么。就是嘛,你可以,用斧头。现在,我会打电话给奶奶阿列克谢耶夫 - 突然来到他拯救的想法 - 只要运行它。她知道如何处理。
- 任何人都不应被调用 - 瓦尔瓦拉叫住了他 - 他自己有罪,他会作出反应。把斧头......我来教你。而棺材携带。他已经想睡觉,你看。
- 芭芭拉,为什么还要棺材,你说的是可怕的 - 无法抗拒费多尔 - 哪里是在一个棺材样给宝宝睡着了。你说 - mertvenky诞生了,在这里,他是 - 移动。
- 所以我mertvenkaya - 灰色的嘴唇拉长,但它不是像一个微笑 - 阿里不明白? ......进棺材。而最需要放松。而其实他很快就饿了。在这里,你醒来,我会教你如何喂养mertvenkih。
最后一件事,他看到费多尔,在他覆盖了黑色的天鹅绒翼是旧的,分支到缝隙,天花板上。
第二天早上,他的父母和姐姐回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冷却下来,但睁着眼睛一直保持痛苦的警惕的表情。他怎么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但整个楼层走廊被水淹没了厚厚的沼泽水,他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与天不能舀。
和疏浚当干仍是一种气味 - 防蛀,防霉和腐烂 - 是许多年,有时看好消退,但难免回各立冬
。 芭芭拉是在村里从来没有见过 - 但表面上是因为其门可罗雀多年八卦,有时会传来沉闷和单调的婴儿哭声。
©玛莎 - koroleva
资料来源:
战争结束后,在一片混乱中消失了,许多人来说,外星人,相比之下,来了,一定是好的。也许,正是这些朝圣者在寻求更好的命运之一。她采取了最极端的空置房在林中,很老的和小的,并为十年,二十年开车把他送到总荒凉的状态。有时候,富有同情心的邻居修理她的屋顶,然后在染胡须喃喃自语:没有,好,谢谢,她雨水大声滴在取代骨盆,我做到了,它是干的,而野蛮人是不够的“谢谢”也不说,所以甚至没有看的脸。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活,他吃什么。她总是去了同样的衣服deryuzhki其下摆重与干泥。在相同的 - 但它的气味不厚麝香人类排泄物,这是不从皮肤洗涤,地下和模具。
后来有一天,在六十年代初期,当地的球员之一,有感动伏特加,他闯入她的家 - 无论podnachil谁,无论是抽象的女性气质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象并不重要。这是在五月份,安静的,明确的,满月的夜晚,朵朵草药和蟋蟀唤醒了密集的香味 - 以及整个村前庆祝胜利,发挥了手风琴,冶炼馅饼,喝,吃了,走了。男子名叫费多尔,这是二十五年。 [下一页]
他闯入瓦尔瓦拉的房子,已经有一次,在大厅里,比如他感到不安。房子是一种奇怪的气味 - 空虚和衰减。就连村里的酒鬼叔叔谢尔盖在家里闻到完全不同,虽然丙基灵魂早在那些日子里,当宝宝是费多尔。谢尔盖的叔叔闻到温暖的烤箱,再强悍,脏脚,酸奶,腐烂门垫 - 这是令人厌恶的,但在恶臭气味的不协调感觉让几乎沦落成的存在,但仍然有生命。和芭芭拉闻,仿佛房子就没有来了几十年 - 潮湿的地下室,尘土飞扬的窗帘和模具。陀突然很想转身走上自己的高跟鞋,但不知何故,他说服自己,这是不是“男人”。他向前移动 - 触摸,因为房子很黑 - 帘子的窗户在一些碎布月光。
捅露出双臂向前门 - 她屈服于一个安静,吱嘎开启。费奥多尔小心翼翼走了进去,稍微碰了头了吧 - 芭芭拉涨幅不大,门的房子 - 它匹配。房间中,他发现自己,是为暗费多尔很快就失去了方向的空间,但突然有人在角落里轻轻搅拌,动物的恐惧,从而导致大多数人的黑暗加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他的战士突然惊醒和野蛮。随着费奥多尔短一声,他冲上前去。
- 去 - 语音芭芭拉,安静和平淡,和费多尔敢发誓,他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许多人相信,在所有的偏心的最后一栋房子麻木,甚至在战争年代,却再也没醒过来。
她伸出手的地方,拉开窗帘,和费多尔终于见到了她 - 在蓝色灯光的月亮似乎平息死者的丑恶嘴脸。
- 这里还有一个! - 他试图声音欢快,而是因为所谓的兴奋“的一声公鸡”,并在自己的愤怒的,他流下了悲观的瓦尔瓦拉,戳他的拳头在她毫无生气的脸, - 来吧,来吧......我快。
她没有反抗,并给了他心灵的力量。 “也许她梦想着它,很高兴到死,不相信自己的幸福, - 他认为 - 一个人的东西,我想,二十年她,如果不是更多。
芭芭拉都包裹在一些碎布,像寿衣。他一样,顶部敞着外套,羊毛,但它原来是一种地幔,甚至更深层次的 - 东西,看起来像尼龙,滑,爽的感觉。最终,愤怒的,他拉抹布,而那些破解,几乎在他手中分崩离析。瓦尔瓦拉以及所有躺在寂静,伸展双臂在身体两侧,为死者,谁是准备洗澡。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和他心中的角落里,陀突然说,他们不发光。马特的眼睛,像个洋娃娃。
但是,他的血已经沸腾的熔岩希望倒出来,从火中释放他,他几乎是,谁将会解锁口 - 无论是女人温暖,poslyunyavlenny拳头还是这个灰色娃娃。
胸部芭芭拉就像一块空白的画布麻袋,其中费奥多尔的母亲把这坚果,它们聚集在树林里。它既不完备,也不乳房柔软度,和她的乳头就像木香菇,又粗又黑,触摸他们不想。那一刻仿佛想起西奥多岔 - 人们常常不明白,你怎么能要求它褪色蜡体是可怕的,恶心的相同,另 - 仿佛着了魔,只是一种盲目的意志,冲动和激情,因为它是。膝盖,他传播她的大腿 - 同样的冷静和灰如蜡和扳手插入她 - 西奥多的一部分,这是可怕的,令人厌恶的,它似乎是他的肉包括不是女人,但在投手与冷发酵出炉。里面芭芭拉是宽松,凉爽和潮湿。而现在,在她的种子壶嘴,费多尔离开,纠结于裤子的道路上。他觉得,如果他是春耕整天砍伐森林,但注销了这个弱点和头晕伏特加。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没有脱衣服,躺下来睡觉。
整个晚上,他做恶梦。他梦见自己走在村里的墓地,墓穴之间,并在各方面给他伸起双手沾满了地上。尽量把握裤腿,和手指有冰冷和坚硬。他的耳朵嗡嗡声站 - 缺乏果汁生命的声音哀求道:“而且我......和我......请......和我...»
在这里,在他面前的赛道上有一个女孩 - 她站在他的背后,脆弱,低,长麦头发散乱在肩上。她穿着婚纱。陀冲到她作为一个救世主女神,但她慢慢地转身,很明显 - 也死了。苍白的脸绿点去了一次丰满的上嘴唇半otgnila,牙齿露出,他的眼睛不亮。
- 我... - 她呆呆地重复 - 来吧......我故意埋在婚礼......我等了你...
费奥多尔从什么她的母亲泼他在冰水中的勺子面对醒。 “很opoloumel醉了!我沐浴到魔鬼和喊叫整夜,就好像我有铁的意志!»
它花了几个星期。起初陀无法摆脱痛苦的感觉,就好像它伸出了沉重的翅膀,它关闭了阳光。食欲,欲望笑,去工作,去呼吸。但渐渐地,他莫名其妙地恢复,苏醒,又开始问他的母亲早上煎饼,扫视着最美丽的处女村庄尤利娅长粗的辫子,并在他眼中的魔鬼。与芭芭拉,他尽量不见面 - 但是,这并不困难,她很少离开他的房子和花园,如果他们出去到村里的街道,然后蜷缩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尘土飞扬的套鞋,而不是冲突的人。渐渐的,奇怪的夜晚从内存中消失了 - 和费多尔甚至不是很确定,这是一个现实。他的心似乎雪球蒙蔽 - 真正的事实和相应的噩梦,甚至不明白 - 真相,那 - 一个可怕的形象,制造内部的黑暗。
冬天来了。
冬天的夜晚费奥多尔通常木工 - 手艺教给他的父亲,两个有金色的手。随着访问的市中心 - 谁把一个餐桌,有人来修理围栏,给谁,附着在房子的露台。
并于11月下旬,有一天,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 敲门声不停,就好像它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当陀打开 - 在街上空无一人。人打扰晚上安静的家庭一样溶解冰随地吐痰雨夹雪空间。只有在地板上,牵制潮湿的石头是白色信封。里面的钱 - 放眼望去,费多尔抱着他,看着里面,更惊讶。不是数百万,但巨额赔偿 - 所以他只是问了一个夏天的阳台建设。村里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件不寻常的 - 邻居肯定没有饿死,但为了节省钱不是在哪里,但对于所有的首选工作分期付款。加上从信封票据有附注。 “我问你做棺材,长度 - 1米材料 - 橡木或松木。拿钱马上,但是对于工作,我会做好准备的第一次机会。“
不容易受惊是费多尔,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内在的东西他去冷的时候读完。长度 - 1米。原来,棺材 - 孩子。为什么是他愿意付出这么多?如果客户问他价钱,费多尔称之为一笔二十次小,也不会认为自己得罪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奇怪的方式进行预约?这样的悲伤,从别人的厌恶?但事实证明,他甚至不是一个选择离开 - 给谁钱回来了?你当然可以,并让他们在信封,当客户将,门槛摆在你的脸上。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孩子死亡。而且,人们会来的,并没有什么准备。毛巾把他埋了还是怎么的?
这是辛苦费多尔的灵魂,但他仍然执行的工作。对于两个晚上议会。最好的主板了,试过好像棺材为帝王珍宝一样。即使雕刻装饰盖 - 做一些事情还是冬天的夜晚没有什么。
一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又接着开始了第三,但工作,所以没有人来了。小棺材站在已狭窄的通道和代理都紧张。走过了他,父亲费奥多尔严肃地说:“etit ......”,和他的母亲,他的绊脚石机械打腿残之一,于是来到她的感觉,坐在阶梯并简要哭了。
现在,在新的一年一次出色的晚上,当西奥多离开家独自一人。父母和妹妹去附近的村庄探亲,并打算在那里过夜。
夜是黑暗和暴风雪 - 茂密的冰雪披肩地球,也不是天上不会看到
。 突然,敲门声 - 同一个持久急忙敲费奥多尔马上签下他,而他的心脏蓬勃发展 - 仿佛带着无限冰冷的山。
小心找上门来,他问 - 谁,但是,他没有回答。为什么,然后传给自己,他打开门 - 在门廊上是一个小女人,裹着一件夹克和一个大的羊毛披肩。他甚至不承认它瓦尔瓦拉 - 当它看到灰脸无表情,退缩了。
- 你想要什么?为什么priperlas? - 在故意无礼,他试图汲取力量。
- 现在是时候 - 平淡,她说,走了进去过去他 - 我想了几个星期穿,但现在我看到有。它的时间。
- 什么是你讲的东西durischa?去otkudova priperlas。
然后芭芭拉提出了她的脸,他走了几步,他的眼睛飞奔到前庭无奈,直到埋在一个小斧头,这是他和他的父亲切芯片照明炉子。 “布拉德一些。所以我不会在她的,女人弱,用斧头......我是她的手指pereshibit可以说,她做一些事情,惨......”女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像斑点冰水坑。同样的沉闷和木偶一样的那个晚上,他这几个月试图忘记。
芭芭拉笑了笑 - 仍然没有感情。
- 你是什么,陀思porazvlecheshsya并没有回答。带上水和抹布,我生下。
- 你他妈的...... - 然后才在她敞着上衣巨大的圆腹看到
- 任何分钟,现在开始,你还等什么的
。 她一点也不像你所关心的关于女人的第一个出生的外观。无血平静的面容,干裂的嘴唇,即使是很小的声音。
- 再说,我付出。所有诚实的。做了什么,我问?我管理的?
费多尔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当他意识到突然觉得小和手无寸铁的。由于在那些日子里,当他的父亲把他吓得leshim和班尼科夫,和陀那么整个晚上试图平息气息 - 这一切想象中的噪音和哒,一些其他的,隐藏的成人生活,开始在家里的时候都去睡觉了。我想冲上去他的母亲,呼吸舒缓温暖,但耻辱阻止。
- 为什么要你......棺材? - 几乎是耳语的最后一句话,他呼吸面对野蛮人。
- 嗯,当然 - 她笑了 - 地方,因为他想睡觉。 Mertvenky事实上诞生了 - 和抚摸着他的绷紧的胃。
费多尔生病。
- 水正在成为, - 指挥瓦尔瓦拉 - 阻力和破布。开始。
作为一个梦想,他来到了烤箱,她拿着一个水壶,然后爬进后备箱的母亲发现了一些旧床单。一切,是发生在他身上似乎愚蠢的笑话。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村白痴,真理会生出他的门廊,他将不得不参与其中。而该死的钱,棺材。 “Mertvenky出生,因为...”
当西奥多回到了门口,他正躺在地板上,用他的裙子和分开不流血的腿,她的背部拱起,仿佛女子被雷电击中,但人依然没有表示任何畏惧,无痛苦,无期待。
西奥多姐姐,也出生在家里 - 突然回合开始,这是冬天也一样,他们没有时间开车去乡村医院。他想起了母亲,她的子宫喊的满脸通红,满身是汗的脸,更像是一个野性的咆哮,记起摊开她的沾有汗液,头发,什么气味在房间枕头 - 一热,密室内,他怎么也没有本身 - 但后来又有恐惧,有一定的永恒的规律存在的恐惧。母亲接着问喝,然后把她的额头上一把雪,然后在打开的窗口,然后将其关闭。然后,他听到了一声闷响小妹妹,她和她父亲喝了饮料,高兴之余,她的母亲看起来很开心,尽管所有的被子都湿透了她的血。
芭芭拉默默的,他的牙齿,生出了新的生活,她在她的臀部和背部 - 巧妙,像蛇一样,也是充满异味的树冠 - 泥炭沼泽,堆肥,湿树根,雨蠕虫。突然出来的匆忙,好像阀门被打开 - 一个绿褐色,为停滞的池塘水。费多尔不得不跳 - 水是臭烘烘的,以至于在走廊整个地板被水淹没。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泔水从她的子宫选择到的光的小家伙,一个婴儿,一个灰色的,毫无生气的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村,他的手背擦了擦额头,离开地面的婴儿 - 他懒洋洋地提出他的手。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戴了面纱像一个白色薄膜。费多尔扭过头去 - 看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不愉快的,什么不是。他甚至哭了,但转过头,明显是想看看周围。
- 你站在 - 严肃地叫芭芭拉 - 你需要剪断脐带。阿里没有读过书。
- 我不知道 - 从疲惫和厌恶,几乎昏厥,他喃喃自语
。 - 还有什么能。还有斧头是 - 他们砍伤。
- 你在说什么。就是嘛,你可以,用斧头。现在,我会打电话给奶奶阿列克谢耶夫 - 突然来到他拯救的想法 - 只要运行它。她知道如何处理。
- 任何人都不应被调用 - 瓦尔瓦拉叫住了他 - 他自己有罪,他会作出反应。把斧头......我来教你。而棺材携带。他已经想睡觉,你看。
- 芭芭拉,为什么还要棺材,你说的是可怕的 - 无法抗拒费多尔 - 哪里是在一个棺材样给宝宝睡着了。你说 - mertvenky诞生了,在这里,他是 - 移动。
- 所以我mertvenkaya - 灰色的嘴唇拉长,但它不是像一个微笑 - 阿里不明白? ......进棺材。而最需要放松。而其实他很快就饿了。在这里,你醒来,我会教你如何喂养mertvenkih。
最后一件事,他看到费多尔,在他覆盖了黑色的天鹅绒翼是旧的,分支到缝隙,天花板上。
第二天早上,他的父母和姐姐回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冷却下来,但睁着眼睛一直保持痛苦的警惕的表情。他怎么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但整个楼层走廊被水淹没了厚厚的沼泽水,他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与天不能舀。
和疏浚当干仍是一种气味 - 防蛀,防霉和腐烂 - 是许多年,有时看好消退,但难免回各立冬
。 芭芭拉是在村里从来没有见过 - 但表面上是因为其门可罗雀多年八卦,有时会传来沉闷和单调的婴儿哭声。
©玛莎 - koroleva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