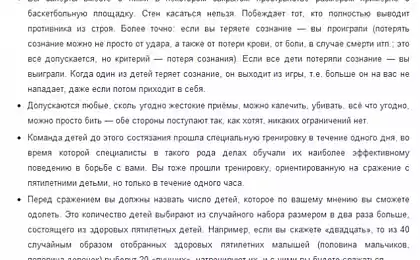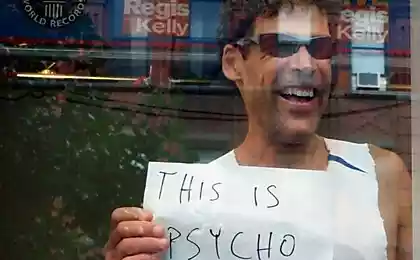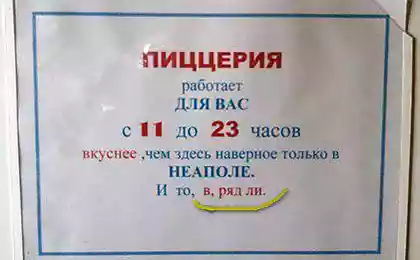682
这是什么 - 冻死在运行
“我曾在铁路部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米努辛斯克和阿巴坎之间。我们在那里倒有些轨道。我们进行了第66次KrAZ,电池是只有一台机器。植物:我们把一只KrAZ,随着电池,并开始拖累其他KrAZ的针叶林,在路上。他随身携带约20分钟,伤口与推进器。他然后工作了,只要发动机不溢出,直到他去世。一个月站立,另一半放着。如果你停滞不前 - 全部告别。停滞在轨道上 - 和你好。而在春,夏工作,秋 - 好吧,吓人。但到了冬天它是可怕的。搪塞路在林中的 - 恐怖电影。我活了下来。
我服了一年,已经有一个初级士官,排长,并在后期制作的高级二传手。它发生,我几乎停止了车来车往。然后,它起到了致命的作用。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是值班的公司。职务队出于某种原因,他工作的夜班,我不得不把他们的食物。但它名曰 - 食物。水箱注满水后茶,罐通常是连洗净,削皮几乎冲到了土豆,鲱鱼黑色和棕色的品种,其中20年被某处仓库腌制,然后煮熟,整个浆。鲱鱼与土豆去掉 - 这是第二次,和第一 - 棕色,黑色和深红色浆。即使是面包给出。他是冷冻和潮湿。他切碎用斧头。
和两罐这些美味佳肴责任司机不得不采取夜班。但司机太累了,我只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什么,甚至不说话。当我坐在房间里,感觉很好,我决定去为他感到遗憾。霜冻是零下35。如果你吐,下传来了一块冰。[下一页]
正如我曾在房间,去了赛道只是断断续续的,我穿着河北所谓的夏天。我们称这种形式的玻璃,因为它实际上是合成和洁如玻璃。在Steklyashka是冬天的衣服,他的脚 - 篷布靴。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夏天的衣服。所有谁工作外,在工作靴的士兵,靴子是没有套鞋。因此,我们被禁止热身,站在消防超过一米半紧密,因为那时融化的雪靴和他们成为湿。篝火,顺便说一下,烧全天候。烧毁数十吨的KrAZ全新的轮胎。是的,我们已经晒 - 轮胎
。
在一般情况下,我坐在KrAZ去的道路上。去土,他们工作的人有一个小十多公里的沉积的地方。我到达的地方,卸罐,抽着烟,就回去了。和5公里是幻灯片上是必要的,包括一个下部齿轮。 KrAZ第三和第五档平行排列,很容易混淆。而且我不开车经验 - 卡住第五档安全,并立即熄火,在针叶林的中间。电池没有。所有断电。本机是很酷。我坐10分钟 - 在驾驶舱负。然后我刺穿野生恐惧。在一秒钟。我意识到,我在她的玻璃和床单之一。我记得作为挺举和寒冷的一个已经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只是下了车。我算过了因地形的自然拖车不再运行。之前部分 - 六,七公里。就跑。我甚至没有上限,什么都没有。这种玻璃在寒冷变得1秒真的很喜欢玻璃,让我,其实,有一个内衣。
我很动感,静静思考了一个小时的这六款公里。但不知何故,我通过针叶林正在运行。试想一下,那里的道路?这不是昂贵的,它只是穿越了丛林和轧制gryazische其冻结的冻结。它看起来像覆盖着一些巨大的钻石,具有巨大的坑洼表面,被撞机多年。 KrAZ这条路在11公里大概两个小时。
地方40分钟运行后,我意识到,我专门航行,因为不觉得他的腿。他们只是两个甲板,二重的木块,甚至是一块铁的砸在地上。 Footcloths've失去了时间。但退我没有可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下来,我小艇。只要运行。此外,我完全呆住了他的耳朵。然后,我把他的衬衣了他的裤子,并把它放在他的头上 - 只是主频了,因为我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耳朵运行。我离开了她在我的怀里,在这样的背部和主频包裹在头上,震撼。我只是看着出来的鼻子和眼睛。但我已经看到了糟糕的,因为我有,而不是眼睛只有两个雪堆。
我跑啊跑,在某些时候,我意识到: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提前看到了什么。意识包括片段。我不知道多少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多久,我跑了 - 百米或一公里我唯一知道的地方非常接近的那部分,我还在推进。
呼吸变得非常痛苦。就好像我的胸部是COM - 第一把火,然后冰。然后我停下感觉喉部。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与意识 - 这是不可分割的。有一个,是非常有害的,他说:“沃洛佳,来吧,让我们跑。”而且还有一个柔软宜人,好撒玛利亚人,谁说:“一切都已经。放松。别担心。你会找到。你来。你已经做的伎俩。“第三,我与他们运行。我不停止。然后,我完全停止感到身体 - 胳膊或腿。我觉得我 - 一个庞大的身躯,一个陌生的,什么地方飞
最后一件事,我看到 - 一个明星。明星在雾中。但不是从天上。我们在检查站又轻又出现了某种障碍上是一些明星。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不知怎么知道我的使命已经结束,只是晕了过去。我晕倒了障碍,因为身体已经决定,我已经达到的目标。
当我还在跑,和意识mutilos,我在想:什么样的父母说,说 - 死在战斗职责或壮烈牺牲?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如果我给苏联追授英雄?我才19岁,我从小在苏联,和主人公的明星是如此令人垂涎。甚至当我运行出于某种原因,大概要冷静回忆青蛙假死:一百年,他们是 - 仅此而已。我将一无所获。他想起了婴儿猛犸迪马和他的狗otela树干。全沙拉是在我的头上。一般来说,我认为冷血。它就像一部电影的某种。然后,当他倒下了,几秒钟就见到家人的照片 - 与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如,我看到照片的哥哥,但如果他有70年。这位老人,但我明白,这是它。然后 - 一切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有kombatovoz,谁去来回一个士兵,因为他有一个女人的地方。这是在早上五点,他回到了一部分。由于道路是可怕的,他去缓慢而痛苦。我躺在马路对面,像日志。他担心罢工,并停止丢弃日志从道路,看见我。他拉着我的衣领Zavoloka迅速进入一辆汽车,带到一部分。
我前来观看上午10时。当然,我愣了所有的肢体。他们把我放在床上。家伙,我已经脱落了毯子,裹,喝热茶。再有就是疼痛。无处不在。腿。手中。眼睛不开了,耳朵都在燃烧。起初我不明白,但后来我看到了士兵,并意识到我在那里。他立刻变得很痛苦,我惩罚,因为我去了,扔了另一辆车。我冻伤,当然,所有的脚趾和手,耳,鼻。直到案发命令隐藏的晚上,然后我被带到米努辛斯克并放置在医疗单位。我惊恐的几天等待断指。他们是黑色的。和医生决定每天 - 切手指或没有,嘲笑我Meresyev。耳朵也完全黑了。但与坏疽成本。我没有受到伤害。
自9月底至5月底我穿皮毛一体的靴子和羊毛手套,因为,即使在温度加5-7,我的手指发麻,脚和手。我没有一件T恤衣领。我身穿衬衫和领带的西装总是解开上面的按钮。否则,是不可能的。我当时规定7天警卫室。但是,没有一天我绝对不会饱和整整10年后,我在中士的以色列军队。并有这么热,一个会死。但热量,对我来说,最好是冷»。
©弗拉基米尔戈尔巴赫,商人,46年通过埃斯奎尔

来源:
我服了一年,已经有一个初级士官,排长,并在后期制作的高级二传手。它发生,我几乎停止了车来车往。然后,它起到了致命的作用。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是值班的公司。职务队出于某种原因,他工作的夜班,我不得不把他们的食物。但它名曰 - 食物。水箱注满水后茶,罐通常是连洗净,削皮几乎冲到了土豆,鲱鱼黑色和棕色的品种,其中20年被某处仓库腌制,然后煮熟,整个浆。鲱鱼与土豆去掉 - 这是第二次,和第一 - 棕色,黑色和深红色浆。即使是面包给出。他是冷冻和潮湿。他切碎用斧头。
和两罐这些美味佳肴责任司机不得不采取夜班。但司机太累了,我只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什么,甚至不说话。当我坐在房间里,感觉很好,我决定去为他感到遗憾。霜冻是零下35。如果你吐,下传来了一块冰。[下一页]
正如我曾在房间,去了赛道只是断断续续的,我穿着河北所谓的夏天。我们称这种形式的玻璃,因为它实际上是合成和洁如玻璃。在Steklyashka是冬天的衣服,他的脚 - 篷布靴。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夏天的衣服。所有谁工作外,在工作靴的士兵,靴子是没有套鞋。因此,我们被禁止热身,站在消防超过一米半紧密,因为那时融化的雪靴和他们成为湿。篝火,顺便说一下,烧全天候。烧毁数十吨的KrAZ全新的轮胎。是的,我们已经晒 - 轮胎
。
在一般情况下,我坐在KrAZ去的道路上。去土,他们工作的人有一个小十多公里的沉积的地方。我到达的地方,卸罐,抽着烟,就回去了。和5公里是幻灯片上是必要的,包括一个下部齿轮。 KrAZ第三和第五档平行排列,很容易混淆。而且我不开车经验 - 卡住第五档安全,并立即熄火,在针叶林的中间。电池没有。所有断电。本机是很酷。我坐10分钟 - 在驾驶舱负。然后我刺穿野生恐惧。在一秒钟。我意识到,我在她的玻璃和床单之一。我记得作为挺举和寒冷的一个已经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只是下了车。我算过了因地形的自然拖车不再运行。之前部分 - 六,七公里。就跑。我甚至没有上限,什么都没有。这种玻璃在寒冷变得1秒真的很喜欢玻璃,让我,其实,有一个内衣。
我很动感,静静思考了一个小时的这六款公里。但不知何故,我通过针叶林正在运行。试想一下,那里的道路?这不是昂贵的,它只是穿越了丛林和轧制gryazische其冻结的冻结。它看起来像覆盖着一些巨大的钻石,具有巨大的坑洼表面,被撞机多年。 KrAZ这条路在11公里大概两个小时。
地方40分钟运行后,我意识到,我专门航行,因为不觉得他的腿。他们只是两个甲板,二重的木块,甚至是一块铁的砸在地上。 Footcloths've失去了时间。但退我没有可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下来,我小艇。只要运行。此外,我完全呆住了他的耳朵。然后,我把他的衬衣了他的裤子,并把它放在他的头上 - 只是主频了,因为我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耳朵运行。我离开了她在我的怀里,在这样的背部和主频包裹在头上,震撼。我只是看着出来的鼻子和眼睛。但我已经看到了糟糕的,因为我有,而不是眼睛只有两个雪堆。
我跑啊跑,在某些时候,我意识到: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提前看到了什么。意识包括片段。我不知道多少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多久,我跑了 - 百米或一公里我唯一知道的地方非常接近的那部分,我还在推进。
呼吸变得非常痛苦。就好像我的胸部是COM - 第一把火,然后冰。然后我停下感觉喉部。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与意识 - 这是不可分割的。有一个,是非常有害的,他说:“沃洛佳,来吧,让我们跑。”而且还有一个柔软宜人,好撒玛利亚人,谁说:“一切都已经。放松。别担心。你会找到。你来。你已经做的伎俩。“第三,我与他们运行。我不停止。然后,我完全停止感到身体 - 胳膊或腿。我觉得我 - 一个庞大的身躯,一个陌生的,什么地方飞
最后一件事,我看到 - 一个明星。明星在雾中。但不是从天上。我们在检查站又轻又出现了某种障碍上是一些明星。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不知怎么知道我的使命已经结束,只是晕了过去。我晕倒了障碍,因为身体已经决定,我已经达到的目标。
当我还在跑,和意识mutilos,我在想:什么样的父母说,说 - 死在战斗职责或壮烈牺牲?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如果我给苏联追授英雄?我才19岁,我从小在苏联,和主人公的明星是如此令人垂涎。甚至当我运行出于某种原因,大概要冷静回忆青蛙假死:一百年,他们是 - 仅此而已。我将一无所获。他想起了婴儿猛犸迪马和他的狗otela树干。全沙拉是在我的头上。一般来说,我认为冷血。它就像一部电影的某种。然后,当他倒下了,几秒钟就见到家人的照片 - 与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如,我看到照片的哥哥,但如果他有70年。这位老人,但我明白,这是它。然后 - 一切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有kombatovoz,谁去来回一个士兵,因为他有一个女人的地方。这是在早上五点,他回到了一部分。由于道路是可怕的,他去缓慢而痛苦。我躺在马路对面,像日志。他担心罢工,并停止丢弃日志从道路,看见我。他拉着我的衣领Zavoloka迅速进入一辆汽车,带到一部分。
我前来观看上午10时。当然,我愣了所有的肢体。他们把我放在床上。家伙,我已经脱落了毯子,裹,喝热茶。再有就是疼痛。无处不在。腿。手中。眼睛不开了,耳朵都在燃烧。起初我不明白,但后来我看到了士兵,并意识到我在那里。他立刻变得很痛苦,我惩罚,因为我去了,扔了另一辆车。我冻伤,当然,所有的脚趾和手,耳,鼻。直到案发命令隐藏的晚上,然后我被带到米努辛斯克并放置在医疗单位。我惊恐的几天等待断指。他们是黑色的。和医生决定每天 - 切手指或没有,嘲笑我Meresyev。耳朵也完全黑了。但与坏疽成本。我没有受到伤害。
自9月底至5月底我穿皮毛一体的靴子和羊毛手套,因为,即使在温度加5-7,我的手指发麻,脚和手。我没有一件T恤衣领。我身穿衬衫和领带的西装总是解开上面的按钮。否则,是不可能的。我当时规定7天警卫室。但是,没有一天我绝对不会饱和整整10年后,我在中士的以色列军队。并有这么热,一个会死。但热量,对我来说,最好是冷»。
©弗拉基米尔戈尔巴赫,商人,46年通过埃斯奎尔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