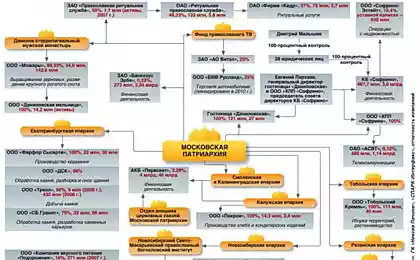677
在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和不信的感受
事有凑巧,我出生,长大后,我在一个非常世俗的国家的人的形成。教会有从国家分离,如果不是圣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附近,我怕我会做的大多数并不知道某种宗教,神,教会的存在,任何事情,都等。
不用说,家里没有宗教的影子。学校没有讨论宗教问题。在圈内,在那里我的父母在谈论一个社会 - 我们都完全过无神论者或接近他们。是的,其实这样的问题没有表态。在大街上,并在院子里我周围都是普通的人,我厂的工人,知识分子的职业有一个 - 一个医生的医疗单位,因为它也有宗教题材ugaral一次也没有。
在该国的教会是最好的一个博物馆。在最坏的情况,他们储存的土豆和幻想之外(马铃薯仓库)架构它与普通的建筑没有差异。
我只想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与东正教第一次遇到:我们来到他父亲的亲属在城市弗拉基米尔。在这里,他们必须有某种原因,他们都非常虔诚的,在今天的话来说 - 教堂里。但我不知道它,让我吃惊......图标!在红色角落。不,还有,我还真没见过。这是关于那个时候我八年,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呢?目前仍然烧毁灯......老实说,我不记得我被告知,我只记得那个房东表明,必须祷告。
我不喜欢。它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我的oktyabryatskoy中的其他一切(淡入先驱)的现实。祈祷的人... ...在某些主板zakopchёnye......我不明白的芯片。
第二次会议举行不错凭借良好的五年后,当我十三左右。我们继续这个非常寺院,三位一体,谢尔盖之旅。劳勒斯和苏联政府行事院子里是80年代中期,有提出(这一天公寓)的温床,而所有的:三位一体谢尔盖大修道院 - 东正教的一个严重的中心。这是写在任何手册。
......这是深秋。天渐渐黑了早期。斯诺没有。因此,这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在我们区一个特别不舒服,桂冠也让我郁闷压抑的印象打扮,因为高罩一身黑,(CAPS他)看似庞大,可怕的黑胡子腹牧师;至少有面色狰狞成群,但有一点液体borodёnkami,修道;修女永恒的,所有 - 黑色,深,脸面都分离(最好),有时公开的敌对,可疑。和周围 - 奶奶,老,衣着破旧,也不知何故一切邪恶...
教堂里 - 黑暗,沉重的泥浆我在一个完全黑暗的角落迄今看不见的气味,需要一定的蜂拥 - 是一个老女人,但是邪恶的眼睛放光:时尚可言,因为吵架的教区居民,游客,并与对方。照明 - 只蜡烛,但油灯。我看不到一个该死的,而是来和亲吻墙(在我看来,这样在第一,因为我看不到图标)。
......而在入口处的修道院坐在我到这地步了前所未有的人群残废和乞丐,乞讨。我看见乞丐,削弱可见。在莫斯科三站,他们当时并不罕见。而在其他地方(我们走过了很多与我的家人)对面。但如此多在一个地方一次 - 样通过了战书。这最后的印章图片:我了解到,有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的妇女接吻的牧师修饰外表的手在他的胡须屑,它们遮盖他们凝重的交叉;在这里一切都服从于某些僵化的礼仪千百年来,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从普通的自来水,一个程式化的交叉,平水是流动的,但它是水 - 神圣的,而且是必要的她站在队列;我们一定要吻描绘在画脚,吻在玻璃上,这是很好的,如果至少偶尔抹任何东西,消毒,同时要了解什么是描绘及他为什么要吻,把蜡烛 - 是不可能的,没有专业知识或经验丰富的民族志学者腋下。
在回来的路上,他的父亲,谁也不喜欢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这一天,顺便说一句! - 笑着告诉他如何小,在战争期间取自罪村奶奶外公。我的祖母是虔诚的,拖着他每个星期天去教堂。然后用力祈祷,忏悔,接受圣餐,等等。这座教堂很远了,我们几乎凌晨四点,pizdyuhat近十到十五公里,冷参观教堂不能只在圣餐的父亲,等前吃什么 - 总之,它是激情不喜欢这个东西,而且自那时以来一直保持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
他们回到家里,我忘了这件事。对于我的生活就是宗教的不平凡的地方是,从不看它了一百俄里社区,随处可见。无论是你的图标或交叉。和好了。我们如何生活。即使没有那么糟糕。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同时,在我国不信神的人开始前总churching的过程。教会冲到人群的最广泛的领域:从区委书记到土匪和小伙子们
。
对于后者我的秘书见过。而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了解自己的推力教会的原因造成可恶的浮华,而是认真虔诚。那我甚至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在战争中。其实小伙子们的生活是短暂的,像跑步烟花,爆竹:闪光短暂的飞行,嘘 - 所有。当生命悬于一线,这是很平常的人,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并认为他们是受保护的。而在一般情况下,它仍然是许多工作要做没什么不可以。忽然帮助吗?更糟的是,它只是不会...
我记得在教堂Tarasovka(在我们的教堂的一部分颇为流行)的男生去组织一个礼拜日。我带着我。呵呵......如果一个线程,现在,如其他博客可以想象出我的脑海发布 - 二伟,开始在评论!油画:流行音乐,然后服务唱诗班唱歌,吓得蜷缩在墙壁上的DIB,ZENK只盯在教堂前 - 德美汽车业的颜色,然后,全黑的无烟煤,并在寺庙的中心......他们。公牛...剃光头,黑色皮革几乎是从肌肉爆裂,另一种是健康的相互多头。低着头,交叉,gubёshkami巴掌......我已经那么,坦率地说,我有点razvidet吧!
然后,一定要 - 把一支蜡烛。巴布卡什么,只是生活在恐惧之中,vytsepit并得出问题在哪里放置敬酒,这对于和平,在那里 - 到rebёnochka有......嗯,在输出端 - 捐赠。谁是凉爽。
它并没有帮助他们,顺便说一句。在六个月内,几乎全部阵亡。但是,这些谁被杀死 - 也是在教堂,然后去了。而且,或许,是相同的。那么,如果卡拉什汽车离开...
然而,在同一时间,有一个短的路,我churching。
生活是不含糖。虽然我对小伙子们,而不是一个,而是属于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简单地说 - 一个叫卖。俄罗斯 - 区域风险的农业,甚至在业务方面 - 所以最后。也够问题。而一些莫名其妙前后左右都是虔诚的,交叉的维度就是不衡量,即使是我们的女儿,然后是获得乐趣 - 突然响起一个星期六的洗礼。好吧,这是我决定的。
流行音乐我很熟悉。当我问他 - 他告诉了我一切。而且,是的,我忘了说:我不洗,当然。
好了,他告诉我说,好,你首先需要承认。
我想我是认真的。非常重视。事实是,唯一的罪过就是我 - 这是我的处女放弃。在我看来,这罪是完全由谁投掷了我又处女的数量抵消。那么事实是,没有,我没扔,不杀生,不偷盗,贿赂,即使他们不得不放弃 - 一分钱,有趣。然后其他的腐败不严重,早在90多岁。在一般情况下,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交代什么?
而亵渎神灵的想法杜比卑鄙的我一路到大脑。我什么都不知道神学,但一些已经在考虑中的项目管理。妈的,如果他有我的poebulek的事情 - 我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如果他不关心 - 这就是我要撼动空气中的牧师东西,他的性面前,是吧?
磨擦他的心脏和灵魂,思想临死前告诉你关于爱情和学校的罪取笑教师?欺负。嗯,这是。更要告诉汽车是如何被盗的有一天,一个醉汉。骑走了。更告诉如何tyril钱和车的父母,顺便说一句,太 - 车程。所以也,就没什么事。我收集了起来。
在这一天,我走了,你也知道,到教堂。所有这些开明的。它提供我的祭司。他毕业于服务,走了,笑得很开心。我立刻开始业务,友好的交谈:
- 听着,你说你必须有一个自定义的连接?你能帮助Kruzak通关? Kruzak驱动我在这里... - 并按照Kruzak的主题,驱使他,在很长的,Mlýn的!
他是无罪的。他显然忘了思考我的问题,我没让一个人的印象,谁能够认真来找他承认,接受洗礼,当时的笑。
不过我喜欢水的桶冲了过来。什么是你的,怕啥,ohuel相当chtol?!谁是 - 一个忏悔?牧羊人?你上周stopisyat雄鹿队坚持了6惠斯特的苦难?!
并且如果其他?好了,其他一些其他的Hvatkinu帕夏坚持stopisyat美元。而对于如果太守好,没有大麻。或桑拿与女孩。
Sdurel chtol你呢?他们 - 的人,其他人一样。凭借同一套pripizdey和蟑螂。也许更糟。也许更糟。
......我们聊到了牧师的Kruzak,我答应帮他解决问题,并在左边。他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并问:我是什么,其实,即使是在教堂里来的呢?你以为只是为了他的电动助力海关的贪婪?嗯,这样的精神之父忏悔...
但后来有一些churching再次发作。已经是地方 - 我们的家庭。生病的母亲。当他们宣布了可怕的诊断,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抓住任何可能以某种方式取得成功。
然后向国外仍然悬而未决,货币是值得非常生气货币基金不存在,保险是不存在的,我们的药已经然后 - 完整的狗屎。这就是我想说的苏联免费医疗。妈的刚才,因为苏联的保持不变,但变得越来越支付高昂的价格。然后真正的癌症中心,如医生建议Urinotherapy尝试......作为一个选项...查看?然后时尚是在所有的传统医学,而不是所谓的传统。女巫,算命,巫师,民间医者......他们的军团!而关于每一个谣言有它这就是它 - 创造奇迹,叫死人从坟墓,现场恢复活力二十多年来,阴茎与乳房增大,既概括又特别。
当然,你知道,这一切是不管是谁,以及如何这个垃圾在追逐什么级别的完整的垃圾。但是,我们不能以其他方式:你不能说给心爱的人 - 妈妈,我们不会处理这些垃圾,你死 - 你死了,因为......给我一个人谁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与主要的事情 - 做。
这家由治疗师赶到女巫从呱呱 - 顺势疗法,不忘对目前的教授和灯具国内医药(关于这些和母亲灯具历时三年)。
更接近高潮来了一个牧师。已经从彼得。他是谁,在哪里谁推荐他 - 一些熟悉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牧师可言,所有的目光都散发这样的彩旗!乐于助人,安静,妈妈坐在床边,嘀咕了一整天。
妈妈说 - 很容易,当他正跟她说话。而且他对上帝,圣经......好吧,如果更简单 - 坐,然后。他坐在那儿。每一天,为作业。没有钱,没有什么他没有。你看,一个圣洁的人。
......但是,他成为了他们所有的传统治疗师和治疗师建议。和许多早期的不同,他们只花了现金,以及更多。女巫,茶香菇木耳在做,天知道是什么,那么饮食,以符合要求的,那么这个世界否认,然后 - 所有孩子立刻跨越奠定了......我们不会介意的 - 这对母亲的健康不就已经聚集交叉设置(虽然我胆怯地坚持,有过适合于需要支付:让母亲率先复苏 - 困难时,我没有找到一个东正教)。
但它并没有再次发生,在我母亲去世了。
牧师站了起来,揉揉她的手和抚摸borodёnku,轻轻地,平静地说,“上帝给了 - 上帝已经采取了”我真想打他,但这样的人能够在太空解散...
贝斯,一个字。
妈妈才49岁......
......所以后来我已经对祭司和中华民国严重的投诉。这是为什么呢?是的,因为我还是只能假设有一个上帝,或任何更高的功率,因为它不叫。难道他(她)的任何关于我母亲的命运?我不知道。但牧师是准确的。而我现在知道:这里也没有神在其中一点比全多 - 所以这是他们!
我没有为我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与教堂里。如果你只是不知道中华民国什么,我是无所谓吧,毕竟上述与其成员的沟通,所有的这些故事,我开始认真地对她的敌意。
现在我看起来像一个教堂有趣的交配日夜与国家,挥舞着旗帜,据我所知,我的儿子,如果他们想成为能说什么,我能说的是:我在一个非常世俗的国家长大了!
当然,如果国家不改变。
可悲的是,先生们,同志们。
©baxus

资料来源:
不用说,家里没有宗教的影子。学校没有讨论宗教问题。在圈内,在那里我的父母在谈论一个社会 - 我们都完全过无神论者或接近他们。是的,其实这样的问题没有表态。在大街上,并在院子里我周围都是普通的人,我厂的工人,知识分子的职业有一个 - 一个医生的医疗单位,因为它也有宗教题材ugaral一次也没有。
在该国的教会是最好的一个博物馆。在最坏的情况,他们储存的土豆和幻想之外(马铃薯仓库)架构它与普通的建筑没有差异。
我只想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与东正教第一次遇到:我们来到他父亲的亲属在城市弗拉基米尔。在这里,他们必须有某种原因,他们都非常虔诚的,在今天的话来说 - 教堂里。但我不知道它,让我吃惊......图标!在红色角落。不,还有,我还真没见过。这是关于那个时候我八年,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呢?目前仍然烧毁灯......老实说,我不记得我被告知,我只记得那个房东表明,必须祷告。
我不喜欢。它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我的oktyabryatskoy中的其他一切(淡入先驱)的现实。祈祷的人... ...在某些主板zakopchёnye......我不明白的芯片。
第二次会议举行不错凭借良好的五年后,当我十三左右。我们继续这个非常寺院,三位一体,谢尔盖之旅。劳勒斯和苏联政府行事院子里是80年代中期,有提出(这一天公寓)的温床,而所有的:三位一体谢尔盖大修道院 - 东正教的一个严重的中心。这是写在任何手册。
......这是深秋。天渐渐黑了早期。斯诺没有。因此,这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在我们区一个特别不舒服,桂冠也让我郁闷压抑的印象打扮,因为高罩一身黑,(CAPS他)看似庞大,可怕的黑胡子腹牧师;至少有面色狰狞成群,但有一点液体borodёnkami,修道;修女永恒的,所有 - 黑色,深,脸面都分离(最好),有时公开的敌对,可疑。和周围 - 奶奶,老,衣着破旧,也不知何故一切邪恶...
教堂里 - 黑暗,沉重的泥浆我在一个完全黑暗的角落迄今看不见的气味,需要一定的蜂拥 - 是一个老女人,但是邪恶的眼睛放光:时尚可言,因为吵架的教区居民,游客,并与对方。照明 - 只蜡烛,但油灯。我看不到一个该死的,而是来和亲吻墙(在我看来,这样在第一,因为我看不到图标)。
......而在入口处的修道院坐在我到这地步了前所未有的人群残废和乞丐,乞讨。我看见乞丐,削弱可见。在莫斯科三站,他们当时并不罕见。而在其他地方(我们走过了很多与我的家人)对面。但如此多在一个地方一次 - 样通过了战书。这最后的印章图片:我了解到,有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的妇女接吻的牧师修饰外表的手在他的胡须屑,它们遮盖他们凝重的交叉;在这里一切都服从于某些僵化的礼仪千百年来,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从普通的自来水,一个程式化的交叉,平水是流动的,但它是水 - 神圣的,而且是必要的她站在队列;我们一定要吻描绘在画脚,吻在玻璃上,这是很好的,如果至少偶尔抹任何东西,消毒,同时要了解什么是描绘及他为什么要吻,把蜡烛 - 是不可能的,没有专业知识或经验丰富的民族志学者腋下。
在回来的路上,他的父亲,谁也不喜欢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这一天,顺便说一句! - 笑着告诉他如何小,在战争期间取自罪村奶奶外公。我的祖母是虔诚的,拖着他每个星期天去教堂。然后用力祈祷,忏悔,接受圣餐,等等。这座教堂很远了,我们几乎凌晨四点,pizdyuhat近十到十五公里,冷参观教堂不能只在圣餐的父亲,等前吃什么 - 总之,它是激情不喜欢这个东西,而且自那时以来一直保持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
他们回到家里,我忘了这件事。对于我的生活就是宗教的不平凡的地方是,从不看它了一百俄里社区,随处可见。无论是你的图标或交叉。和好了。我们如何生活。即使没有那么糟糕。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同时,在我国不信神的人开始前总churching的过程。教会冲到人群的最广泛的领域:从区委书记到土匪和小伙子们
。
对于后者我的秘书见过。而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了解自己的推力教会的原因造成可恶的浮华,而是认真虔诚。那我甚至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在战争中。其实小伙子们的生活是短暂的,像跑步烟花,爆竹:闪光短暂的飞行,嘘 - 所有。当生命悬于一线,这是很平常的人,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并认为他们是受保护的。而在一般情况下,它仍然是许多工作要做没什么不可以。忽然帮助吗?更糟的是,它只是不会...
我记得在教堂Tarasovka(在我们的教堂的一部分颇为流行)的男生去组织一个礼拜日。我带着我。呵呵......如果一个线程,现在,如其他博客可以想象出我的脑海发布 - 二伟,开始在评论!油画:流行音乐,然后服务唱诗班唱歌,吓得蜷缩在墙壁上的DIB,ZENK只盯在教堂前 - 德美汽车业的颜色,然后,全黑的无烟煤,并在寺庙的中心......他们。公牛...剃光头,黑色皮革几乎是从肌肉爆裂,另一种是健康的相互多头。低着头,交叉,gubёshkami巴掌......我已经那么,坦率地说,我有点razvidet吧!
然后,一定要 - 把一支蜡烛。巴布卡什么,只是生活在恐惧之中,vytsepit并得出问题在哪里放置敬酒,这对于和平,在那里 - 到rebёnochka有......嗯,在输出端 - 捐赠。谁是凉爽。
它并没有帮助他们,顺便说一句。在六个月内,几乎全部阵亡。但是,这些谁被杀死 - 也是在教堂,然后去了。而且,或许,是相同的。那么,如果卡拉什汽车离开...
然而,在同一时间,有一个短的路,我churching。
生活是不含糖。虽然我对小伙子们,而不是一个,而是属于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简单地说 - 一个叫卖。俄罗斯 - 区域风险的农业,甚至在业务方面 - 所以最后。也够问题。而一些莫名其妙前后左右都是虔诚的,交叉的维度就是不衡量,即使是我们的女儿,然后是获得乐趣 - 突然响起一个星期六的洗礼。好吧,这是我决定的。
流行音乐我很熟悉。当我问他 - 他告诉了我一切。而且,是的,我忘了说:我不洗,当然。
好了,他告诉我说,好,你首先需要承认。
我想我是认真的。非常重视。事实是,唯一的罪过就是我 - 这是我的处女放弃。在我看来,这罪是完全由谁投掷了我又处女的数量抵消。那么事实是,没有,我没扔,不杀生,不偷盗,贿赂,即使他们不得不放弃 - 一分钱,有趣。然后其他的腐败不严重,早在90多岁。在一般情况下,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交代什么?
而亵渎神灵的想法杜比卑鄙的我一路到大脑。我什么都不知道神学,但一些已经在考虑中的项目管理。妈的,如果他有我的poebulek的事情 - 我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如果他不关心 - 这就是我要撼动空气中的牧师东西,他的性面前,是吧?
磨擦他的心脏和灵魂,思想临死前告诉你关于爱情和学校的罪取笑教师?欺负。嗯,这是。更要告诉汽车是如何被盗的有一天,一个醉汉。骑走了。更告诉如何tyril钱和车的父母,顺便说一句,太 - 车程。所以也,就没什么事。我收集了起来。
在这一天,我走了,你也知道,到教堂。所有这些开明的。它提供我的祭司。他毕业于服务,走了,笑得很开心。我立刻开始业务,友好的交谈:
- 听着,你说你必须有一个自定义的连接?你能帮助Kruzak通关? Kruzak驱动我在这里... - 并按照Kruzak的主题,驱使他,在很长的,Mlýn的!
他是无罪的。他显然忘了思考我的问题,我没让一个人的印象,谁能够认真来找他承认,接受洗礼,当时的笑。
不过我喜欢水的桶冲了过来。什么是你的,怕啥,ohuel相当chtol?!谁是 - 一个忏悔?牧羊人?你上周stopisyat雄鹿队坚持了6惠斯特的苦难?!
并且如果其他?好了,其他一些其他的Hvatkinu帕夏坚持stopisyat美元。而对于如果太守好,没有大麻。或桑拿与女孩。
Sdurel chtol你呢?他们 - 的人,其他人一样。凭借同一套pripizdey和蟑螂。也许更糟。也许更糟。
......我们聊到了牧师的Kruzak,我答应帮他解决问题,并在左边。他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并问:我是什么,其实,即使是在教堂里来的呢?你以为只是为了他的电动助力海关的贪婪?嗯,这样的精神之父忏悔...
但后来有一些churching再次发作。已经是地方 - 我们的家庭。生病的母亲。当他们宣布了可怕的诊断,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抓住任何可能以某种方式取得成功。
然后向国外仍然悬而未决,货币是值得非常生气货币基金不存在,保险是不存在的,我们的药已经然后 - 完整的狗屎。这就是我想说的苏联免费医疗。妈的刚才,因为苏联的保持不变,但变得越来越支付高昂的价格。然后真正的癌症中心,如医生建议Urinotherapy尝试......作为一个选项...查看?然后时尚是在所有的传统医学,而不是所谓的传统。女巫,算命,巫师,民间医者......他们的军团!而关于每一个谣言有它这就是它 - 创造奇迹,叫死人从坟墓,现场恢复活力二十多年来,阴茎与乳房增大,既概括又特别。
当然,你知道,这一切是不管是谁,以及如何这个垃圾在追逐什么级别的完整的垃圾。但是,我们不能以其他方式:你不能说给心爱的人 - 妈妈,我们不会处理这些垃圾,你死 - 你死了,因为......给我一个人谁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与主要的事情 - 做。
这家由治疗师赶到女巫从呱呱 - 顺势疗法,不忘对目前的教授和灯具国内医药(关于这些和母亲灯具历时三年)。
更接近高潮来了一个牧师。已经从彼得。他是谁,在哪里谁推荐他 - 一些熟悉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牧师可言,所有的目光都散发这样的彩旗!乐于助人,安静,妈妈坐在床边,嘀咕了一整天。
妈妈说 - 很容易,当他正跟她说话。而且他对上帝,圣经......好吧,如果更简单 - 坐,然后。他坐在那儿。每一天,为作业。没有钱,没有什么他没有。你看,一个圣洁的人。
......但是,他成为了他们所有的传统治疗师和治疗师建议。和许多早期的不同,他们只花了现金,以及更多。女巫,茶香菇木耳在做,天知道是什么,那么饮食,以符合要求的,那么这个世界否认,然后 - 所有孩子立刻跨越奠定了......我们不会介意的 - 这对母亲的健康不就已经聚集交叉设置(虽然我胆怯地坚持,有过适合于需要支付:让母亲率先复苏 - 困难时,我没有找到一个东正教)。
但它并没有再次发生,在我母亲去世了。
牧师站了起来,揉揉她的手和抚摸borodёnku,轻轻地,平静地说,“上帝给了 - 上帝已经采取了”我真想打他,但这样的人能够在太空解散...
贝斯,一个字。
妈妈才49岁......
......所以后来我已经对祭司和中华民国严重的投诉。这是为什么呢?是的,因为我还是只能假设有一个上帝,或任何更高的功率,因为它不叫。难道他(她)的任何关于我母亲的命运?我不知道。但牧师是准确的。而我现在知道:这里也没有神在其中一点比全多 - 所以这是他们!
我没有为我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与教堂里。如果你只是不知道中华民国什么,我是无所谓吧,毕竟上述与其成员的沟通,所有的这些故事,我开始认真地对她的敌意。
现在我看起来像一个教堂有趣的交配日夜与国家,挥舞着旗帜,据我所知,我的儿子,如果他们想成为能说什么,我能说的是:我在一个非常世俗的国家长大了!
当然,如果国家不改变。
可悲的是,先生们,同志们。
©baxus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