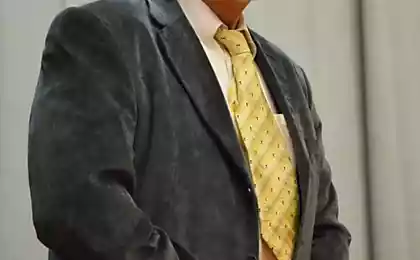603
现实的尸体存在的地狱之旅
十一万九十九千两百八十
"伟大的圣人说"噢王,所有的地狱般的行星系统的数第二十八个,是位于南部,我们的宇宙,下面的地球和行星的祖先,超过该水域的通用海洋。 我会告诉你简短地谈一谈这些行星,他们如何看待和彼此不同。 这些行星的地方惩罚的罪人。""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的3-6
这个故事告诉我的一个朋友和尚-Dhamaka克das。 你是一名记者。 也许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 —只是,请不要叫我的名称:我对这个世界—很久以前死亡。
他说情绪。 我只有删除俚语,并提供一个小的文本链接到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他的故事。
我不再有权保持沉默。 五年前,在离开医院后,我试着共同的愿景,与医生、亲戚、熟人,撰写了在报纸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完全排除的。 最后,我开始感觉到,发生的一切对我—凭空想象,如果它可能是一个人,无意识的躺在二十三天。 但现实情况的存在死后是一如此严重,我必须谈论它。
在他死之前我最喜欢的我的同龄人中,有一个完全有罪的生活。 我们没有营业—不在网,它是"种植的一个吮吸者。" 在晚上,聚集在可疑场所和开派对最好他们可能。
赚了一大堆的钱,我们也无意识地花费在酷车、酒、毒品和女孩。 主要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赚钱的能力,以及在什么方式这并不重要。 你可以去的浮渣,但在短粗—你在权力机构。 道德家我们鄙视的,相信他们会嫉妒和输家。
当灵魂是可悲的,它的发生有时候我去了他的弟弟,敲钟的老信徒的修道院。 这是简单的,就像一个孩子,我真诚地欢欣鼓舞,并试图阅读他们的东西的旧约圣经的书籍:一些有关的更高命运的人,上帝爱我们所有人。
我认为他保护,吹嘘的收入,并给他钱,但是他只是静静地微笑着说:
—它是空的,尼克。 虚荣的梳妆台—或迟或早都将通过和将来的最终检验死亡。
但他从不害怕,我也是上帝的愤怒也不是地狱。 他领导的生命的义。 只有罪,他被发现,饮用,但基督教似乎是不受禁止的。
一天晚上,我们坚决不同意。 他始终没有钱,我突然感到遗憾的一点,认为"够了",他们说,玩愚蠢的工作要做,他将谈论上帝服务的。 我留下非常恼火和隔天早上他已经走了—有急事,他被击中了一列火车。
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非常震惊和作,尤其是大幅认为,死亡是不要等待,也没有电话没有—它总是存在的。
当一个星期后的很难喝酒开始清理了他的房间顺序,在许多基督教的文献中突然发现薄伽梵-gītā,与众多的书签。 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从来没有告诉我关于他的魅力的印度哲学,小心翼翼地打开书...读。
"薄伽梵歌"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但是看到我的低迷状态,他说:
所以,来吧,你现在就需要。
一个星期后我突然爆发的同伴,说明我将独自工作和沮丧。 什么都不做是不想要的。 试图读圣经但不明白。 在伽梵-gītā同样的印象,因为如果在一个黑暗的房间要开灯。 我的问题:"谁是我们? 为什么你住在哪里?" 我有一个惊人地明确和简单的答案。
我找到了地址在书寺庙的克里希纳意识,并愉快地把有免费的时间。 我喜欢安静友好的人民,他称自己是忠实的仆人克里希纳。 在他们的社会自己举行的我的所有的悲伤。 我开始参加他们的早晨服务、讲座、以及有时牺牲一些细节,甚至帮助在厨房去剥土豆。
然后,放松与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挥手向高加索地区。 这笔钱仍然是,我们仍然盲目地通过燃烧生活,似乎它将永远。
但很快我们的田园生活结束了。 变成不规则的支付,不得不投身到初级商品的金钱关系与他们所有的属性:餐馆、酒,打架等。 猛地在一个漂亮的操作体面,我走进下一个回合。 并且在某些点上,他开始看到另一个现实,或者简单地说出来。 在科学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震颤性谵妄"当男人穿越微妙的能量领域的分离我们从其他的世界。
后来,在"圣典-谭"我找到一个准确的描述任何这些实体,住在我们旁边,被称为如此美丽平行世界。 我不知道我怎么然后独立管理要摆脱这种可怕的公司,但这次我决定停止。
举行为期两周,然后喝了一瓶啤酒和突然觉得分离开他的身体。 房间里很快充满了熟悉灰绿色的实体。 但东西在他们的行为改变。 看起来像他们在等待人。 然后有的动物我从未见过的。 当所有的枯萎和尊重分开。 毫无疑问—来抓我! 腿跑到温暖的涓涓细流。
"在死亡的时候一个看到神的使者的死亡,yamadutas面对他充满血丝的眼睛,并且,吓坏了,他发出的尿液和粪便的"。
"圣典-谭"Canto3,第30章文本19
Sledstvie可以采取任何形式。 通常这些人是最害怕的。 就个人而言,我始终无动于衷"恐怖电影"我唯一害怕的是背叛。 和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点。 采用的幌子朋友他们昏倒在椅子和启动通常的小谈话,我震惊地发现我的记忆得到所有的肮脏行为和想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污物累积在那里! 这是当它真正成为"极度痛苦的浪费了多年,对轻微和零用的过去。" 难怪的学校被迫学习。
然后开始交叉检查。 我很快就得到了混淆,并开始发疯。 无法承受的紧张、冲到窗口跳入玻璃。 下降,从七楼,迅速地重复一些祈祷...
"Yamaduta对受害者的硬盘的事实他罪恶活动。 他们中的一个控制的思想,第二个问题,以及第三行为的罪人不会离开的所以没有机会说谎。 然后一个开始真诚悔改的"。
"圣典-谭",评论,第26章
Respetable四上午的诞生。 痛击中地面我感觉不到它,就这样悄悄地站了起来开始走他们的肢解的尸体。 看在泥坑里的血上伸出来的腿骨片和知道的高度下降,我清楚地理解,为希望出现奇迹,至少天真的。 没有什么但是自我厌恶我有经验。 妻子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我,这是正确的—谁想要一个喝醉了吗?
在过去六年半找到我。 当众人走到了一起,我决定开玩笑和大声地说:—好吧,你看什么看! 活死人没看见,或者别的什么? 为了挽歌的!
但是,没有一个作出答复。
—现在我们笑! —嘶嘶从背后的不祥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和被吓呆了—yamaduta! 离开身体的,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 此外,还有一个加重处罚情节。
赶到"快"。 一块肉,没有多余的多愁善感装到车上。 我跑之后,但立即被撞倒了一个可怕的打击。 Yamaduta立即把我的耐用看不见的净和拖入空间。
虽然身体不是,我完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看到,听到,感觉,并颤抖着在冰冷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什么...
拍立即开始。 从打击的橡胶警棍的头我失去了知觉,不能找出它是什么星星或火花吗? 一个惊人的发现—它会出现的微妙的身体也失去意识了。
"只是因为卫兵逮捕了罪犯,则受他的惩罚,yamaduta采取拘留的罪人。 他们加强了对他的脖子上一个时间循环,并且,复盖他的尸体与一个特殊的外壳可以让你通过空间,被拖到的第一个地狱般的星球叫Tāmisra的。 在两个或三个时刻,它们复盖的距离在第九十九千yojanas(一Yojana=12 872m),然后进行的罪人一个痛苦的酷刑,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在那里,他遭受了严重下的打击激烈的使者Yamaraja和痛苦失去的感情"了。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8
逐步开始使用一个新的状态。 击中头部,哦,好像是应该的。
注意到这一点,yamaduta有替换的警棍、皮鞭遭受苦难的加剧。 在某些点上提出了想法,如果你喝了,疼痛不会被察觉如此强烈,我要伏特加酒。 他们说
—现在!
一个推我的下巴,而第二开始慢慢倒下我的喉咙一些液体,他说:
培亮,不要感到羞愧。
我怒吼。 这不是伏特加! 我扭动着疼痛、窒息和...喝醉了 和他们幸灾乐祸:
—什么宿醉这不是呢!
因为他我知道是早晨,当所有震动和扭动的。
"那些滋润的热情melinoma,使者死亡的被扔进地狱Ahana,还有牧师一边这副期间所表现的仪式。 有仆人的Yamaraja,罪人站在他的胸部,倒到他们的喉咙的铁."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29
惩罚在地狱是一个很多。 然后我撕成碎片的一些邪恶的动物状的生物(这是茹茹和cravedi在地球上,他们是找不到的—ed. 提交人),以骨吃白蚁。 然后烤在一个铜锅,被冻在冰川,拖过了荆棘,剥皮肤还活着。 许多类型的酷刑,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众所周知的地球上,但是它们都适用于我—我没想到! 一些想起牢固。
一旦在地狱,我慢慢浸在沸石油。 当痛苦达到一个峰值,取出来,但一旦停止,下降了。
非常痛苦的还有,当你发芽通过茎上的年轻竹子。 锋利的喜欢锥子,它们延伸至第三十厘米每晚。
但更难以赤裸裸的站在耻辱柱,当你框杆通过那些人你的生活,撕裂的肌腱,他们咬人,摇摆的残酷的殴打的话,宣告你已经积累起来的。 而这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相,你可以既没有隐藏也没有争论,因为他死了! 所以只有死后就会知道什么是混蛋事实证明,在他的一生! 像有关的死并不是说不好,但那应该是什么?
谁是从事犯罪活动来支持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他遭受地狱的折磨他的亲戚。 这样的罪人被放在一个燃烧的火灾,并且当他们烤,使他们有自己的骨肉。
"圣典-谭"Canto3,第30章、项目28
我遭遇了很多从他自己的想法。 已经生病的,但是他抱怨和戳无端的鼻子底下最肮脏的像什么好东西在生命。 也许真的不是吗? 不假期完全虚假的记忆或者如何的先锋。
和生活糟透了,死亡不是一个快乐。 没有间隙的。
在某一点上我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光室和软女性的声音说:
—你现在内的一切都是撕裂和破坏,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肯定会解决,但现在放松和享受。
在这里,我认为,伟大的! 结束了我的餐在天堂!
人们在这个世俗社会开始享受的各种饮料。 我还命令"粉红香槟"。 我带来了它,是的有很多—一个整体框!
所有祝贺我,说一些令人愉快的演讲,令人鼓舞的,点头,微笑,喝了,喝了。 我突然发现我不可能到达富热尔. 我试图通过手势显示,饥渴! 这样一个火热的渴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喝一杯生锈的自来水,我准备任何东西。
然后再在监狱、屠户、欺凌。 有,同志们在遭受痛苦。 这似乎是沿着遭受地狱的任何更长的时间—所以没有,还力求安排podlyanku! 如果他们从此更容易了。 它一直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我死了几十个,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时间,改变体和个星球,这是一个伟大的多。
但是一个地球Crimination—我们应该告诉你更多。 在梵语"krimi"指的蠕虫。 在这个星球上的下落刑事—肛门要素--那些生活在牺牲他人的痛苦。 整个地球—大湖,充满了一个血腥的混乱和充满着大肥蠕虫。 我没有时间来回落,作为以我从各方面挖这些生物。 我又开始疯狂地吞食了他们。 哦,上帝,这就像我们的生活在地球上的!
如果只有那些现在,促进了犯罪和性别,他知道怎么它将为他们! 我只能希望他们永恒的生命。 他们最好没死!
然后我一些时间站在水池有一些令人作呕的物质,但感到耻辱和痛苦已经彻底减弱,并且邻居的酷刑也不是那么拥挤—还吞了很多。
"痴迷的欲望和失去了他的头脑,罪人强迫他的妻子喝它的精子,死后去地狱Balabaksha的。 在那里,他被扔进Shukra Nadi(河的精液)和强迫喝。"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27
我现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忍受的地狱,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这不是夸张。 微妙的身体的感觉完全一样粗鲁。 唯一的区别是粗糙的是摧毁了一次和薄可以做到死的,直到永远。
所有这些地狱般的苦难是,只有在为了限制人们意识到仅仅是本能的,然后他是乖乖地出生在任何动物的形式。
"在生物将otctraded在地狱和天生的交替在所有较低的形式生活的前人类,它赎为自己的罪行,是重生的地球上男人。"
"圣典-谭"Canto3,第30章,项目34
Amnistia有一天我在一个透明的包裹是一个巨大的宝座房。 坐在宝座上的人,像伊万的可怕,举行了法院。 当他转过来,秘书宣读了我的情况,并告知有关预防措施,这意味着有即将来临我的地狱的生活中,我介绍的。 顺便说一句,这是第一次我遇的电影我的生活。 垃圾电影没有想法,没有阴谋。 固体Chernukha与色情。
靠近上帝的死亡,Yamaraja是不是可怕的。 他是那种,人道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残酷我的折磨。 他问我,先生这么轻轻地,在一个慈父般的方式,我崩溃了,哭了起来。 给我水,正常,没有缺陷。 我喝醉了,然后只认识了他的问题:
—如果你这样做,该怎么做吗?
我突然脱口而出:
—作为一个僧了上帝的服务!
Yamaraja们感到惊讶:
—上帝? 这是很好的一个上帝,我为—这些,例如:倾听的音乐,歌唱中合唱团。
不,不是这样。
然后该机构听起来—难,如电影"虻的"。
—不,说不的! 我喜欢:
克利须那,
克利须那,
克里希纳克里希纳
野兔兔子...
他笑了起来:
—服侍上帝有的信仰。 在这里,你是,有人相信呢?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Daruka和尚,我会见了克希神庙。 他的表情是那么纯洁、辐射,他看着我这样的爱我几乎窒息了的幸福:
—就是他,我相信他!
Jaya!'所述Yamaraja和拍他的手中--所有消失。
我醒来的时候,在重症监护室。 事实证明,身体彻底结盟和固有特殊的配件。 所有这一次,它是无意识的。 我知道,带我回来的原因—我是有机会重他的生命。 虽然在地狱里我被无限期地在地面上它只有二十三天。
医生很惊讶我勇敢地经受了所有的治疗方法。 当然! 地方面没有什么比我经验丰富在那里!
当痛苦是特别生气,我故意去的身体和走在房子周围,听到争议的医生,关于如何能够生存下去或者没有。 确保我没有看到一个长期徘徊在的微妙的体,首先是在医院复杂,并随后在莫斯科举行。
访问的多次在公寓,他的妻子,并且看到,我的访问使他们极大的焦虑。 关于我只记得,开始骂人,然后感到遗憾甚至试图访问,但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立即作出反应到我访问的父亲。 他住在莫斯科附近,我有出现像他已经放弃了一切,采取了一个篮子里的蔬菜和水果去了我。
虽然在医院里,多次看到yamadutas的。 并且,把冷与恐怖活动,眼看着他们的排的灵魂死去,但我很幸运的是不感兴趣他们了。
当我被排出,随后的公寓再次拔老朋友和女朋友—不是两手空空的,当然。 我要加入饮用,因为那天晚上来到一个地狱的伙计们,开始把我拖出来的身体。 在平衡的呼吸,我嘶哑的:"克利须那!"醒来的时候一身冷汗。 害怕睡觉,直到黎明再重复这种拯救生命祈祷。
在早晨,在某种程度上有decostyle库尔斯克火车站去到村,远离罪恶。 在奶奶在一个安静的局势变得严重,汤姆汤姆读"圣典-谭"和在第三,第五首歌发布了一个详细的结构的说明我们的宇宙从上世界熟悉的地狱般的行星。 然后终于决定把自己的服务的上帝。
六个月后,又到莫斯科来检索的金属架,保持我的身体。 医生很惊讶看到我,单独行走,而没有拐杖。 按所有标准,我应该至少六个月躺在床上。
Oklemavshis手术之后,我去克里希纳,但是在和平的前景已经走了。 寺庙移动Sukharevo,在莫斯科举行。 之后学习的地址,去了那里的第一个人见面是Daruka—那个拉我出地狱。 哭笑,我告诉他关于我不幸的事和Yamarāja,誓言。 一年后,我开始从精神主并成为一个和尚。
现在,提供购买神圣的圣经"薄伽梵歌或圣典-谭"—我坦率地说,这些图书救了我。 和人看到我的话的真诚愿望的良好给他们,对它作出反应。 我自己非常高兴的唯一的事情我每天都祈祷上帝,给人们回忆他们的原始精神性质,然后他们会有机会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甚至死亡后没有休息。
作者:阿纳托利Todorov
资料来源:www.zvek.info/karma-and-reincarnation/17-puteshestvie-v-ad.html
"伟大的圣人说"噢王,所有的地狱般的行星系统的数第二十八个,是位于南部,我们的宇宙,下面的地球和行星的祖先,超过该水域的通用海洋。 我会告诉你简短地谈一谈这些行星,他们如何看待和彼此不同。 这些行星的地方惩罚的罪人。""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的3-6
这个故事告诉我的一个朋友和尚-Dhamaka克das。 你是一名记者。 也许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 —只是,请不要叫我的名称:我对这个世界—很久以前死亡。
他说情绪。 我只有删除俚语,并提供一个小的文本链接到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他的故事。
我不再有权保持沉默。 五年前,在离开医院后,我试着共同的愿景,与医生、亲戚、熟人,撰写了在报纸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完全排除的。 最后,我开始感觉到,发生的一切对我—凭空想象,如果它可能是一个人,无意识的躺在二十三天。 但现实情况的存在死后是一如此严重,我必须谈论它。
在他死之前我最喜欢的我的同龄人中,有一个完全有罪的生活。 我们没有营业—不在网,它是"种植的一个吮吸者。" 在晚上,聚集在可疑场所和开派对最好他们可能。
赚了一大堆的钱,我们也无意识地花费在酷车、酒、毒品和女孩。 主要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赚钱的能力,以及在什么方式这并不重要。 你可以去的浮渣,但在短粗—你在权力机构。 道德家我们鄙视的,相信他们会嫉妒和输家。
当灵魂是可悲的,它的发生有时候我去了他的弟弟,敲钟的老信徒的修道院。 这是简单的,就像一个孩子,我真诚地欢欣鼓舞,并试图阅读他们的东西的旧约圣经的书籍:一些有关的更高命运的人,上帝爱我们所有人。
我认为他保护,吹嘘的收入,并给他钱,但是他只是静静地微笑着说:
—它是空的,尼克。 虚荣的梳妆台—或迟或早都将通过和将来的最终检验死亡。
但他从不害怕,我也是上帝的愤怒也不是地狱。 他领导的生命的义。 只有罪,他被发现,饮用,但基督教似乎是不受禁止的。
一天晚上,我们坚决不同意。 他始终没有钱,我突然感到遗憾的一点,认为"够了",他们说,玩愚蠢的工作要做,他将谈论上帝服务的。 我留下非常恼火和隔天早上他已经走了—有急事,他被击中了一列火车。
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非常震惊和作,尤其是大幅认为,死亡是不要等待,也没有电话没有—它总是存在的。
当一个星期后的很难喝酒开始清理了他的房间顺序,在许多基督教的文献中突然发现薄伽梵-gītā,与众多的书签。 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从来没有告诉我关于他的魅力的印度哲学,小心翼翼地打开书...读。
"薄伽梵歌"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但是看到我的低迷状态,他说:
所以,来吧,你现在就需要。
一个星期后我突然爆发的同伴,说明我将独自工作和沮丧。 什么都不做是不想要的。 试图读圣经但不明白。 在伽梵-gītā同样的印象,因为如果在一个黑暗的房间要开灯。 我的问题:"谁是我们? 为什么你住在哪里?" 我有一个惊人地明确和简单的答案。
我找到了地址在书寺庙的克里希纳意识,并愉快地把有免费的时间。 我喜欢安静友好的人民,他称自己是忠实的仆人克里希纳。 在他们的社会自己举行的我的所有的悲伤。 我开始参加他们的早晨服务、讲座、以及有时牺牲一些细节,甚至帮助在厨房去剥土豆。
然后,放松与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挥手向高加索地区。 这笔钱仍然是,我们仍然盲目地通过燃烧生活,似乎它将永远。
但很快我们的田园生活结束了。 变成不规则的支付,不得不投身到初级商品的金钱关系与他们所有的属性:餐馆、酒,打架等。 猛地在一个漂亮的操作体面,我走进下一个回合。 并且在某些点上,他开始看到另一个现实,或者简单地说出来。 在科学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震颤性谵妄"当男人穿越微妙的能量领域的分离我们从其他的世界。
后来,在"圣典-谭"我找到一个准确的描述任何这些实体,住在我们旁边,被称为如此美丽平行世界。 我不知道我怎么然后独立管理要摆脱这种可怕的公司,但这次我决定停止。
举行为期两周,然后喝了一瓶啤酒和突然觉得分离开他的身体。 房间里很快充满了熟悉灰绿色的实体。 但东西在他们的行为改变。 看起来像他们在等待人。 然后有的动物我从未见过的。 当所有的枯萎和尊重分开。 毫无疑问—来抓我! 腿跑到温暖的涓涓细流。
"在死亡的时候一个看到神的使者的死亡,yamadutas面对他充满血丝的眼睛,并且,吓坏了,他发出的尿液和粪便的"。
"圣典-谭"Canto3,第30章文本19
Sledstvie可以采取任何形式。 通常这些人是最害怕的。 就个人而言,我始终无动于衷"恐怖电影"我唯一害怕的是背叛。 和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点。 采用的幌子朋友他们昏倒在椅子和启动通常的小谈话,我震惊地发现我的记忆得到所有的肮脏行为和想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污物累积在那里! 这是当它真正成为"极度痛苦的浪费了多年,对轻微和零用的过去。" 难怪的学校被迫学习。
然后开始交叉检查。 我很快就得到了混淆,并开始发疯。 无法承受的紧张、冲到窗口跳入玻璃。 下降,从七楼,迅速地重复一些祈祷...
"Yamaduta对受害者的硬盘的事实他罪恶活动。 他们中的一个控制的思想,第二个问题,以及第三行为的罪人不会离开的所以没有机会说谎。 然后一个开始真诚悔改的"。
"圣典-谭",评论,第26章
Respetable四上午的诞生。 痛击中地面我感觉不到它,就这样悄悄地站了起来开始走他们的肢解的尸体。 看在泥坑里的血上伸出来的腿骨片和知道的高度下降,我清楚地理解,为希望出现奇迹,至少天真的。 没有什么但是自我厌恶我有经验。 妻子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我,这是正确的—谁想要一个喝醉了吗?
在过去六年半找到我。 当众人走到了一起,我决定开玩笑和大声地说:—好吧,你看什么看! 活死人没看见,或者别的什么? 为了挽歌的!
但是,没有一个作出答复。
—现在我们笑! —嘶嘶从背后的不祥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和被吓呆了—yamaduta! 离开身体的,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 此外,还有一个加重处罚情节。
赶到"快"。 一块肉,没有多余的多愁善感装到车上。 我跑之后,但立即被撞倒了一个可怕的打击。 Yamaduta立即把我的耐用看不见的净和拖入空间。
虽然身体不是,我完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看到,听到,感觉,并颤抖着在冰冷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什么...
拍立即开始。 从打击的橡胶警棍的头我失去了知觉,不能找出它是什么星星或火花吗? 一个惊人的发现—它会出现的微妙的身体也失去意识了。
"只是因为卫兵逮捕了罪犯,则受他的惩罚,yamaduta采取拘留的罪人。 他们加强了对他的脖子上一个时间循环,并且,复盖他的尸体与一个特殊的外壳可以让你通过空间,被拖到的第一个地狱般的星球叫Tāmisra的。 在两个或三个时刻,它们复盖的距离在第九十九千yojanas(一Yojana=12 872m),然后进行的罪人一个痛苦的酷刑,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在那里,他遭受了严重下的打击激烈的使者Yamaraja和痛苦失去的感情"了。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8
逐步开始使用一个新的状态。 击中头部,哦,好像是应该的。
注意到这一点,yamaduta有替换的警棍、皮鞭遭受苦难的加剧。 在某些点上提出了想法,如果你喝了,疼痛不会被察觉如此强烈,我要伏特加酒。 他们说
—现在!
一个推我的下巴,而第二开始慢慢倒下我的喉咙一些液体,他说:
培亮,不要感到羞愧。
我怒吼。 这不是伏特加! 我扭动着疼痛、窒息和...喝醉了 和他们幸灾乐祸:
—什么宿醉这不是呢!
因为他我知道是早晨,当所有震动和扭动的。
"那些滋润的热情melinoma,使者死亡的被扔进地狱Ahana,还有牧师一边这副期间所表现的仪式。 有仆人的Yamaraja,罪人站在他的胸部,倒到他们的喉咙的铁."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29
惩罚在地狱是一个很多。 然后我撕成碎片的一些邪恶的动物状的生物(这是茹茹和cravedi在地球上,他们是找不到的—ed. 提交人),以骨吃白蚁。 然后烤在一个铜锅,被冻在冰川,拖过了荆棘,剥皮肤还活着。 许多类型的酷刑,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众所周知的地球上,但是它们都适用于我—我没想到! 一些想起牢固。
一旦在地狱,我慢慢浸在沸石油。 当痛苦达到一个峰值,取出来,但一旦停止,下降了。
非常痛苦的还有,当你发芽通过茎上的年轻竹子。 锋利的喜欢锥子,它们延伸至第三十厘米每晚。
但更难以赤裸裸的站在耻辱柱,当你框杆通过那些人你的生活,撕裂的肌腱,他们咬人,摇摆的残酷的殴打的话,宣告你已经积累起来的。 而这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相,你可以既没有隐藏也没有争论,因为他死了! 所以只有死后就会知道什么是混蛋事实证明,在他的一生! 像有关的死并不是说不好,但那应该是什么?
谁是从事犯罪活动来支持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他遭受地狱的折磨他的亲戚。 这样的罪人被放在一个燃烧的火灾,并且当他们烤,使他们有自己的骨肉。
"圣典-谭"Canto3,第30章、项目28
我遭遇了很多从他自己的想法。 已经生病的,但是他抱怨和戳无端的鼻子底下最肮脏的像什么好东西在生命。 也许真的不是吗? 不假期完全虚假的记忆或者如何的先锋。
和生活糟透了,死亡不是一个快乐。 没有间隙的。
在某一点上我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光室和软女性的声音说:
—你现在内的一切都是撕裂和破坏,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肯定会解决,但现在放松和享受。
在这里,我认为,伟大的! 结束了我的餐在天堂!
人们在这个世俗社会开始享受的各种饮料。 我还命令"粉红香槟"。 我带来了它,是的有很多—一个整体框!
所有祝贺我,说一些令人愉快的演讲,令人鼓舞的,点头,微笑,喝了,喝了。 我突然发现我不可能到达富热尔. 我试图通过手势显示,饥渴! 这样一个火热的渴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喝一杯生锈的自来水,我准备任何东西。
然后再在监狱、屠户、欺凌。 有,同志们在遭受痛苦。 这似乎是沿着遭受地狱的任何更长的时间—所以没有,还力求安排podlyanku! 如果他们从此更容易了。 它一直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我死了几十个,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时间,改变体和个星球,这是一个伟大的多。
但是一个地球Crimination—我们应该告诉你更多。 在梵语"krimi"指的蠕虫。 在这个星球上的下落刑事—肛门要素--那些生活在牺牲他人的痛苦。 整个地球—大湖,充满了一个血腥的混乱和充满着大肥蠕虫。 我没有时间来回落,作为以我从各方面挖这些生物。 我又开始疯狂地吞食了他们。 哦,上帝,这就像我们的生活在地球上的!
如果只有那些现在,促进了犯罪和性别,他知道怎么它将为他们! 我只能希望他们永恒的生命。 他们最好没死!
然后我一些时间站在水池有一些令人作呕的物质,但感到耻辱和痛苦已经彻底减弱,并且邻居的酷刑也不是那么拥挤—还吞了很多。
"痴迷的欲望和失去了他的头脑,罪人强迫他的妻子喝它的精子,死后去地狱Balabaksha的。 在那里,他被扔进Shukra Nadi(河的精液)和强迫喝。"
"圣典-谭"Canto5,第26章文本27
我现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忍受的地狱,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这不是夸张。 微妙的身体的感觉完全一样粗鲁。 唯一的区别是粗糙的是摧毁了一次和薄可以做到死的,直到永远。
所有这些地狱般的苦难是,只有在为了限制人们意识到仅仅是本能的,然后他是乖乖地出生在任何动物的形式。
"在生物将otctraded在地狱和天生的交替在所有较低的形式生活的前人类,它赎为自己的罪行,是重生的地球上男人。"
"圣典-谭"Canto3,第30章,项目34
Amnistia有一天我在一个透明的包裹是一个巨大的宝座房。 坐在宝座上的人,像伊万的可怕,举行了法院。 当他转过来,秘书宣读了我的情况,并告知有关预防措施,这意味着有即将来临我的地狱的生活中,我介绍的。 顺便说一句,这是第一次我遇的电影我的生活。 垃圾电影没有想法,没有阴谋。 固体Chernukha与色情。
靠近上帝的死亡,Yamaraja是不是可怕的。 他是那种,人道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残酷我的折磨。 他问我,先生这么轻轻地,在一个慈父般的方式,我崩溃了,哭了起来。 给我水,正常,没有缺陷。 我喝醉了,然后只认识了他的问题:
—如果你这样做,该怎么做吗?
我突然脱口而出:
—作为一个僧了上帝的服务!
Yamaraja们感到惊讶:
—上帝? 这是很好的一个上帝,我为—这些,例如:倾听的音乐,歌唱中合唱团。
不,不是这样。
然后该机构听起来—难,如电影"虻的"。
—不,说不的! 我喜欢:
克利须那,
克利须那,
克里希纳克里希纳
野兔兔子...
他笑了起来:
—服侍上帝有的信仰。 在这里,你是,有人相信呢?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Daruka和尚,我会见了克希神庙。 他的表情是那么纯洁、辐射,他看着我这样的爱我几乎窒息了的幸福:
—就是他,我相信他!
Jaya!'所述Yamaraja和拍他的手中--所有消失。
我醒来的时候,在重症监护室。 事实证明,身体彻底结盟和固有特殊的配件。 所有这一次,它是无意识的。 我知道,带我回来的原因—我是有机会重他的生命。 虽然在地狱里我被无限期地在地面上它只有二十三天。
医生很惊讶我勇敢地经受了所有的治疗方法。 当然! 地方面没有什么比我经验丰富在那里!
当痛苦是特别生气,我故意去的身体和走在房子周围,听到争议的医生,关于如何能够生存下去或者没有。 确保我没有看到一个长期徘徊在的微妙的体,首先是在医院复杂,并随后在莫斯科举行。
访问的多次在公寓,他的妻子,并且看到,我的访问使他们极大的焦虑。 关于我只记得,开始骂人,然后感到遗憾甚至试图访问,但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立即作出反应到我访问的父亲。 他住在莫斯科附近,我有出现像他已经放弃了一切,采取了一个篮子里的蔬菜和水果去了我。
虽然在医院里,多次看到yamadutas的。 并且,把冷与恐怖活动,眼看着他们的排的灵魂死去,但我很幸运的是不感兴趣他们了。
当我被排出,随后的公寓再次拔老朋友和女朋友—不是两手空空的,当然。 我要加入饮用,因为那天晚上来到一个地狱的伙计们,开始把我拖出来的身体。 在平衡的呼吸,我嘶哑的:"克利须那!"醒来的时候一身冷汗。 害怕睡觉,直到黎明再重复这种拯救生命祈祷。
在早晨,在某种程度上有decostyle库尔斯克火车站去到村,远离罪恶。 在奶奶在一个安静的局势变得严重,汤姆汤姆读"圣典-谭"和在第三,第五首歌发布了一个详细的结构的说明我们的宇宙从上世界熟悉的地狱般的行星。 然后终于决定把自己的服务的上帝。
六个月后,又到莫斯科来检索的金属架,保持我的身体。 医生很惊讶看到我,单独行走,而没有拐杖。 按所有标准,我应该至少六个月躺在床上。
Oklemavshis手术之后,我去克里希纳,但是在和平的前景已经走了。 寺庙移动Sukharevo,在莫斯科举行。 之后学习的地址,去了那里的第一个人见面是Daruka—那个拉我出地狱。 哭笑,我告诉他关于我不幸的事和Yamarāja,誓言。 一年后,我开始从精神主并成为一个和尚。
现在,提供购买神圣的圣经"薄伽梵歌或圣典-谭"—我坦率地说,这些图书救了我。 和人看到我的话的真诚愿望的良好给他们,对它作出反应。 我自己非常高兴的唯一的事情我每天都祈祷上帝,给人们回忆他们的原始精神性质,然后他们会有机会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甚至死亡后没有休息。
作者:阿纳托利Todorov
资料来源:www.zvek.info/karma-and-reincarnation/17-puteshestvie-v-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