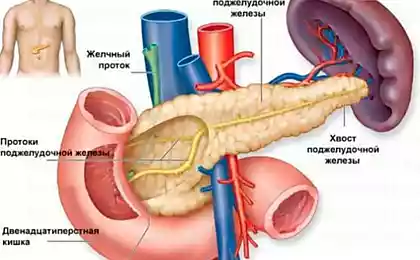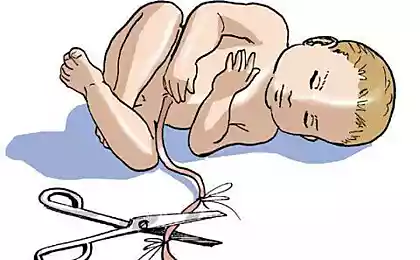669
血的袖子。
安德烈,是献给我的朋友。
在90年五月,我们的国际班,许多当时的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在学校军训。还有,根据NVP(基本军事训练)的比率一些在学年结束时。
这是五月底,我们的营地位于高加索地区的最美丽的峡谷之一,在一千多米以上的morya.Svetilo温暖的太阳,山,草的高度,我们或三十几无须青年,在模拟studotryadov工作服的形式,坐在附近的围栏,感到自豪事实上,今天终于从这些机器被解雇。我们坐着抽烟,并在斯捷潘ogromenny保加利亚吉打希腊人,购买karachai,cherkesoov,当地的哥萨克的“血”Tsoya.My -mnogonatsionalnaya“黑帮”(什么是民族家伙明白,无论是hohlyugi或俄语)一起跟着唱。

血的袖子。
我的袖子上的序列号!
祝我好运,
祝我好运吧......
不要停留在草丛中。
现在经常在车里听这首歌是不断地之一idilliya.My眼前年轻,唱歌,不知道pizdos与多年来国家将如何创造我们的前辈!
没有人留在了草地上,但Ildar。
我记得在94年遇到他在村里在陡峭的inomarke.Krasny“林肯”与车臣nomerami.On蛮横豪饮在村中心,切割晚上睡在汽车上的ulitsam.Potom已经熟悉99报告说,他们给他带来了晚上车臣,静静地墓地安葬在山上的村庄之一的郊区。那么很多karachaychat,品尝甜蜜的许诺等等带来的瓦哈比教派,可耻的熏黑丘svezherytoy土地nehuy来推力量!
相比之下Ildar,萨沙,我们粗暴odnoklashka,争取权力。他得到了一对盒火箭前面感谢spizzhennyh部分由未来的居民dizbata Novgorodom.Kak他被送往一家公司的同一场风暴撕裂Groznyy.Iz 106人在17.Vsego一对夫妇巷战个月的后面。这家伙得了上帝保佑!他拍的捷克人,射向他的VVshnikam复仇,housebroken和obkolovshis parmidolom是把尸体成堆。不再有萨莎。 Dembelnuvshis他坐在一根针,十几年来在麻醉ugare.I完全一氧化碳中毒度过的。
斯捷潘,我们在军前吉他手还没有坐进风暴dozhil.Napivshis more.Nashli他的身体只有在第三天。
兄弟Potsanuki ssavshie开水90,希望能转移到希腊安全地svalili.No的父亲去世了,最新的集集埋葬了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定居在莫斯科,成功地通过了奇迹的军队无法无天90年代中后期。
拉脱维亚埃德加满足军队后,刚刚复员。他在缩水的欧洲,花了两年时间在监狱里,现在从事销售的外国车,如地方办事处。
山姆是在该地区靠近车臣。我没得什么感谢世界上所有的神作斗争。因为她的眼睛看着这个丑陋的meropriyatie.Pomnyu士兵撕裂臀部在别斯兰机场从直升机运输到医院霍尔兹曼出院。
我记得从车臣爆炸物于12月96结束,19岁的男孩都空着,目光呆滞,像在头上的老人和白发蓬乱。当问及白发,回答漠然。他们说,有没有打算灰色当你在城市的全捷克人的中心zazhmut像一个铁桶一只老鼠。
我们的另一个配置文件制备,以防塔利班越过边境的。性交的尾巴和鬃毛,不放过我们俩也没有弹药并于5月97稍微rasslabili.Blagodarya的船长和Prapor过去阿夫甘,阿布哈兹和车臣我现在还堆积肌肉的一座山,而是由腿困扰,女性不冻结所有,热,痛,晚上抽搐。
朋友安德烈,我最亲密的odnoklashka谁帮我在灵狮骑兵学校争取和他们的哥哥担任morpehom.Malenky,敦实,充满激情的摔跤和拳击,但幸存下来的地狱检查服务于100新兵的精锐部队,只有两个desyatka.Na复员带来了他买大麻在进入米兰的端口的存在。烟,我们有美好的时光...... Pomaia在民用领域,94秋,他离开kontraknu侦察。我记得在十二月94来出差,伴随着货车与弹药过境白兰地Dagestan.Za玻璃,醉愤愤不平。“你不会相信在达吉斯坦,甚至孩子们,我们的手势,手指滑过他的喉咙,你kerdyk俄罗斯。请问什么Andryukha是什么可怕的!“ - 他告诉我的。他是对的。然后有所有的车臣战役,Pervomaysk,在那里他亲自naherachil十几个歹徒袭击在山上,一个续约合同。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在库班的城市之一买了一套公寓。
在2003年,我才知道他已经上吊自杀。只是陈词滥调忌用。他离开了俄罗斯军队的行列,对他的所有忠实的兄弟在武器放下他们的头祖国的荣耀的原因。伤到肺,可怕的狂欢后康复,在我脑海中的声音,一双破洗衣机在酒醉昏迷。最近在一个年轻漂亮的parnyaga坟墓看着我,一个纪念碑。而濒临大胆浮雕。
血的袖子。
我的袖子上的序列号!
资料来源:
在90年五月,我们的国际班,许多当时的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在学校军训。还有,根据NVP(基本军事训练)的比率一些在学年结束时。
这是五月底,我们的营地位于高加索地区的最美丽的峡谷之一,在一千多米以上的morya.Svetilo温暖的太阳,山,草的高度,我们或三十几无须青年,在模拟studotryadov工作服的形式,坐在附近的围栏,感到自豪事实上,今天终于从这些机器被解雇。我们坐着抽烟,并在斯捷潘ogromenny保加利亚吉打希腊人,购买karachai,cherkesoov,当地的哥萨克的“血”Tsoya.My -mnogonatsionalnaya“黑帮”(什么是民族家伙明白,无论是hohlyugi或俄语)一起跟着唱。

血的袖子。
我的袖子上的序列号!
祝我好运,
祝我好运吧......
不要停留在草丛中。
现在经常在车里听这首歌是不断地之一idilliya.My眼前年轻,唱歌,不知道pizdos与多年来国家将如何创造我们的前辈!
没有人留在了草地上,但Ildar。
我记得在94年遇到他在村里在陡峭的inomarke.Krasny“林肯”与车臣nomerami.On蛮横豪饮在村中心,切割晚上睡在汽车上的ulitsam.Potom已经熟悉99报告说,他们给他带来了晚上车臣,静静地墓地安葬在山上的村庄之一的郊区。那么很多karachaychat,品尝甜蜜的许诺等等带来的瓦哈比教派,可耻的熏黑丘svezherytoy土地nehuy来推力量!
相比之下Ildar,萨沙,我们粗暴odnoklashka,争取权力。他得到了一对盒火箭前面感谢spizzhennyh部分由未来的居民dizbata Novgorodom.Kak他被送往一家公司的同一场风暴撕裂Groznyy.Iz 106人在17.Vsego一对夫妇巷战个月的后面。这家伙得了上帝保佑!他拍的捷克人,射向他的VVshnikam复仇,housebroken和obkolovshis parmidolom是把尸体成堆。不再有萨莎。 Dembelnuvshis他坐在一根针,十几年来在麻醉ugare.I完全一氧化碳中毒度过的。
斯捷潘,我们在军前吉他手还没有坐进风暴dozhil.Napivshis more.Nashli他的身体只有在第三天。
兄弟Potsanuki ssavshie开水90,希望能转移到希腊安全地svalili.No的父亲去世了,最新的集集埋葬了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定居在莫斯科,成功地通过了奇迹的军队无法无天90年代中后期。
拉脱维亚埃德加满足军队后,刚刚复员。他在缩水的欧洲,花了两年时间在监狱里,现在从事销售的外国车,如地方办事处。
山姆是在该地区靠近车臣。我没得什么感谢世界上所有的神作斗争。因为她的眼睛看着这个丑陋的meropriyatie.Pomnyu士兵撕裂臀部在别斯兰机场从直升机运输到医院霍尔兹曼出院。
我记得从车臣爆炸物于12月96结束,19岁的男孩都空着,目光呆滞,像在头上的老人和白发蓬乱。当问及白发,回答漠然。他们说,有没有打算灰色当你在城市的全捷克人的中心zazhmut像一个铁桶一只老鼠。
我们的另一个配置文件制备,以防塔利班越过边境的。性交的尾巴和鬃毛,不放过我们俩也没有弹药并于5月97稍微rasslabili.Blagodarya的船长和Prapor过去阿夫甘,阿布哈兹和车臣我现在还堆积肌肉的一座山,而是由腿困扰,女性不冻结所有,热,痛,晚上抽搐。
朋友安德烈,我最亲密的odnoklashka谁帮我在灵狮骑兵学校争取和他们的哥哥担任morpehom.Malenky,敦实,充满激情的摔跤和拳击,但幸存下来的地狱检查服务于100新兵的精锐部队,只有两个desyatka.Na复员带来了他买大麻在进入米兰的端口的存在。烟,我们有美好的时光...... Pomaia在民用领域,94秋,他离开kontraknu侦察。我记得在十二月94来出差,伴随着货车与弹药过境白兰地Dagestan.Za玻璃,醉愤愤不平。“你不会相信在达吉斯坦,甚至孩子们,我们的手势,手指滑过他的喉咙,你kerdyk俄罗斯。请问什么Andryukha是什么可怕的!“ - 他告诉我的。他是对的。然后有所有的车臣战役,Pervomaysk,在那里他亲自naherachil十几个歹徒袭击在山上,一个续约合同。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在库班的城市之一买了一套公寓。
在2003年,我才知道他已经上吊自杀。只是陈词滥调忌用。他离开了俄罗斯军队的行列,对他的所有忠实的兄弟在武器放下他们的头祖国的荣耀的原因。伤到肺,可怕的狂欢后康复,在我脑海中的声音,一双破洗衣机在酒醉昏迷。最近在一个年轻漂亮的parnyaga坟墓看着我,一个纪念碑。而濒临大胆浮雕。
血的袖子。
我的袖子上的序列号!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