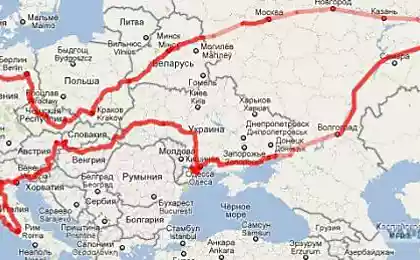622
“我们将与你住上了岸。”

我们将与你住在岸上,
围起来,高大的堤坝
在大陆,在一个小圈子,
搭建一个临时搭建的灯。
我们将与您
卡打 并听取了疯狂的冲浪,
咳嗽,潜移默化地叹了口气,
如果过强风。
我老了,而你 - 你还年轻
。 但它会作为教先锋,
该法案将去天 - 而不是几年 -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新的时代
。 在荷兰,其相反,
我们解散的花园,你
并且将牡蛎炒门槛<BR/> 而阳光明媚的吃章鱼。
让雨黄瓜的噪音,
我们扎戈拉与您爱斯基摩人,
和温柔,你花你的手指
处女,原封不动地带。
我得把镜中的锁骨
看看 并发现了一波
背后 和一个旧锡盒的盖革
在逐渐淡出,满身是汗的表带。
冬天来了,残酷地扭动
莎草我们的木屋顶。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孩子,
那么我们所说的安德鲁和安娜。
也就是说,到了皱纹的脸被嫁接,
没有忘记俄文字母,
呼气最后
中的第一个声音 和,因此,在将来建立。
我们将战斗卡,并在这里
我们将与王牌携带
上潮的绕组银行。
而我们的孩子会心照不宣地
你看,不理解什么,
像灯的蛾跳动,
在时机成熟时对他
回到越过大坝。
约瑟夫·布罗茨基,1965年
前瞻:julianbeattie
通过<一href="http://julianbeattie.com/uncategorized/amy-owen-south-ripley-qld/">julianbeattie.com/uncategorized/amy-owen-south-ripley-q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