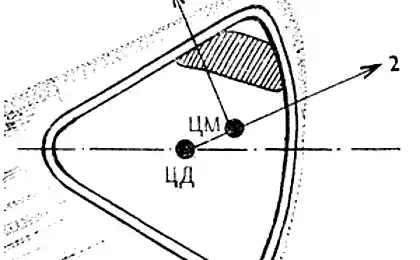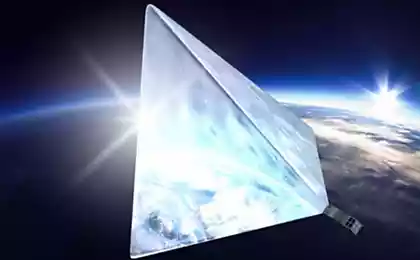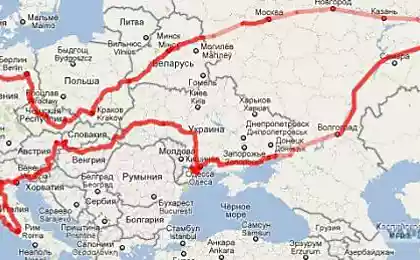1035
太空行走№23:征服新领域

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卢卡Parmitano,在一次太空行走数23
谈到她的感受和经验
我闭着眼睛,而克里斯导致气闸内的空气压力的倒计时 - 这已经是接近于零。不过,我不累,恰恰相反!我觉得完全充电,就好像电,没有血液,通过我的血管里流淌。我只是想确保我能够感知并记住所发生的一切。我在精神上准备自己去开门,因为这时候我会离开的第一站。也许这只是还有那天晚上至少现在,没有什么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当压力下降到3千帕,这是时间转动手柄,将舱口本身。外面漆黑一片;它不是黑色的,它是黑暗的 - 完全没有光线。我急切地浸涨的时候伸出来保护我们的安全电缆的观点。感觉完全放心,我弯腰,让克里斯通过。几秒钟内,我们最终确认彼此的份额。甚至尽管我们俩都前往国际空间站或多或少相同的部分,其实我们的行程有很大的不同,决定编排的严谨研究。我的路线直奔车站的后面,而克里斯必须先移动到前方站花绕Z1你的绳索 - 梁的中央结构在节点1。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无论是在轨道或地球上 - 我无法想象这个决定有多难影响到当天的活动。
我特别注意每一个动作,使我们的方式,我们留给外界一个星期前的保护袋。我很平静,但不要让自己放松,这将是一个错误。内袋我觉得这将成为我一天最有可能紧,任务重的部分电缆。我必须将它们连接到外部插座台同时它们固定在台表面小块线材。这两种操作提示,很多人会用他们的手指,而我从经验中知道,这是因为空气填充的手套箱非常累人。
克里斯参加了电缆的第一部分最后一周,所以我要抓住这个自由的一部分,慢慢引导她的巢。之后,在开始的时候有些困难,我通知休斯顿的完成了任务,并准备采取第二线。抓住下一个电缆,我转了站上的最困难的境地,我简直三种不同的模块之间的楔形,这样我的衣服,我的PSG(我的“背包”)的遮阳板是几英寸的外墙节点3,节点1和实验室。慢慢地,把相当大的努力我管理的第二线连接到插座。然后,一味朝着相反的方向,我放手的,我要工作了尴尬的位置。地上谢恩告诉我,我将近40分钟前比预期完成,克里斯也执行提前了任务。
就在那一刻,当我思考如何放松电缆多加小心(在失重抽搐,他喜欢一个人所拥有),我开始“感觉”,什么是错。突然间,我开始感觉到水在脖子后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很沮丧,因为在我的位置不会想对付的惊喜。我提出我的头从一边到另一边,确认他们的第一印象,和超人的努力强迫自己告知休斯顿自己的感受,因为他们知道,因为它可能预示了EVA的结束。巴蒂尔证实,他们已经收到我的短信,问我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克里斯,谁刚刚完成,仍然存在并指向我希望在视觉识别我的头盔水源。
起初,我们都认为它要么是从我的罐子protёkshaya瓶装水用吸管,或只是出汗。但我认为该流体太冷要的话,并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变得更大。我还发现了饮用水的阀不流动。当我告诉这对克里斯和巴蒂尔,我们立即得到订单“,完成”出击。另一种选择 - 以“中止”采用的是更严重的麻烦的情况下。我给的指示返回气闸。我们共同决定,克里斯应该可以解决所有的以外的元素在他来之前回以同样的方式到网关,即最初,他会移动到该站的前部。因此,我们分享。
回去沿线的气密室,我越来越确信,水的量增加。我觉得它会在我的耳机,我想知道如果我失去了我的连接。水几乎完全覆盖我的遮阳板的前端,坚持它,挡住了我的观点。我明白,我将不得不转向直立位置,圆我的方式在天线中的一个,和我的系绳通常会上路了。而此时我滚,两件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夕阳西下,和我的能力看,是违反水完全消失,使我的眼睛是无用的;但糟糕的是,水进入了我的鼻子 - 一个真正可怕的感觉,我会加剧他们妄图将水,摇了摇头。而此时,头盔全是水我的上部,什至不知道什么是下一次呼吸,我会填满你的肺部空气,而不是液体。更糟的是,我不知道在我需要移动要回气闸哪个方向。我看到的只有几英寸在他的面前,甚至不能考虑,我们用它来左右移动站的笔。
我试图与克里斯和巴蒂尔连:我能听到他们互相交谈,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我几乎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听不到我。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拼命地想行动计划。重要的是尽快进去。我知道,如果我留在原地,克里斯要跟从我,但多少时间我已经离开了?这是很难说。于是,我想起我的系绳。解开绳子机制发展的实力大约13 N,其中“拉”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想法是马马虎虎,但她是最好的我设法想出:跟着绳子的气闸。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耐心地处理摸索,我就开始移动,所有的时间考虑,如果它达到我的嘴怎么可以去除水中。我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 - 打开泄压阀靠近我的左耳:如果我开始降压,我可以把释放一些水,至少要等到它冻结,则流量将停止。但违反我的太空服的“洞” - 这是最极端的措施
。
我搬过来,我想,无限的时间(但我知道只用了几分钟)。最后,救灾的伟大意义,我通过水在我眼前的窗帘窥视,我设法看到一个隔热罩网关:多一点点,我会是安全的。其中一个是我收到的最后一个指令 - 里面马上走,无需等待克里斯。根据协议,我不得不去的气闸持续,因为先出来。但无论是我还是克里斯没有问题,改变在我们返回的命令。要和我闭上眼睛,我设法得到里面呆那么克里斯可以去。我觉得他后面的动作;克里斯进入气密室,并通过振动来判断,关闭舱口。在这一点上的连接切换到卡伦,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我可以听到它不够好。但据我所知,她不听我的,因为我继续尽管我已经回答了重复相同的指令。我跟着她,尽我所能的指令,但是当相机开始将空气泵,我失去了声音。水钻进了我的耳朵,我现在完全切断。
我试图保持运动到最低限度,以免打扰水我的头盔内。我不断地给自己的健康信息,说我是确定和抽空气进入室内可以继续。现在,当压力上升的网关,我知道,如果跑水了我,我可以随时打开头盔。难道我失去了知觉,但在任何情况下,比西装水槽更好。在某些时候,克里斯挤压她我的手套,我示意他显示“OK”。他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演讲之前就进入了气闸!
慢慢地爬行分钟,直到气闸室内的压力上升到正常,最后,用浮雕突然波动,我可以看到内门开了,整个团队聚集在她的身后,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们把我拉到尽可能快。卡伦解开我的头盔并轻轻地提起它我头上。费多尔·保罗马上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感谢他们,但我不听他们的话,因为我的耳朵和鼻子几分钟,将装满水。
宇宙 - 一个苛刻的,荒凉的边境,我们 - 研究人员,而不是殖民者。我们的工程师的技能和我们周围使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即使他们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有时会忘记它的技术。
最好不要忘记。
资料来源: habrahabr.ru/post/218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