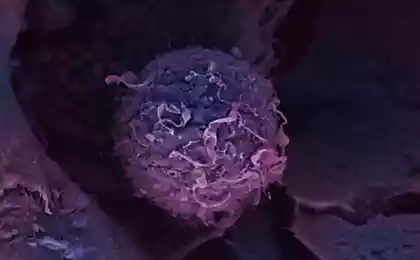1120
珏,我再次在医院
正如我答应教授先生,在三月初,我得到了在这里聚集地介绍我的身体异物进入医院的地方。而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的习惯,我会自动离开被推到她最喜欢的香皂盒,摄像头的口袋里的房子的时候。当你手边是一种能拍一些照片,然后你开始捕捉一切。这一次也不例外,虽然我一开始只在手术后的第三天制作的图片,所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切之前,当我再次开始独立在空间移动的时间。
通过barankin1000
75张照片

1.如何做经典开始从衣架报告))这是我在一个小储物柜在房间部门,地方虽小,但它不是谁打电话与一堆行李,足够内衣一些变化和T恤,肥皂rylnoe是一个酒店其中附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街道。免费保险箱是一个惊喜。蓬头垢面抛弃恤证明我的病情,弯曲至少有一点,我不能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免除事情恰恰扔在货架上自己。

2. Write'll所有的细节,我会写的好的和坏的将是很多很多的书。
为了,我被任命为3月6日早上8点来对进入房间,并定于3月11日的手术。收集袋后,有点取笑Irinka(最好是惹恼比经历,心烦),它与一堆ts.u.的离开农场时间几乎采取了他的弟弟送到了医院。
首先,有必要在入口处的警察局,在那里我立刻高兴的事实,我可能今晚回家联系服务,一张小桌子,是predstatsionar,那就是我今天的检查,如果我没有慢性病的任何疾病或ekspromntnyh我手术前不需要podshamanivat,然后我会去到了傍晚domoy.Nas那些希望下刀去了几个人,都送到专门的候车室有不舒服的椅子和一个单一的,更不舒服替补。然后在白天呼吁各种调查和文书工作。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只好坐在一个正常的椅子,或从一个地板移动到自己。通过“等候室”的墙是“房间”中,我们有能力做的茶,咖啡,取出机水气和无,吃果酱,黄油,蜂蜜饼干或点心或苹果,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没有限制。当它是午餐时间,患者在部门,我们也带来了午餐托盘。
16小时,我们有三个人,一个人被带到一个房间,20分钟后是驱动美国过去已经实施(幸运的),有人早点回家,有人把在众议院,而我们三人都与医生预计最后一次谈话在此之前,我个人有三个不同的医生3谈话。这个时候,我已经全紫,我就可以不切麻醉,我也不会感到接近八时硬椅子和众多的走让我行走的僵尸谁拥有一个目标,去的地方。就在这之前,同样的医生禁止我去几乎完全和尽可能少坐,然后上演了一场马拉松式的。
但是,一切都玩完了,我被要求接受采访,我很幸运,仍然另一个女人谁试图躺在板凳上,但她没能成功,太窄家店。
医生们长期威胁的后果我给了很多的文件,与他们在可能出现的风险上市签收,他们没有责任后,我签的文件。不要签署这些文件,你不运行的,只是这样的选择。
然后,他给了一个扭转这些腺体是要介绍我和欢呼声在我们聚会的最后一刻手终于找到了我的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乐呵呵地放心,现在正好是我的脊椎上一次的操作,在这里,他们被切断,然后研磨,posverlyat在这个和这个地方,这里一煮,它会被删除,而不是把他们在这部分在这里。然后我就被送回了家,并指示回到他们或周日3月10日18:00 3月11日,但无论是上午6:30,我选择了第一个选项。
上周日恢复列表ts.u. Irinka采取解压手提箱和笔记本电脑,去解决一个未知的时期臀位床。条款的住院时间从两周很模糊数月,预测操作,谁都无法结果。从我与当地的医生沟通,我已经知道,他们试图尽可能多的负倒病人,那么它变得更易于管理,并在取得成果的情况下,非常感谢,并且在出现错误或故障,您可以经常说的,“我们警告过了!” 。类似的想法是由患者的休息表示,一个女人谁留在我的“候车室”,与医生的第一次谈话后表示,“如果我是这样描述的一切,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来这里,但只是逐渐凋零回家»。
上周日晚上,分离似乎田园诗,几乎是空的走廊,一对夫妇的游客一起生病的亲人,小室和一个护士偶尔的呻吟声在走廊散步,从病房移动到病房招聘电话和灯入口灯的房子上面。
定义我进病房13号,我不遭受损害,甚至不会注意它,但邻居我立刻回忆说,很多酒店没有客房与此号码。

3.商会三,很好的位置在走廊的尽头被极少数人通过,绕过食物,我们是第一批。
更多的方式向众议院试图给我吃饭,但我拒绝了手术,明天不值钱牛肚馅。邻居是两个退休人员,一个德国人和波兰人,他们随时可以出院。这是令人愉快的dedulki只是打鼾得要命,晚上每次起床上厕所。开灯在床上,在前门,我去睡觉就在门口,门上厕所对面,我在那短暂的时刻,当他们可以睡刺目的光芒,并摔门唤醒。
当天上午,像往常一样,有没有给,被送到了阵雨,被迫装扮宝宝的汗衫背后没有系(记住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电影中的一个,出演他的第五点),纱布内衣和特制袜子,袜子必须点亮的提取物。然后,他给了一个平静的药片和四分之一到早上十点被带到自己的床上在手术室。轮流医生和护士走近术前,被他们的姓名及职务为代表,他们告诉自己的职责在操作过程中,任我游了一下,被插入导管的时候,我开始挖了一些解决方案。然后,他被要求将自己在手术台上,而我只要一躺下就可以了 - 马上换上麻醉面罩,所以我给予麻醉首次通过解决方案和注射前的一切。在我看来,我持续了十几秒,只设法积极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在环境的变化»
有没有什么梦想或幻想,我不知道,是从面罩直接传输到三方,问题的山坡:“你没事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肆无忌惮的喜悦的浪潮。我成功地捕捉塑料袋挂在我的头上留下了我在幕后管束的样子,一堆电线从毯子下走出来的一些设备与屏幕上的前臂刚开始收紧袖口自动式眼压计。在附近有几个床,其在不同程度上充足的是不同性别和年龄与我一样,软管和管的数目的患者。墙上的时钟显示6:15我希望这不是在上午。然而,与从哪个角度我看到靠在我的医生。 kinoshtampovym是正确的,有点扭曲的薄雾人俯身摄像头,声音是相当普遍的。
我相信,我是英雄,我可以回家了现在。问喝酒,干树是像骆驼酒精来了几个星期的液体中使用这一切只是时间的伏特加酒。在水中,他们拒绝 - 早说,拒绝撒尿,太:“你有一个导管移动全部由自己”,浪费它本身,而是欲望是正常的,所有的时间想忍住
。
他们问我动腿,再动手,每个人,包括我,很高兴,一切都正常运作。再有就是一个半小时趴在恢复室。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疼痛的腹部和背部,切嘴唇和鼻子在这里和那里,然后。嘴唇有一点点心痛至今,一直备受肿胀,皮肤从他们身上剥下完全,从而使头几天我买不起喝热茶,而在鼻子直至恢复讨厌管,氧气坚持的房子。
该室从适合自己家的门复员的心情回来,邻居们给了我一个嘈杂的欢呼由一对护士的加入和患者是在这一刻,在走廊上,但没有颜色。
我睡那天晚上不知何故失败。首先,疼痛,它是尽管痛下杀手,我滴进一步苦练每几个小时,不想每次取最小咬的位置和运动进入了我,尤其是在胃。其次,滴管,把管干扰了正常的手。三,躺在所有的时间在相同的位置,背部和全身发麻蠕动,对周围半夜,我试图把在他的身边,但我ochkanul在疯狂扭曲痛苦的第一个动作,躺在他的背部。第四,在左手伸出5导管和他们都牢固地附着用石膏几层,手在手术过程中抢了我可能更多,我梦见很快天亮,早上承诺所有导管被去除,腾出手(手退到两个天)。第五,除了打鼾的邻居,每隔一小时一个护士来检查我?
在第八分庭凌晨进入了一个新的护士与大卡车,这是一个弯路,没有强制性的旁路医生。每天自带一个护士感兴趣的问题,测量压力,温度和每天分发药物,注射,换绷带,帮助打扮,使永久标记在疾病的病史,医生来,无非出于需要,如果他看到的记录,并非所有的方式和手术后的第一天之内。
护士从所有的针,膏药释放我和晚餐答应从导管释放进入膀胱,但我还是不能起床。
然后来了一个医生谁是主要的,在我手术时,他说,一切都很好,他们能够在连续做两次手术一次,在体内出现了故障,否则它将有几天做一个。现在,我塞着铁,我会响在机场通道控制,但我没有磁铁在拖车上,金属没有磁性。并给了我一个特别的ausvays,说明我已经建立,有多少,什么大小应该总是随身携带,一下子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医生需要知道我有植入物,并在前面的最重要的表现在金属探测器。
几个小时终于消除了最后的导尿管,我立刻绘制彩陶其他没有中介沟通,原来,我还在坚持走出后门,两管在其结束两个像样的瓶子。这就是所谓的排水和我需要他去了三天,通过管所有的同时被吸入脓液非常难受的事情。当你躺在逃生印刷机的地方你回来时,你起床,你需要动手拖瓶,当你躺下时,必须先理顺软管,把瓶子放在床头的两侧,不断感受异物在里面,它可能是纯粹的心理因素。<溴/ >
第一次起来很害怕,我记得当上升疼痛几次少,在上升阶段中它是以前的操作之后,下一次。首先,拉起来,把你的脚在床上,在膝盖弯曲,现在靠在他们,感觉他的手在右边站在床上休息时他的腿,拉着他的手臂,诅咒和吞咽鼻涕眼泪转向一边,一名护士在那里,但是有助于议会研究需要。躺下,休息,现在调整呼吸轻轻地降落在地板上的脚,躺下来,他把他的手搁在床垫和推他轻轻地(这很重要)翻译成垂直状态的身体 - 我坐下!此外,烟,他的呼吸,赶走从他的眼睛的面纱,靠在床上,他的手的边缘,并推动成为一个半弯曲的位置,然后慢慢地,哽咽着,拉直。而当恢复正常的心跳和呼吸,你可以尝试走,更主要的是不要急着起来,忘了正常的步骤,只是小步。
一切都很顺利,我独自上厕所,回到了床上,只好骗posleobeda,直到它是一种物理治疗师。这时,书面德国邻居和另一位邻居同意一名医生,我被带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离高考。
图为在前台是一张床,在那里我度过了第一个两晚,但留给我的床靠窗的地方。

4.当我由众议院运输,前门进口的新邻居。普通祖父德,让国家结构没有改变:俄语,波兰语,德语。真正的全新印象中的疯狂和硬化完全丧失。它是关于什么兴致勃勃地自言自语,随机回答员工的问题,或简单地忽略他们。但只要他的电话响了,他马上变得非常理解地与对话者沟通。所以这是所有的时间,而他留与我们在众议院,现实完全停电,直到不来电或来的亲戚或朋友,并与他们交谈就像一个正常的人。
当我写的,我被运到桌子上,在小车的脚“王牌”靠窗的座位,床noutom。

5.在床上要住。首先,每床,床头柜带高度可调的铰接盖,小车轮子,移动方便提供。立即指定的电话号码,可选择你可以得到一个当地的号码打电话,并接受按标准费率收取的呼叫。小屏幕 - 电视,连接到它无需耳机看电视耳机是禁止的。我没有使用任何电话,没有电视,携带的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无线网络在房间里体面的,它的成本2,50元一天,或15至50%的一周,我花了一天的第一天,第二天术后一周相连。

6.在床上方便的遥控器,你可以完全的舒适为您提供便利的位置安排。更积极,我很喜欢后,掌握了管理结构的所有智慧。顺便说我是幸运的,床是最新款式,工作几乎是悄无声息,而不是晚上辗转反侧痛苦的地方拉伤自己的我,点击按钮将自身与技术的奇迹的帮助,而不会干扰睡眠的邻居一个舒适的位置。但我的爷爷带回美国的第三天,在床上曾大声的商业大楼的电梯。

7.由于该床将继续参观了病房。在墙壁上卫生间挂一次性手套三种尺寸和消毒液的手。医生和护士全自动使用这些属性始终。如果你打算举行某种程序的病人,然后立即戴上手套,然后扔在垃圾桶里,然后消毒双手。如果你刚刚进入一个房间,聊不碰任何在此之前,当输出还需要消毒双手。右墙壁上可以看到一小卫士,去病房护士立即按下按钮出现在走廊入口处众议院的火焰点亮为绿色,这意味着病房不能去给外人,而其他工作人员知道去哪里找同事。还有一个内置扬声器和工作人员交谈,互相从不同腔室。如果其他房间有人按下呼叫按钮的人员,到病房里这点是工作人员开始发出蜂鸣声扬声器和显示在显示房号,并从被供给的信号(前提是他们不要忘记入口处点击按钮)床位数。在那里,面板上的控制面板在房间里所有的灯,你可以调整每个灯泡的亮度。

32.
35.
55.
56.
63.
64.
70.
72.
资料来源:
通过barankin1000
75张照片

1.如何做经典开始从衣架报告))这是我在一个小储物柜在房间部门,地方虽小,但它不是谁打电话与一堆行李,足够内衣一些变化和T恤,肥皂rylnoe是一个酒店其中附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街道。免费保险箱是一个惊喜。蓬头垢面抛弃恤证明我的病情,弯曲至少有一点,我不能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免除事情恰恰扔在货架上自己。

2. Write'll所有的细节,我会写的好的和坏的将是很多很多的书。
为了,我被任命为3月6日早上8点来对进入房间,并定于3月11日的手术。收集袋后,有点取笑Irinka(最好是惹恼比经历,心烦),它与一堆ts.u.的离开农场时间几乎采取了他的弟弟送到了医院。
首先,有必要在入口处的警察局,在那里我立刻高兴的事实,我可能今晚回家联系服务,一张小桌子,是predstatsionar,那就是我今天的检查,如果我没有慢性病的任何疾病或ekspromntnyh我手术前不需要podshamanivat,然后我会去到了傍晚domoy.Nas那些希望下刀去了几个人,都送到专门的候车室有不舒服的椅子和一个单一的,更不舒服替补。然后在白天呼吁各种调查和文书工作。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只好坐在一个正常的椅子,或从一个地板移动到自己。通过“等候室”的墙是“房间”中,我们有能力做的茶,咖啡,取出机水气和无,吃果酱,黄油,蜂蜜饼干或点心或苹果,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没有限制。当它是午餐时间,患者在部门,我们也带来了午餐托盘。
16小时,我们有三个人,一个人被带到一个房间,20分钟后是驱动美国过去已经实施(幸运的),有人早点回家,有人把在众议院,而我们三人都与医生预计最后一次谈话在此之前,我个人有三个不同的医生3谈话。这个时候,我已经全紫,我就可以不切麻醉,我也不会感到接近八时硬椅子和众多的走让我行走的僵尸谁拥有一个目标,去的地方。就在这之前,同样的医生禁止我去几乎完全和尽可能少坐,然后上演了一场马拉松式的。
但是,一切都玩完了,我被要求接受采访,我很幸运,仍然另一个女人谁试图躺在板凳上,但她没能成功,太窄家店。
医生们长期威胁的后果我给了很多的文件,与他们在可能出现的风险上市签收,他们没有责任后,我签的文件。不要签署这些文件,你不运行的,只是这样的选择。
然后,他给了一个扭转这些腺体是要介绍我和欢呼声在我们聚会的最后一刻手终于找到了我的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乐呵呵地放心,现在正好是我的脊椎上一次的操作,在这里,他们被切断,然后研磨,posverlyat在这个和这个地方,这里一煮,它会被删除,而不是把他们在这部分在这里。然后我就被送回了家,并指示回到他们或周日3月10日18:00 3月11日,但无论是上午6:30,我选择了第一个选项。
上周日恢复列表ts.u. Irinka采取解压手提箱和笔记本电脑,去解决一个未知的时期臀位床。条款的住院时间从两周很模糊数月,预测操作,谁都无法结果。从我与当地的医生沟通,我已经知道,他们试图尽可能多的负倒病人,那么它变得更易于管理,并在取得成果的情况下,非常感谢,并且在出现错误或故障,您可以经常说的,“我们警告过了!” 。类似的想法是由患者的休息表示,一个女人谁留在我的“候车室”,与医生的第一次谈话后表示,“如果我是这样描述的一切,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来这里,但只是逐渐凋零回家»。
上周日晚上,分离似乎田园诗,几乎是空的走廊,一对夫妇的游客一起生病的亲人,小室和一个护士偶尔的呻吟声在走廊散步,从病房移动到病房招聘电话和灯入口灯的房子上面。
定义我进病房13号,我不遭受损害,甚至不会注意它,但邻居我立刻回忆说,很多酒店没有客房与此号码。

3.商会三,很好的位置在走廊的尽头被极少数人通过,绕过食物,我们是第一批。
更多的方式向众议院试图给我吃饭,但我拒绝了手术,明天不值钱牛肚馅。邻居是两个退休人员,一个德国人和波兰人,他们随时可以出院。这是令人愉快的dedulki只是打鼾得要命,晚上每次起床上厕所。开灯在床上,在前门,我去睡觉就在门口,门上厕所对面,我在那短暂的时刻,当他们可以睡刺目的光芒,并摔门唤醒。
当天上午,像往常一样,有没有给,被送到了阵雨,被迫装扮宝宝的汗衫背后没有系(记住这个安东尼·霍普金斯,电影中的一个,出演他的第五点),纱布内衣和特制袜子,袜子必须点亮的提取物。然后,他给了一个平静的药片和四分之一到早上十点被带到自己的床上在手术室。轮流医生和护士走近术前,被他们的姓名及职务为代表,他们告诉自己的职责在操作过程中,任我游了一下,被插入导管的时候,我开始挖了一些解决方案。然后,他被要求将自己在手术台上,而我只要一躺下就可以了 - 马上换上麻醉面罩,所以我给予麻醉首次通过解决方案和注射前的一切。在我看来,我持续了十几秒,只设法积极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在环境的变化»
有没有什么梦想或幻想,我不知道,是从面罩直接传输到三方,问题的山坡:“你没事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肆无忌惮的喜悦的浪潮。我成功地捕捉塑料袋挂在我的头上留下了我在幕后管束的样子,一堆电线从毯子下走出来的一些设备与屏幕上的前臂刚开始收紧袖口自动式眼压计。在附近有几个床,其在不同程度上充足的是不同性别和年龄与我一样,软管和管的数目的患者。墙上的时钟显示6:15我希望这不是在上午。然而,与从哪个角度我看到靠在我的医生。 kinoshtampovym是正确的,有点扭曲的薄雾人俯身摄像头,声音是相当普遍的。
我相信,我是英雄,我可以回家了现在。问喝酒,干树是像骆驼酒精来了几个星期的液体中使用这一切只是时间的伏特加酒。在水中,他们拒绝 - 早说,拒绝撒尿,太:“你有一个导管移动全部由自己”,浪费它本身,而是欲望是正常的,所有的时间想忍住
。
他们问我动腿,再动手,每个人,包括我,很高兴,一切都正常运作。再有就是一个半小时趴在恢复室。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疼痛的腹部和背部,切嘴唇和鼻子在这里和那里,然后。嘴唇有一点点心痛至今,一直备受肿胀,皮肤从他们身上剥下完全,从而使头几天我买不起喝热茶,而在鼻子直至恢复讨厌管,氧气坚持的房子。
该室从适合自己家的门复员的心情回来,邻居们给了我一个嘈杂的欢呼由一对护士的加入和患者是在这一刻,在走廊上,但没有颜色。
我睡那天晚上不知何故失败。首先,疼痛,它是尽管痛下杀手,我滴进一步苦练每几个小时,不想每次取最小咬的位置和运动进入了我,尤其是在胃。其次,滴管,把管干扰了正常的手。三,躺在所有的时间在相同的位置,背部和全身发麻蠕动,对周围半夜,我试图把在他的身边,但我ochkanul在疯狂扭曲痛苦的第一个动作,躺在他的背部。第四,在左手伸出5导管和他们都牢固地附着用石膏几层,手在手术过程中抢了我可能更多,我梦见很快天亮,早上承诺所有导管被去除,腾出手(手退到两个天)。第五,除了打鼾的邻居,每隔一小时一个护士来检查我?
在第八分庭凌晨进入了一个新的护士与大卡车,这是一个弯路,没有强制性的旁路医生。每天自带一个护士感兴趣的问题,测量压力,温度和每天分发药物,注射,换绷带,帮助打扮,使永久标记在疾病的病史,医生来,无非出于需要,如果他看到的记录,并非所有的方式和手术后的第一天之内。
护士从所有的针,膏药释放我和晚餐答应从导管释放进入膀胱,但我还是不能起床。
然后来了一个医生谁是主要的,在我手术时,他说,一切都很好,他们能够在连续做两次手术一次,在体内出现了故障,否则它将有几天做一个。现在,我塞着铁,我会响在机场通道控制,但我没有磁铁在拖车上,金属没有磁性。并给了我一个特别的ausvays,说明我已经建立,有多少,什么大小应该总是随身携带,一下子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医生需要知道我有植入物,并在前面的最重要的表现在金属探测器。
几个小时终于消除了最后的导尿管,我立刻绘制彩陶其他没有中介沟通,原来,我还在坚持走出后门,两管在其结束两个像样的瓶子。这就是所谓的排水和我需要他去了三天,通过管所有的同时被吸入脓液非常难受的事情。当你躺在逃生印刷机的地方你回来时,你起床,你需要动手拖瓶,当你躺下时,必须先理顺软管,把瓶子放在床头的两侧,不断感受异物在里面,它可能是纯粹的心理因素。<溴/ >
第一次起来很害怕,我记得当上升疼痛几次少,在上升阶段中它是以前的操作之后,下一次。首先,拉起来,把你的脚在床上,在膝盖弯曲,现在靠在他们,感觉他的手在右边站在床上休息时他的腿,拉着他的手臂,诅咒和吞咽鼻涕眼泪转向一边,一名护士在那里,但是有助于议会研究需要。躺下,休息,现在调整呼吸轻轻地降落在地板上的脚,躺下来,他把他的手搁在床垫和推他轻轻地(这很重要)翻译成垂直状态的身体 - 我坐下!此外,烟,他的呼吸,赶走从他的眼睛的面纱,靠在床上,他的手的边缘,并推动成为一个半弯曲的位置,然后慢慢地,哽咽着,拉直。而当恢复正常的心跳和呼吸,你可以尝试走,更主要的是不要急着起来,忘了正常的步骤,只是小步。
一切都很顺利,我独自上厕所,回到了床上,只好骗posleobeda,直到它是一种物理治疗师。这时,书面德国邻居和另一位邻居同意一名医生,我被带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离高考。
图为在前台是一张床,在那里我度过了第一个两晚,但留给我的床靠窗的地方。

4.当我由众议院运输,前门进口的新邻居。普通祖父德,让国家结构没有改变:俄语,波兰语,德语。真正的全新印象中的疯狂和硬化完全丧失。它是关于什么兴致勃勃地自言自语,随机回答员工的问题,或简单地忽略他们。但只要他的电话响了,他马上变得非常理解地与对话者沟通。所以这是所有的时间,而他留与我们在众议院,现实完全停电,直到不来电或来的亲戚或朋友,并与他们交谈就像一个正常的人。
当我写的,我被运到桌子上,在小车的脚“王牌”靠窗的座位,床noutom。

5.在床上要住。首先,每床,床头柜带高度可调的铰接盖,小车轮子,移动方便提供。立即指定的电话号码,可选择你可以得到一个当地的号码打电话,并接受按标准费率收取的呼叫。小屏幕 - 电视,连接到它无需耳机看电视耳机是禁止的。我没有使用任何电话,没有电视,携带的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无线网络在房间里体面的,它的成本2,50元一天,或15至50%的一周,我花了一天的第一天,第二天术后一周相连。

6.在床上方便的遥控器,你可以完全的舒适为您提供便利的位置安排。更积极,我很喜欢后,掌握了管理结构的所有智慧。顺便说我是幸运的,床是最新款式,工作几乎是悄无声息,而不是晚上辗转反侧痛苦的地方拉伤自己的我,点击按钮将自身与技术的奇迹的帮助,而不会干扰睡眠的邻居一个舒适的位置。但我的爷爷带回美国的第三天,在床上曾大声的商业大楼的电梯。

7.由于该床将继续参观了病房。在墙壁上卫生间挂一次性手套三种尺寸和消毒液的手。医生和护士全自动使用这些属性始终。如果你打算举行某种程序的病人,然后立即戴上手套,然后扔在垃圾桶里,然后消毒双手。如果你刚刚进入一个房间,聊不碰任何在此之前,当输出还需要消毒双手。右墙壁上可以看到一小卫士,去病房护士立即按下按钮出现在走廊入口处众议院的火焰点亮为绿色,这意味着病房不能去给外人,而其他工作人员知道去哪里找同事。还有一个内置扬声器和工作人员交谈,互相从不同腔室。如果其他房间有人按下呼叫按钮的人员,到病房里这点是工作人员开始发出蜂鸣声扬声器和显示在显示房号,并从被供给的信号(前提是他们不要忘记入口处点击按钮)床位数。在那里,面板上的控制面板在房间里所有的灯,你可以调整每个灯泡的亮度。

32.
35.
55.
56.
63.
64.
70.
72.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