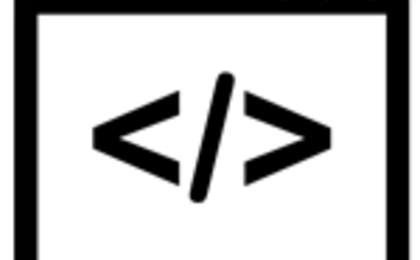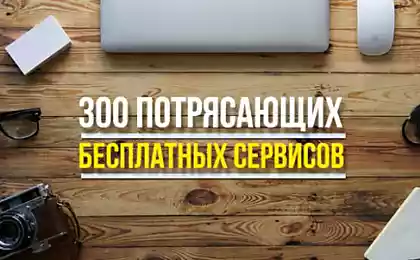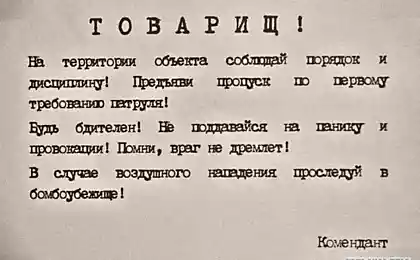866
工作军事记者(4张)
纽约时报若昂·席尔瓦的摄影记者谈他的工作,一年后,他失去了双腿被炸在坎大哈矿井。
“在23日的早晨,当我踩到了地雷2010年10月的那一刻,我很清醒地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周围的人死去这么多的人,我已经死了,在朋友的手里 - 我不是夸大 - 当它发生了,我只是想,“全部清除。轮到我了。它的时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上午 - 与往常一样,当你与军方出去。有麻烦的迹象。我们并没有出手。正常的边境巡逻。士兵们谁不属于该页面的纽约时报,和报纸的休息,太,说实话。因此,这里是今天上午。

坎大哈的阿尔甘达卜地区。工兵组 - 私人Laplaunt(左),军士麦克斯韦(右)和涵盖警长沃特曼(中心) - 领先排的,检查农村公路和邻里我是第三个链条。男人,这是第一个,带动了服务犬。他的身后是另一个负责安全,然后I.它不是狗闻到。然后来了的家伙,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对我来说,它的工作。我听到一个机械的点击。我意识到,这是不好的。醒来时,已经躺在地上脸朝下,裹着尘土飞扬,有清醒的认识:只要地雷爆炸,想到什么好
。
我看到了,我的腿没了,周围覆盖的惊喜。我说,“伙计们,帮助我。”他们转过身来,看到我在地上,立刻得到了正事。拖着我出去患处的一对夫妇的米。目前已经到了,医生开始给我。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坦率地说,他们是不是很好,但我试图捕捉事件。我知道事情不好,但我觉得他还活着。肾上腺素淹没。我很清醒,并意识到发生的一切。所以,我做了几个镜头。于是他放弃了他的相机,去B计划,这是拿起手机。我拨了号码薇薇安,他的妻子说:“我没有双腿,可是生活,可能会吧。”顺便说一句,我有两个孩子。然后,他把电话递给记者,她跟周慧敏和安慰她。
然后,我躺下来有一支香烟。同时,医生们疯狂地让我的东西:吊带,直接注射入胸部和一系列精美绝伦的东西。这些家伙救了我的命。直升机降落运送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前我是直升机里面,我是在完全和绝对的意识。在那里,我终于通过了。
跟我的情况是什么新鲜事。记者被杀害或自古以来致残。从那时起,当有人拿着相机第一次上战场。而我却不幸成为其中之一。那一天,我拼命倒霉,并在同一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米娜被拴在一个桶,这是约15磅自制炸药,以及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爆炸。有了这个第二次爆炸,剩下的我,很容易适合在一个火柴盒。这是惊人的什么惊喜,有时生活带来。称之为上帝的普罗维登斯,叫运气,但不知何故,你叫 - 我很感激
。

集团提请注意任何异物,包括爆炸陨石坑先前检测到矿井
现在,我在中心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沃尔特·里德在华盛顿,美国最大的军医院 - 君子)有些时候不想下床天。但是,每一个新的一天说服我,我是多么幸运。总会有人谁是雪上加霜。二十多岁的年轻球员 - 他们截肢3四肢和生殖器,它们将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它是不容易的。还有很多孩子患上抑郁症,他们都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一切。
但它也鼓励 - 因为你要学会明白:你怎么不一直不好,有人比你差
。
自那时以来,花了九个月。对于行业处于困难时期。特别讨厌脱颖而出四月。 ( - 2011年春季军事摄影记者在利比亚遇难 - 君子添赫瑟林顿,克里斯Hondros和安东Hammerl) - 我们失去了三个朋友添,克里斯和安东尼。利比亚是用锋利的脾气小姐。
或许,这将是一年前我来完全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我还需要一点勇气,毅力和一点 - 如果我们坦率地说 - 多一点药比我能吞下
当我看到,我没有脚,我没有意识到它是多么严重。只觉得自己的一些本能的水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知道,爆炸损坏了尿道。我受伤的内脏。这损害了肛门和我开发败血症。正是这一点,因为我快死了。的斗争是对细菌,而不是腿。
通常情况下,截肢的地步,你已经对假体放置后,它需要大约10周。就我而言,那是大约五个月,因为我的身体继续攻击的感染。医生不得不完全恢复肛门和尿道。七月份我通过管子撒尿在一个塑料袋。幸运的是,这一切的背后。我还是用一个回肠造口术,但最后的操作,并修复它。
我想我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它再次之一。那是当然,我的脚没了。他们永远不会长大。但你知道,这是什么。然而,什么都没有。我还活着,我在这里。生活还没有结束。
经常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谁砍对方的人,而这一切,甚至照片吗?”但是,你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如果你想帮助的人,没有必要成为一名摄影师。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帮助。我不只是出货打伤他的车后座上,并竞相与他们的医院。
只是遗憾的是,有时图像获得如此强大,似乎背后的摄像头 -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而事实并非如此。画面捕捉的眼睛,立刻印在脑海中。而其中的一些图片不离开我们到永远。

警长马克斯韦尔,在皮带的狗高级官员 - 在爆炸前几秒钟由若昂·席尔瓦框架
我最亲密的朋友凯文·卡特(南非摄影师,英联邦棒棒俱乐部的四名成员,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是席尔瓦的部分之一 - 君子),最终自杀身亡。他把名画苏丹:在泥地,脸朝下,是一个女孩,她的秃鹫手表。他非常批评这张照片。谁没有什么激励他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丝毫的想法的人 - 他们批评他,直到他终于成为纠结在它的内部矛盾。他被授予了普利策一个月后自杀。
人们相信默认看哪,无情的摄影师刚刚路过的孩子,按下按钮。事实上,孩子是从一个施粥的人道主义使命几百米。但是,这是摄影的功率。你被分配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使得它能够播放,而且它是一个强大的形象。他派饥荒的消息。突然,从哪儿冒出来,在苏丹流入资金。在做出这个画面,他救更多的生命比如果不是做到了。在镜头的另一面 - 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那个人想要得到一个信息,它传达给世界,仍然屹立不倒
。
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意外。在高中时,我从来没有去到任何fotokruzhke。我的朋友学习平面设计,和的事情之一,他的照片。有一次,他被赋予的速度,运动的主题工作。他就跟着我们到赛道取车的照片,然后我想:“好了好了,并且在这个角色,我可以看到自己。这样的事情对我的口味»。
然后,我做了我第一次生命中的图片。而我就像一只苍蝇叮咬。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正是我想做的事。然后就结束了种族隔离,曼德拉被释放,全国充斥着政治暴力 - 一个残酷的,这样需要的特写镜头。四年在南非杀害了15000,然后把所有的20000人,而没有坦克和火炮。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家乡,在我家门口,我觉得是有需要 - 所有的记录,并告诉全世界的人是要灭亡
我开始移动非洲各地,并面临着许多其他的冲突。应该说,这场战争 - 不仅是我在做什么。我不喜欢把自己一个战地摄影师。当然,这是我的专业,我的激情。但参观战争 - 是不是摄影记者的唯一责任
。
在沃尔特·里德,我并没有吸引到照片。前五个星期,我在重症监护室。我是如此下药,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模糊。在手术台上,我走过的日子去了。只有七个半月我就能够下床。然后,我被送到了重症康复中心(军事医学中心沃尔特里德系 - 君子)为军队,所有列车的水手和士兵四肢截肢。首先,我去睡觉,并在其上我提出在运动垫上,在这里我们做了练习。过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动轮椅。

爆炸后几秒钟重伤若昂·席尔瓦另需三枪,然后从手中
释放相机
而趴在众议院在恢复室,在你设定的目标。医生说争夺,“所以,现在你需要去到一个新的水平。”专科或物理治疗师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会做的负重测试,之后你可以走。”你想,“哦,哇。嗯,这是什么东西。目前专注于什么»。
现在我住的门诊病人在一个特殊的镇受伤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但我还没有返回。我会做一个横截面,收紧你的腹部肌肉,以解除结肠造口术,并重新连接小肠结肠。
在康复过程中会采取最有可能的一年。我需要学习如何做没有拐杖。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运行 - 当我说跑,我并不想在假肢上运行。我要对这些脚奔跑在这里,所以,当我回去工作,要能短横线(胡安·席尔瓦双腿截肢膝盖以下 - 君子)。从容的运行将没有名字,但它仍然必须运行。特别是,现在我觉得我在恩典对方任何方式。
我会再次拍照。将继续努力,为纽约时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我能回去的军事新闻,并会做的。怀疑在这一点上我没有。
我们制定这样说:腿我没有更多的,但我仍然会导致有一天他的女儿在过道。不过,我看到我的儿子将如何成长,如何弄成暴跌。
虽然他们仍然太小。 “教皇没有腿 - 但他有现在他的脚像一个机器人,很酷。”那么,你知道:“我爸爸 - 一个变压器!”我们从他们那里没有隐瞒;我们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想他们是我的骄傲»。
来源
“在23日的早晨,当我踩到了地雷2010年10月的那一刻,我很清醒地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周围的人死去这么多的人,我已经死了,在朋友的手里 - 我不是夸大 - 当它发生了,我只是想,“全部清除。轮到我了。它的时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上午 - 与往常一样,当你与军方出去。有麻烦的迹象。我们并没有出手。正常的边境巡逻。士兵们谁不属于该页面的纽约时报,和报纸的休息,太,说实话。因此,这里是今天上午。

坎大哈的阿尔甘达卜地区。工兵组 - 私人Laplaunt(左),军士麦克斯韦(右)和涵盖警长沃特曼(中心) - 领先排的,检查农村公路和邻里我是第三个链条。男人,这是第一个,带动了服务犬。他的身后是另一个负责安全,然后I.它不是狗闻到。然后来了的家伙,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对我来说,它的工作。我听到一个机械的点击。我意识到,这是不好的。醒来时,已经躺在地上脸朝下,裹着尘土飞扬,有清醒的认识:只要地雷爆炸,想到什么好
。
我看到了,我的腿没了,周围覆盖的惊喜。我说,“伙计们,帮助我。”他们转过身来,看到我在地上,立刻得到了正事。拖着我出去患处的一对夫妇的米。目前已经到了,医生开始给我。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坦率地说,他们是不是很好,但我试图捕捉事件。我知道事情不好,但我觉得他还活着。肾上腺素淹没。我很清醒,并意识到发生的一切。所以,我做了几个镜头。于是他放弃了他的相机,去B计划,这是拿起手机。我拨了号码薇薇安,他的妻子说:“我没有双腿,可是生活,可能会吧。”顺便说一句,我有两个孩子。然后,他把电话递给记者,她跟周慧敏和安慰她。
然后,我躺下来有一支香烟。同时,医生们疯狂地让我的东西:吊带,直接注射入胸部和一系列精美绝伦的东西。这些家伙救了我的命。直升机降落运送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前我是直升机里面,我是在完全和绝对的意识。在那里,我终于通过了。
跟我的情况是什么新鲜事。记者被杀害或自古以来致残。从那时起,当有人拿着相机第一次上战场。而我却不幸成为其中之一。那一天,我拼命倒霉,并在同一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米娜被拴在一个桶,这是约15磅自制炸药,以及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爆炸。有了这个第二次爆炸,剩下的我,很容易适合在一个火柴盒。这是惊人的什么惊喜,有时生活带来。称之为上帝的普罗维登斯,叫运气,但不知何故,你叫 - 我很感激
。

集团提请注意任何异物,包括爆炸陨石坑先前检测到矿井
现在,我在中心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沃尔特·里德在华盛顿,美国最大的军医院 - 君子)有些时候不想下床天。但是,每一个新的一天说服我,我是多么幸运。总会有人谁是雪上加霜。二十多岁的年轻球员 - 他们截肢3四肢和生殖器,它们将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它是不容易的。还有很多孩子患上抑郁症,他们都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一切。
但它也鼓励 - 因为你要学会明白:你怎么不一直不好,有人比你差
。
自那时以来,花了九个月。对于行业处于困难时期。特别讨厌脱颖而出四月。 ( - 2011年春季军事摄影记者在利比亚遇难 - 君子添赫瑟林顿,克里斯Hondros和安东Hammerl) - 我们失去了三个朋友添,克里斯和安东尼。利比亚是用锋利的脾气小姐。
或许,这将是一年前我来完全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我还需要一点勇气,毅力和一点 - 如果我们坦率地说 - 多一点药比我能吞下
当我看到,我没有脚,我没有意识到它是多么严重。只觉得自己的一些本能的水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知道,爆炸损坏了尿道。我受伤的内脏。这损害了肛门和我开发败血症。正是这一点,因为我快死了。的斗争是对细菌,而不是腿。
通常情况下,截肢的地步,你已经对假体放置后,它需要大约10周。就我而言,那是大约五个月,因为我的身体继续攻击的感染。医生不得不完全恢复肛门和尿道。七月份我通过管子撒尿在一个塑料袋。幸运的是,这一切的背后。我还是用一个回肠造口术,但最后的操作,并修复它。
我想我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它再次之一。那是当然,我的脚没了。他们永远不会长大。但你知道,这是什么。然而,什么都没有。我还活着,我在这里。生活还没有结束。
经常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谁砍对方的人,而这一切,甚至照片吗?”但是,你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如果你想帮助的人,没有必要成为一名摄影师。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帮助。我不只是出货打伤他的车后座上,并竞相与他们的医院。
只是遗憾的是,有时图像获得如此强大,似乎背后的摄像头 -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而事实并非如此。画面捕捉的眼睛,立刻印在脑海中。而其中的一些图片不离开我们到永远。

警长马克斯韦尔,在皮带的狗高级官员 - 在爆炸前几秒钟由若昂·席尔瓦框架
我最亲密的朋友凯文·卡特(南非摄影师,英联邦棒棒俱乐部的四名成员,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是席尔瓦的部分之一 - 君子),最终自杀身亡。他把名画苏丹:在泥地,脸朝下,是一个女孩,她的秃鹫手表。他非常批评这张照片。谁没有什么激励他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丝毫的想法的人 - 他们批评他,直到他终于成为纠结在它的内部矛盾。他被授予了普利策一个月后自杀。
人们相信默认看哪,无情的摄影师刚刚路过的孩子,按下按钮。事实上,孩子是从一个施粥的人道主义使命几百米。但是,这是摄影的功率。你被分配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使得它能够播放,而且它是一个强大的形象。他派饥荒的消息。突然,从哪儿冒出来,在苏丹流入资金。在做出这个画面,他救更多的生命比如果不是做到了。在镜头的另一面 - 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那个人想要得到一个信息,它传达给世界,仍然屹立不倒
。
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意外。在高中时,我从来没有去到任何fotokruzhke。我的朋友学习平面设计,和的事情之一,他的照片。有一次,他被赋予的速度,运动的主题工作。他就跟着我们到赛道取车的照片,然后我想:“好了好了,并且在这个角色,我可以看到自己。这样的事情对我的口味»。
然后,我做了我第一次生命中的图片。而我就像一只苍蝇叮咬。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正是我想做的事。然后就结束了种族隔离,曼德拉被释放,全国充斥着政治暴力 - 一个残酷的,这样需要的特写镜头。四年在南非杀害了15000,然后把所有的20000人,而没有坦克和火炮。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家乡,在我家门口,我觉得是有需要 - 所有的记录,并告诉全世界的人是要灭亡
我开始移动非洲各地,并面临着许多其他的冲突。应该说,这场战争 - 不仅是我在做什么。我不喜欢把自己一个战地摄影师。当然,这是我的专业,我的激情。但参观战争 - 是不是摄影记者的唯一责任
。
在沃尔特·里德,我并没有吸引到照片。前五个星期,我在重症监护室。我是如此下药,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模糊。在手术台上,我走过的日子去了。只有七个半月我就能够下床。然后,我被送到了重症康复中心(军事医学中心沃尔特里德系 - 君子)为军队,所有列车的水手和士兵四肢截肢。首先,我去睡觉,并在其上我提出在运动垫上,在这里我们做了练习。过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动轮椅。

爆炸后几秒钟重伤若昂·席尔瓦另需三枪,然后从手中
释放相机
而趴在众议院在恢复室,在你设定的目标。医生说争夺,“所以,现在你需要去到一个新的水平。”专科或物理治疗师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会做的负重测试,之后你可以走。”你想,“哦,哇。嗯,这是什么东西。目前专注于什么»。
现在我住的门诊病人在一个特殊的镇受伤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但我还没有返回。我会做一个横截面,收紧你的腹部肌肉,以解除结肠造口术,并重新连接小肠结肠。
在康复过程中会采取最有可能的一年。我需要学习如何做没有拐杖。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运行 - 当我说跑,我并不想在假肢上运行。我要对这些脚奔跑在这里,所以,当我回去工作,要能短横线(胡安·席尔瓦双腿截肢膝盖以下 - 君子)。从容的运行将没有名字,但它仍然必须运行。特别是,现在我觉得我在恩典对方任何方式。
我会再次拍照。将继续努力,为纽约时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我能回去的军事新闻,并会做的。怀疑在这一点上我没有。
我们制定这样说:腿我没有更多的,但我仍然会导致有一天他的女儿在过道。不过,我看到我的儿子将如何成长,如何弄成暴跌。
虽然他们仍然太小。 “教皇没有腿 - 但他有现在他的脚像一个机器人,很酷。”那么,你知道:“我爸爸 - 一个变压器!”我们从他们那里没有隐瞒;我们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想他们是我的骄傲»。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