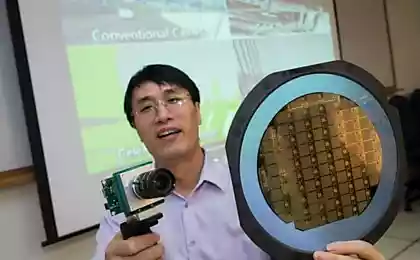679
神经学家约翰*莉莉关于一个不存在的客观性和恐惧感
美国的医生、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学家 约翰*莉莉 (1915年—2001年)最出名的是他的大胆探索性质的意识。 他第一次开始研究如何将人类的大脑和心理功能在隔离。
莉莉进行的研究在感觉剥夺(浮)—闭胶囊与盐水,而这株的人从任何的感觉,并致幻用于实验。 出版了翻译摘录的一次采访约翰*莉莉,其中一个科学家会谈的有关规则的浮动的,根本不存在客观性和意义的恐惧。

当我16岁时,我正准备上大学,我写为校报的文章题为"现实"。 她确定我的人生道路和方向的想法、联系与学习活动和结构的大脑。
我去加州理工学院,开始研究生物科学的和对第一次参加了一个课程在神经解剖学的。 然后我去达特茅斯医学院,还有另外一个当然的,然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有研究大脑更进一步。 所以我了解了更多关于他比我可以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孩子,我去过天主教学校和学到了很多有关于粗糙的男孩和漂亮的女孩。 我爱上了玛格丽特*万斯,但没有告诉她任何东西,尽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关于性的,所以我幻想着我们如何交换尿。
我的父亲是一个机带,必须放在肚子上或一个软点,以及一个电动机,其带的振动。 有一次我站在这台机器,振动刺激的我性感的地区。 然后我突然感觉我的身体似乎分裂开来,而我的整个人被笼罩的喜悦。 这是真棒。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牧师,他说,"你手淫吧!"。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和回答说,"不"。 他称这是一个弥天大罪。 我离开教堂。 我想,"如果他们叫来自上帝的礼物一个弥天大罪,以狱与他们。 那不是我的上帝,他们只是试图控制人。"
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一个陷阱,让人。 我更喜欢条款"内部共识"和"外部的理智。" 国内清醒—这是你的生命你的内心。 这是非常私人的,你通常不会让任何人,因为将完全疯了,虽然我经常见面的人可以谈论它。
当你在一个剥夺的坦克,外部理智就会消失。 外头脑清楚是什么我们现在所做的,在对话过程中分享想法等等。 我不是在谈论你的内在理智和记者不会告诉她的。 然而,如果我们内部的神智部分相吻合,我们可以做朋友
我从来没有使用这个词"幻觉",因为它是高度desorientiert的。 它是一个人为的解释原则,因此,没有用的。 Richard Feynman,物理学家,陷入被剥夺罐20倍。 每次他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小时,然后送给我的邮件是他新书的物理学。
在标题页,费曼写道:"谢谢你的幻觉。" 我叫他,并说,"听着,迪克,你是不是像个科学家。 你应该介绍你有什么经验丰富的,并且不把它扔在垃圾桶标"的幻觉的"。 这是一个任期从精神病学领域,这扭曲了意义;没有什么从你的经验不能被称为虚幻"。
这是什么经验? 好吧,例如,一个人可能会说,像是一个剥夺罐,他觉得鼻子已经转移到肚脐,然后决定,他并不需要一个鼻子或一个肚脐,飞入太空。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你只需要描述。 说明在这一领域是毫无意义的。
我35岁,并研究了八年,在精神分析之前,你去到剥夺罐。 在那一刻,我是自由于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一点。 有人会问:"有没有连接。" 我可以说,"是的,但是我了解到,从我所知我不需要"。
我学到了所有这些鬼话,你带人从学术界,也开始乱说。 我自己废话—保证我会忘记东西的教授,除真的宝贵和有趣的事情。
当我进入剥夺槽,主要的原则是,我使用的是这样的:"对上帝的份上,不predopredelyaet,不要寻找一个目标,只是让它发生"。 氯胺酮和迷幻药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慢慢放开控制自己的经验。
你知道,一些人躺在摄像机小时和尝试的经验和我一样的。 我知道这并最终写了前言,书中的"深深的自己",并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要在一个剥夺的坦克,不要读我的书,不听我的,只是去躺下。
我没有特派团。 特派团将使我荒谬的。 每一次我采取酸在一个剥夺的坦克,这不是像以前一样。 我认为我甚至不能开始描述。 我收到只有十分之一个百分的可能经验和描述它在书籍。
宇宙可以保护我们从我们倾向于预先判断。 当你走出你的身体并给予你完全的自由,你知道,有头脑的远大于人类。 然后你成为真正的谦卑。 然后你总是要回去吧,你想:"好吧,我在这里,在这个该死的身体,和我不一样聪明我是时候去他们。"
你有没有读凯瑟琳给珀斯? 她打开42肽,这能让大脑创造一个心情。 珀斯所说的:"一旦我们了解大脑的化学、精神分析学家将不需要"。 它们认为大脑是一个巨大的多元化工厂。
我们不这样做,当然,什么也没有一概而论,但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些物质的过量用药导致抑郁,其他的兴奋,等等。 那么,生活是不断通过调制化学的大脑。 就个人而言,我很久以前就放弃和停止试图计算出大脑是如何工作—因为他是如此复杂和广阔。 然而,如何复杂,我们仍然不知道。
主要任务的科学了解什么一个人,以及它是如何工作从观点的生物化学。 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我总是说,我的大脑是一个大宫殿,我只是一个小型啮齿动物,它窜来窜去的。 这是大脑的拥有我,不我的大脑。 大型计算机能充分模拟小,但它不能模拟本身,因为它将只是模仿。 没有意识,然后将会消失。
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创建一个超级计算机,将模拟的大脑。 我们的许多发现是完全随机的。 如果我们第一次打开的数学脑,但现在能够提前更进一步。
上帝知道用什么语言使用的大脑。 你可以显示的数字操作的大脑,用来分析神经冲动向上和向下aksonam,但什么是神经冲动吗? 我的理解是,它只是一种方式恢复健康状态的系统,该系统是在中间轴突。
神经冲动下降aksonam,只是清理一个中心点,以备他们下一个影响的时间。 它就像一个梦想。 睡眠状态下的人biocomputer综合和分析发生了什么事之外,抛出无用的记忆和各种有用的。 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型计算机,每次在你开始之前得到一个空空的存储器。 我们所有的时间做。
人们可以说,在剥夺罐,他觉得鼻子已经转移到肚脐,然后决定,他并不需要一个鼻子或一个肚脐,飞入太空
我们都在寻找的意义和解释。 这是天真的。 该说明原则上可以保护我们的恐惧的未知的;但是我喜欢的未知的,我是一个徒弟的惊喜。
玛格丽特*普雷斯顿(助理莉莉在科issledovatelskaya通信圣托马斯岛的维尔京群岛的)东西我被教导的。 有一次,我来到大学,她说,"莉莉博士,你不断地试图使事情发生。 这时候它不会的工作:你只坐着看的"。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如果我创造的事件,我最后感到厌倦。 但是,如果我可能只是放松和让事情发生了就像这样,无聊不是,我会得到的机会给其他人。 现在我可以负担得起,因为我不需要谋生。 然而,有些人能够获得和表现的该死的被动。
你可以成为一个管理员一无所知,然后人们会有事要告诉你。 我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网络,而且他教会了我在条款被动。 他说,"你必须学会像你疯了,你就可以提前那些生气真的。"
我说,"但是什么爱情?"的。 他说。 所有这些强大的感情...你可以表现得像你是他们的经历,但无动于衷,你将失去思考的能力清楚。
我学到的教训。 有一天,我非常愤怒,在他的哥哥和把他的罐碳化钙,它的分解,只是因为他嘲笑我这么多。 他嘲笑我非常的。 我抛出了一个罐子,她飞去,英寸从他的头上。 我僵住了,并认为,"哦我的上帝,我可以杀了他! 我永远不会得到愤怒。"
我曾经写过一章叫"哪里有军队?"。 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从传统。 儿童学习战争的历史,因此它们所有编程中前进。 如果你读了历史书籍,你会了解他们的所有关于战争,这只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拉丁类,我研究了战争的凯撒,随后与法国和开始审查战争的拿破仑,等等。 我们了解凯撒? 这是没有必要分裂高卢为三个部分。 我们已经了解了克娄巴特拉呢? 你可以杀了你自己的毒蛇咬伤的。 但是,如果你开始学习意大利的历史,并满足与达*芬奇或伽利略,它都将落空。 他们居住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这是华丽。 这是唯一的故事的一部分,可能是有趣的。
我们的目标的令人担心的是运动从ortonii以悔改过偏执狂。 Hortonia是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创建模拟选择采取。 悔改是当你离开这一切的背后,并能够更好什么样的高水平的精神发展。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第一次,你害怕死亡
当我第一次进入室内的剥夺后的酸,我惊慌失措。 我突然看到了一线的纪念碑的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不采取酸独自一人。"
一位研究人员忽视这项规则,并把它吃了与他自己的盒式录音机。 我不能什么更多的思考。 伟大的幸福,我因此强烈的是害怕。 我不知道,可能发生。 它是真实的火箭燃料!
我移动了宇宙中的进一步比以往任何时候。 如此偏执的火箭燃料的悔改. 之前我开始采取的剥夺的坦克,我怕水。 我已经帆船在海洋和被吓坏了的鲨鱼。 这是一个真正的长期恐惧症。 最后,我又进入室,并通过这个可怕的体验,只是害怕死亡。 现在水我不是害怕了。
参见:未消化课程的过去
你没有欲望
我从来没有告诉是什么。 我的心理医生是好的描述。 有一次我来找他,坐在椅子上说,"我只有一个新想法,但我不打算谈论这一点"。 他说,"哦,使你意识到,新的想法是相似的胚胎。 它可以杀死一个针,但如果胚胎已经成为一个胎儿或婴儿,他会感到仅有轻微的刺痛的感觉"。 你需要得到想法的长大了要做到之前你开始告诉它。
提交人:纳塔利娅保健专业人员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theoryandpractice.ru/posts/10610
莉莉进行的研究在感觉剥夺(浮)—闭胶囊与盐水,而这株的人从任何的感觉,并致幻用于实验。 出版了翻译摘录的一次采访约翰*莉莉,其中一个科学家会谈的有关规则的浮动的,根本不存在客观性和意义的恐惧。

当我16岁时,我正准备上大学,我写为校报的文章题为"现实"。 她确定我的人生道路和方向的想法、联系与学习活动和结构的大脑。
我去加州理工学院,开始研究生物科学的和对第一次参加了一个课程在神经解剖学的。 然后我去达特茅斯医学院,还有另外一个当然的,然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有研究大脑更进一步。 所以我了解了更多关于他比我可以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孩子,我去过天主教学校和学到了很多有关于粗糙的男孩和漂亮的女孩。 我爱上了玛格丽特*万斯,但没有告诉她任何东西,尽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关于性的,所以我幻想着我们如何交换尿。
我的父亲是一个机带,必须放在肚子上或一个软点,以及一个电动机,其带的振动。 有一次我站在这台机器,振动刺激的我性感的地区。 然后我突然感觉我的身体似乎分裂开来,而我的整个人被笼罩的喜悦。 这是真棒。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牧师,他说,"你手淫吧!"。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和回答说,"不"。 他称这是一个弥天大罪。 我离开教堂。 我想,"如果他们叫来自上帝的礼物一个弥天大罪,以狱与他们。 那不是我的上帝,他们只是试图控制人。"
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一个陷阱,让人。 我更喜欢条款"内部共识"和"外部的理智。" 国内清醒—这是你的生命你的内心。 这是非常私人的,你通常不会让任何人,因为将完全疯了,虽然我经常见面的人可以谈论它。
当你在一个剥夺的坦克,外部理智就会消失。 外头脑清楚是什么我们现在所做的,在对话过程中分享想法等等。 我不是在谈论你的内在理智和记者不会告诉她的。 然而,如果我们内部的神智部分相吻合,我们可以做朋友
我从来没有使用这个词"幻觉",因为它是高度desorientiert的。 它是一个人为的解释原则,因此,没有用的。 Richard Feynman,物理学家,陷入被剥夺罐20倍。 每次他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小时,然后送给我的邮件是他新书的物理学。
在标题页,费曼写道:"谢谢你的幻觉。" 我叫他,并说,"听着,迪克,你是不是像个科学家。 你应该介绍你有什么经验丰富的,并且不把它扔在垃圾桶标"的幻觉的"。 这是一个任期从精神病学领域,这扭曲了意义;没有什么从你的经验不能被称为虚幻"。
这是什么经验? 好吧,例如,一个人可能会说,像是一个剥夺罐,他觉得鼻子已经转移到肚脐,然后决定,他并不需要一个鼻子或一个肚脐,飞入太空。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你只需要描述。 说明在这一领域是毫无意义的。
我35岁,并研究了八年,在精神分析之前,你去到剥夺罐。 在那一刻,我是自由于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一点。 有人会问:"有没有连接。" 我可以说,"是的,但是我了解到,从我所知我不需要"。
我学到了所有这些鬼话,你带人从学术界,也开始乱说。 我自己废话—保证我会忘记东西的教授,除真的宝贵和有趣的事情。
当我进入剥夺槽,主要的原则是,我使用的是这样的:"对上帝的份上,不predopredelyaet,不要寻找一个目标,只是让它发生"。 氯胺酮和迷幻药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慢慢放开控制自己的经验。
你知道,一些人躺在摄像机小时和尝试的经验和我一样的。 我知道这并最终写了前言,书中的"深深的自己",并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要在一个剥夺的坦克,不要读我的书,不听我的,只是去躺下。
我没有特派团。 特派团将使我荒谬的。 每一次我采取酸在一个剥夺的坦克,这不是像以前一样。 我认为我甚至不能开始描述。 我收到只有十分之一个百分的可能经验和描述它在书籍。
宇宙可以保护我们从我们倾向于预先判断。 当你走出你的身体并给予你完全的自由,你知道,有头脑的远大于人类。 然后你成为真正的谦卑。 然后你总是要回去吧,你想:"好吧,我在这里,在这个该死的身体,和我不一样聪明我是时候去他们。"
你有没有读凯瑟琳给珀斯? 她打开42肽,这能让大脑创造一个心情。 珀斯所说的:"一旦我们了解大脑的化学、精神分析学家将不需要"。 它们认为大脑是一个巨大的多元化工厂。
我们不这样做,当然,什么也没有一概而论,但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些物质的过量用药导致抑郁,其他的兴奋,等等。 那么,生活是不断通过调制化学的大脑。 就个人而言,我很久以前就放弃和停止试图计算出大脑是如何工作—因为他是如此复杂和广阔。 然而,如何复杂,我们仍然不知道。
主要任务的科学了解什么一个人,以及它是如何工作从观点的生物化学。 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我总是说,我的大脑是一个大宫殿,我只是一个小型啮齿动物,它窜来窜去的。 这是大脑的拥有我,不我的大脑。 大型计算机能充分模拟小,但它不能模拟本身,因为它将只是模仿。 没有意识,然后将会消失。
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创建一个超级计算机,将模拟的大脑。 我们的许多发现是完全随机的。 如果我们第一次打开的数学脑,但现在能够提前更进一步。
上帝知道用什么语言使用的大脑。 你可以显示的数字操作的大脑,用来分析神经冲动向上和向下aksonam,但什么是神经冲动吗? 我的理解是,它只是一种方式恢复健康状态的系统,该系统是在中间轴突。
神经冲动下降aksonam,只是清理一个中心点,以备他们下一个影响的时间。 它就像一个梦想。 睡眠状态下的人biocomputer综合和分析发生了什么事之外,抛出无用的记忆和各种有用的。 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型计算机,每次在你开始之前得到一个空空的存储器。 我们所有的时间做。
人们可以说,在剥夺罐,他觉得鼻子已经转移到肚脐,然后决定,他并不需要一个鼻子或一个肚脐,飞入太空
我们都在寻找的意义和解释。 这是天真的。 该说明原则上可以保护我们的恐惧的未知的;但是我喜欢的未知的,我是一个徒弟的惊喜。
玛格丽特*普雷斯顿(助理莉莉在科issledovatelskaya通信圣托马斯岛的维尔京群岛的)东西我被教导的。 有一次,我来到大学,她说,"莉莉博士,你不断地试图使事情发生。 这时候它不会的工作:你只坐着看的"。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如果我创造的事件,我最后感到厌倦。 但是,如果我可能只是放松和让事情发生了就像这样,无聊不是,我会得到的机会给其他人。 现在我可以负担得起,因为我不需要谋生。 然而,有些人能够获得和表现的该死的被动。
你可以成为一个管理员一无所知,然后人们会有事要告诉你。 我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网络,而且他教会了我在条款被动。 他说,"你必须学会像你疯了,你就可以提前那些生气真的。"
我说,"但是什么爱情?"的。 他说。 所有这些强大的感情...你可以表现得像你是他们的经历,但无动于衷,你将失去思考的能力清楚。
我学到的教训。 有一天,我非常愤怒,在他的哥哥和把他的罐碳化钙,它的分解,只是因为他嘲笑我这么多。 他嘲笑我非常的。 我抛出了一个罐子,她飞去,英寸从他的头上。 我僵住了,并认为,"哦我的上帝,我可以杀了他! 我永远不会得到愤怒。"
我曾经写过一章叫"哪里有军队?"。 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从传统。 儿童学习战争的历史,因此它们所有编程中前进。 如果你读了历史书籍,你会了解他们的所有关于战争,这只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拉丁类,我研究了战争的凯撒,随后与法国和开始审查战争的拿破仑,等等。 我们了解凯撒? 这是没有必要分裂高卢为三个部分。 我们已经了解了克娄巴特拉呢? 你可以杀了你自己的毒蛇咬伤的。 但是,如果你开始学习意大利的历史,并满足与达*芬奇或伽利略,它都将落空。 他们居住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这是华丽。 这是唯一的故事的一部分,可能是有趣的。
我们的目标的令人担心的是运动从ortonii以悔改过偏执狂。 Hortonia是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创建模拟选择采取。 悔改是当你离开这一切的背后,并能够更好什么样的高水平的精神发展。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第一次,你害怕死亡
当我第一次进入室内的剥夺后的酸,我惊慌失措。 我突然看到了一线的纪念碑的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不采取酸独自一人。"
一位研究人员忽视这项规则,并把它吃了与他自己的盒式录音机。 我不能什么更多的思考。 伟大的幸福,我因此强烈的是害怕。 我不知道,可能发生。 它是真实的火箭燃料!
我移动了宇宙中的进一步比以往任何时候。 如此偏执的火箭燃料的悔改. 之前我开始采取的剥夺的坦克,我怕水。 我已经帆船在海洋和被吓坏了的鲨鱼。 这是一个真正的长期恐惧症。 最后,我又进入室,并通过这个可怕的体验,只是害怕死亡。 现在水我不是害怕了。
参见:未消化课程的过去
你没有欲望
我从来没有告诉是什么。 我的心理医生是好的描述。 有一次我来找他,坐在椅子上说,"我只有一个新想法,但我不打算谈论这一点"。 他说,"哦,使你意识到,新的想法是相似的胚胎。 它可以杀死一个针,但如果胚胎已经成为一个胎儿或婴儿,他会感到仅有轻微的刺痛的感觉"。 你需要得到想法的长大了要做到之前你开始告诉它。
提交人:纳塔利娅保健专业人员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theoryandpractice.ru/posts/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