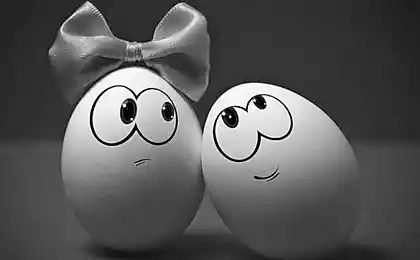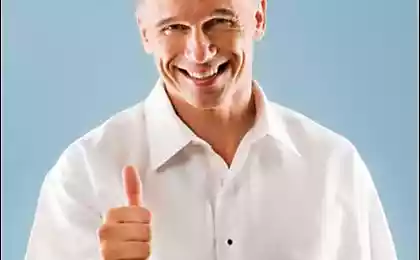981
家庭住宅№6
例如,他有一个最喜欢的杯子。圆上绘制的企鹅。企鹅的名字Paphnutius。
有一次我问:
- 为什么Pafnutii什么?
老公看着我惊讶地问道:
- 哦,怎么样?
我想了想,恍然大悟:事实上,仅此而已。
当天上午,丈夫得到厨柜Paphnutius说:
- 好吧,兄弟Paphnutius,一些咖啡吗?
到了晚上,他们Pafnuti喝茶,和我老公抱怨他对我说:
- 你看,Paphnutius,谁拥有消磨世纪?价格,兄弟,孤独,不pingvinihu溪。

更多在我们生活的保加利亚国家命名季娜伊达。保加利亚 - 不是在保加利亚土生土长的感觉,但在金属切割工具方面。
第一任丈夫叫她Snezana,因为他认为保加利亚人一定保加利亚的名字。然而,已经成为熟悉保加利亚的性格,他意识到她季娜伊达。
当你需要削减金属的东西,他拉她走出谷仓,说:
- 季娜伊达,不pobezumstvovat我们呢?
他们开始发疯。当nabezumstvuyutsya他抱着她进谷仓,把货架上,轻轻地说:
- 甜蜜的梦给你,吉娜。
我们住内阁公寓名为鲍里斯。这就是恭恭敬敬我的名字,是的。
只有当我们买了一套公寓,第一件事下令内阁。我们收集到的衣柜收藏家,他的名字是鲍里斯。
当然,这其实蒙上我的丈夫的耻辱,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
事实上,在我们家的家具休息(以及在我妈的房子,在他父母家,并在我们的许多朋友的家)丈夫收集自己。而衣柜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小菜一碟,但事有凑巧,在交付的一天,他出差,不得不回去仅仅两周之后。
我断然拒绝住在木板和箱子两周不可想象的数字之中,除了我就迫不及待地挂你的衣服挂在衣架上,所以等待我的丈夫没有和邀请存放垃圾。 ,当然,40次后悔过。

鲍里斯垃圾,去看望我,洗了个澡香水,古龙水品牌“针叶林”(或“俄罗斯场”或“青春美心” - 不知道)臭了整个房子。笔者从气味鲍里斯罗维奇逃脱在阳台上。
鲍里斯专心工作,慢慢地,有感觉,真的,有安排,有五个休息喝茶。很奇怪我为什么让他公司在餐桌上。而我只是不能喝浓茶,散发着古龙水。
专业鲍里斯是来自上帝的垃圾,收集柜,从上午9点到晚上11点。我在这段时间丈夫可以轻松地构建一个两层楼的房子,并在院子里一个澡堂。
我的东西,遗落在箱子不知道寒意衣架,因为所有2周丈夫到来之前,我播出了整个房间,特别是衣柜,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的味道。我很惭愧,连坐地铁,因为它在我看来,从我的全车护目镜这个杀手便宜的古龙水。
当我的丈夫赶到时,公寓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氛围。他高兴地跳到家具一个新的东西,高兴地哭了,“哦,更衣室!” - 站在旁边,扔开门。
约一分钟,他来到了自己从恶臭涌出他,然后问我:
- 嗯......那是什么?
- 它鲍里斯 - 我回答。
这是我们的柜子里而得名的方式,收集鲍里斯,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的教父(我们的教父,因此)。
现在我的丈夫,去任何重要的事件,咨询与他穿上柜:
- 鲍里斯,怎么样蓝色的衬衫吗?
或问:
- 不要借给领带,鲍里斯?
或挂在他的西装,说:
- 鲍里斯,让他为自己的荣誉。

更多的,我们有一个茶几斯捷潘。
好了,一切都很简单:我们买它的部分,但在家里原来的汇编指令写在英语和中国。
丈夫先问我读中国的版本,然后10分钟愤慨已婚一些文盲lohushka,即使中国人不知道,然后慷慨地允许读英文。
Lohushka妻子和英文,一般... ... khmmm但别的东西不知何故。
该手册写着:«第一步»。好吧,如果我的发音...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一个茶几成了斯捷潘。
当我在寻找一个打火机或一些杂志,我的丈夫说:
- 我不知道在哪里。问斯捷潘。
更多的,我们有微波炉加。我知道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是什么我不应该知道的。
因为当我的丈夫塞到她食物,轻轻的板块说:“暖,加......为我做的,宝宝......” - 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在甲状腺地区某处卡住。
相呼应的浪漫往事,显然。
更在我们的小屋有灶具,它总是打破了。 Nadia的丈夫叫她。
当我问为什么纳迪亚,他回答说:
- 是的,我有一个......太打破了所有的时间。
当他要在早上炒上一个鸡蛋,它总是问:
- 好吧,纳迪亚,今天是你成了,最后,我的?来吧,宝贝,给我一个机会,我的球。
更多的,我们有一个烟灰缸赖莎。丈夫认为,事实上,她赖莎,可见肉眼。
当我的丈夫想抽烟,他说:
- 赖莎,使一个很好的公司。
而当事情是分心,它把它在一个香烟,说:
- 赖莎,看守。
这种感染是病毒性的。
在我们的一些朋友有一台电视机菲尔(因为«飞利浦»)

冰箱和Anatolii(因为总是挤满像坎肩任何狗屎口袋沃瑟曼)。

其他懒在电视上露命名 - 在荣誉的邻居,这也是,据他们说,懒惰。
在第三个活洗衣机柳博芙·彼得罗夫娜。当他们带来了这款车,并解开自己的老祖母扔了她的手说:
- 美丽的柳博芙·奥尔洛娃!
连我母亲有茶匙命名伊索尔德。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伊索尔德。当我试图找出,妈妈看着我,好像我是疯了(虽然她总是看着我),我的丈夫气愤地说,一个愚蠢的问题没有听说过,任何傻瓜可以理解,为什么所谓的勺子。
有一次我问:
- 为什么Pafnutii什么?
老公看着我惊讶地问道:
- 哦,怎么样?
我想了想,恍然大悟:事实上,仅此而已。
当天上午,丈夫得到厨柜Paphnutius说:
- 好吧,兄弟Paphnutius,一些咖啡吗?
到了晚上,他们Pafnuti喝茶,和我老公抱怨他对我说:
- 你看,Paphnutius,谁拥有消磨世纪?价格,兄弟,孤独,不pingvinihu溪。

更多在我们生活的保加利亚国家命名季娜伊达。保加利亚 - 不是在保加利亚土生土长的感觉,但在金属切割工具方面。
第一任丈夫叫她Snezana,因为他认为保加利亚人一定保加利亚的名字。然而,已经成为熟悉保加利亚的性格,他意识到她季娜伊达。
当你需要削减金属的东西,他拉她走出谷仓,说:
- 季娜伊达,不pobezumstvovat我们呢?
他们开始发疯。当nabezumstvuyutsya他抱着她进谷仓,把货架上,轻轻地说:
- 甜蜜的梦给你,吉娜。
我们住内阁公寓名为鲍里斯。这就是恭恭敬敬我的名字,是的。
只有当我们买了一套公寓,第一件事下令内阁。我们收集到的衣柜收藏家,他的名字是鲍里斯。
当然,这其实蒙上我的丈夫的耻辱,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
事实上,在我们家的家具休息(以及在我妈的房子,在他父母家,并在我们的许多朋友的家)丈夫收集自己。而衣柜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小菜一碟,但事有凑巧,在交付的一天,他出差,不得不回去仅仅两周之后。
我断然拒绝住在木板和箱子两周不可想象的数字之中,除了我就迫不及待地挂你的衣服挂在衣架上,所以等待我的丈夫没有和邀请存放垃圾。 ,当然,40次后悔过。

鲍里斯垃圾,去看望我,洗了个澡香水,古龙水品牌“针叶林”(或“俄罗斯场”或“青春美心” - 不知道)臭了整个房子。笔者从气味鲍里斯罗维奇逃脱在阳台上。
鲍里斯专心工作,慢慢地,有感觉,真的,有安排,有五个休息喝茶。很奇怪我为什么让他公司在餐桌上。而我只是不能喝浓茶,散发着古龙水。
专业鲍里斯是来自上帝的垃圾,收集柜,从上午9点到晚上11点。我在这段时间丈夫可以轻松地构建一个两层楼的房子,并在院子里一个澡堂。
我的东西,遗落在箱子不知道寒意衣架,因为所有2周丈夫到来之前,我播出了整个房间,特别是衣柜,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的味道。我很惭愧,连坐地铁,因为它在我看来,从我的全车护目镜这个杀手便宜的古龙水。
当我的丈夫赶到时,公寓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氛围。他高兴地跳到家具一个新的东西,高兴地哭了,“哦,更衣室!” - 站在旁边,扔开门。
约一分钟,他来到了自己从恶臭涌出他,然后问我:
- 嗯......那是什么?
- 它鲍里斯 - 我回答。
这是我们的柜子里而得名的方式,收集鲍里斯,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的教父(我们的教父,因此)。
现在我的丈夫,去任何重要的事件,咨询与他穿上柜:
- 鲍里斯,怎么样蓝色的衬衫吗?
或问:
- 不要借给领带,鲍里斯?
或挂在他的西装,说:
- 鲍里斯,让他为自己的荣誉。

更多的,我们有一个茶几斯捷潘。
好了,一切都很简单:我们买它的部分,但在家里原来的汇编指令写在英语和中国。
丈夫先问我读中国的版本,然后10分钟愤慨已婚一些文盲lohushka,即使中国人不知道,然后慷慨地允许读英文。
Lohushka妻子和英文,一般... ... khmmm但别的东西不知何故。
该手册写着:«第一步»。好吧,如果我的发音...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一个茶几成了斯捷潘。
当我在寻找一个打火机或一些杂志,我的丈夫说:
- 我不知道在哪里。问斯捷潘。
更多的,我们有微波炉加。我知道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是什么我不应该知道的。
因为当我的丈夫塞到她食物,轻轻的板块说:“暖,加......为我做的,宝宝......” - 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在甲状腺地区某处卡住。
相呼应的浪漫往事,显然。
更在我们的小屋有灶具,它总是打破了。 Nadia的丈夫叫她。
当我问为什么纳迪亚,他回答说:
- 是的,我有一个......太打破了所有的时间。
当他要在早上炒上一个鸡蛋,它总是问:
- 好吧,纳迪亚,今天是你成了,最后,我的?来吧,宝贝,给我一个机会,我的球。
更多的,我们有一个烟灰缸赖莎。丈夫认为,事实上,她赖莎,可见肉眼。
当我的丈夫想抽烟,他说:
- 赖莎,使一个很好的公司。
而当事情是分心,它把它在一个香烟,说:
- 赖莎,看守。
这种感染是病毒性的。
在我们的一些朋友有一台电视机菲尔(因为«飞利浦»)

冰箱和Anatolii(因为总是挤满像坎肩任何狗屎口袋沃瑟曼)。

其他懒在电视上露命名 - 在荣誉的邻居,这也是,据他们说,懒惰。
在第三个活洗衣机柳博芙·彼得罗夫娜。当他们带来了这款车,并解开自己的老祖母扔了她的手说:
- 美丽的柳博芙·奥尔洛娃!
连我母亲有茶匙命名伊索尔德。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伊索尔德。当我试图找出,妈妈看着我,好像我是疯了(虽然她总是看着我),我的丈夫气愤地说,一个愚蠢的问题没有听说过,任何傻瓜可以理解,为什么所谓的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