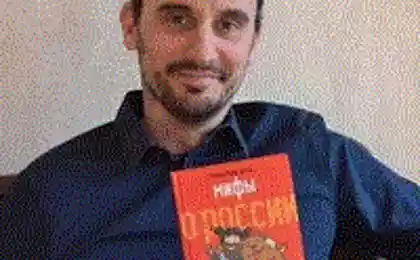923
住复仇后
我小的时候,我想杀了我妹妹。
她住一个有趣的和不明确的,来到学校,在晚上朗读优美的诗歌,与朋友窃窃私语的手机上,并没有让我即使进入她的办公桌上肘部的一角。
妈妈严格地说:“大傻,不要怕麻烦玛丽学习” - 并拉起我的玩具
。 在7年的差异是不可抗拒的深渊。她的生活似乎闪闪发光,在阳光山顶 - 雪和难以捉摸,因为特别有吸引力。
玛莎冷冷地盯着我从时代的高度,偶尔会砍我的好奇,试图爬进她的记录或书籍分类“SCAT”。
我是可怕的,布线,示意我禁止磁铁。我一直在下降:在膝盖上的碎玻璃,只是一个篱笆。填缝我的脸上看不到养老金领取驾驶者 - 我涂狗屎猫玻璃机器,和一个特别讨厌的老男人谁打电话玛莎衣衫褴褛的羊,刮伤对汽车svezheotlakirovannoy漂亮的字避孕套,甚至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所学校是不是那样雄壮描绘在我的梦想:我觉得很难听老师的话几个小时,观察总不动。此外,在办公桌上的邻居是相同的焦躁不安,不可抑制的男孩,其中有共享的势力范围,以及迫切解决的问题 - “XY XY”
当我摔断了胳膊,捏手门衣柜赌博,“猎人与猎物”,对“胡”已积极朝我解决了问题,伊凡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助手在我的滑稽动作。班主任悄悄在学校我的母亲叹了口气恨我们俩,并要求严格每月两次,并承诺“影响力”。
一旦我们在四年级Vanka打乱了年度控制(以及提前一周课),溢出汞的消费阶层 - 学校被邀请到他的父亲。
他回到了阴沉,让我坚定地说:“你去学习和生活中的一所寄宿学校,只是不希望像其他人一样”闭门厨房妈妈的东西快速,充满激情地告诉了他,然后他听见噼里啪啦和振铃像一个贝壳撞上一堆汤匙,妈妈哭了。然后又和另一个。
君坐妾之每一个声音,然后父亲跳下厨房,砰的一声关上门。妈妈坐在地板上,膝盖在他卷起,并压面对茶巾,色有红色斑点。
- 妈妈,对不起 - 我轻声说。
- 没有,宝宝......来找他 - 她转过身去,在地上说
。 我走进主卧室,父亲改变了他的衣服,拉着背带西裤。
- 我恨你 - 我轻声说爸爸回来了。
父亲打了我的脸一转,使我的灯体印放回柜子里。他从来没有打我,而这种打击吹我的宇宙。
躺在地板上,我固执地重复:“我恨,恨......” - 然后跳起来,跑到她的房间,我浑身发抖,用气得发抖。玛莎什么都明白了没有的话,她就坐在我的床上,抱着我抱住了她。她是我的知己,在不满的海洋岛。我不觉得反感和疏远,而是迷茫......我什么欲望都没有摆脱我的妹妹。儿童重熔仇恨到爱情。
三年后,他的父亲的车失去了控制在雾中撞上了广告牌的支持,各地的铁柱扭曲,变成了一堆从扭曲的金属垃圾残留在内部。
在车上,除了他的父亲,我开着我的母亲,谁曾那天飞生病的祖母,但该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取消。
我的祖母生存了他的女儿整整三分钟,然后我说玛莎。我们俩了。玛莎取代了我的母亲。而早前想过她的谋杀,有时有益抛出内存让我紧张去耻辱猩红色污渍。
我拉出来的时候睡眠的手机响了。
“留在嘴唇上的骨灰,在我眼里,风的气息......” - 调定为Mashkin直线。
在早上4 - 余瞥手表,这是不从手取出的发光表盘,即使在夜间。这是严重的,彻底的人的姐姐并没有获得在早上我的电话号码困了,在一个合适的宿醉和愿望肯定谈脂肪。
- 是 - 我嘶哑地说
。 - 大傻 - 姐妹的声音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 - 我需要你。然后点击断开和操作信息“用户不在服务»。
11位,打破了指甲。我姐姐没有回答。再次,更多...烂。我混蛋从床上跳下来,摆脱睡眠的残余。牛仔裤,T恤,夹克,皮质柔软的背包,我习惯性地抛出用品:服装,设备,水,最喜欢的书(上飞机就必须睡觉,然后指望他们)。哦,是的,我需要钱。
票务服务乐呵呵地说:在两小时内下一个航班。确定。
机场充满了人类的嗡嗡声和喧嚣。在空气中,似乎有形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是否合理?几乎没有。
我还在出发前半小时。工作电话是完美的,有缺席许可,其次是解释性的回报。在头纺纱选项,会发生什么?
玛莎结婚了。这似乎很愉快,现在7岁。她的丈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我们只在婚礼上,这是我第一次会议的日期后,立即就越过了他。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学生MAI的,我的生活被动摇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和巨大的zapoloshnyh爱。现在,我甚至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 Mashkin丈夫,棕色或黑色的头发,她只知道一点,可以提取简短的电话交谈与他的妹妹。
呼吁生日和圣诞节,标准问候和陈腐的短语。她结婚后,我们的关系没有破裂,却成了其上一年几次被送往亲吻和压硬币的话细绳:“你是如何,猫咪”,“如果我能来,小姐”而 - 而原因不明的叫早服务
。
家乡遇到了小雨和雾多见于初秋。
我不觉得怀旧,而这一切其他狗屎蓝色的,叫他童年的忧伤。世界上只有一个妹妹。和伊万,我默默惨遭下降,舞会之后。
操作员轻轻地,几乎是情欲,并要求对方一会儿再打过去,希望我的理解。细胞玛莎是残疾,家里的电话沉默了。她的公寓门不高兴 - 燃烧的红眼报警。我们卖我们的父母的房间,当我的妹妹结婚 - 我需要住房在莫斯科;现在他们住的是豪华的砖砌建筑,举重,看守等..
酒店不想去,我不喜欢所有的这些操作,注册和演示文件。
我记得伊万的家庭电话。他被牢牢地嵌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我试图忘记。而他,这个城市,这个电话,他的嘴唇在我身上的舞会......
如果他移动,然后 - 汗。灼灼酒店,无特色的房间,可怜的表从烟头烧伤和污渍在做爱褪色的床单。
万尼亚的妹妹接过了电话。院长马上认出我的声音。而在另一“哦,是什么让”她忙着呼来唤去我自己的细胞,并告诉他随时调用。
在我的潜问题(无论是方便)先见之明地咯咯地笑 - 未婚
伊万说一次,急剧突然 - Zheglov。
是的,这是这样一个有趣的谈姓是我的同学。他睡着了,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员工ugolovki。出于某种原因,我已经麻木了,但我的沉默,只能我的老板,让眼睛的员工称为APC。
- 沙发 - 我怯生生地说Vankina学校的绰号。他看起来像一个沙发 - 一个健康的角度
- 大沙河。 - 声音没有任何表情,这(是诚实的),我预计
。 - 我无处可留
。 - 你在哪里?等一下,我会。
他的九个 -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Vanka - 飞22分钟。门开了,我一屁股坐在前座,在温暖的房间。
我总是呼来喝我们讨厌的,和伊万总是覆盖我,我的骑士和盾牌。而现在,在他的车,我感受到了同样的方式在20年前,在导演的办公室,这需要怎样的老师的门上厕所有一个题词排水的解释。
掩盖我回不倒翁buhtel可悲的是,这不是责备,我们想抹去的,但是乳胶漆耐抓住和溶剂找不到......嗯,这是Mashkin指甲油。
- 什么是风? - 他的问题都是干的,务实的。狼的眼睛,瞳孔收缩,扭曲和转动困了警察。我的专业活动的性质不断面临着内政部,我觉得这个观点了一千。
- 叫夜玛莎。我问来。而现在接了电话,门报警。
- 也许它去度假 - 建议伊万。
- 她喜欢去春来塞浦路斯,喜欢只有一个特定的酒店。玛莎保守的 - 不是我滚草
。 - 走开了一夜
? - 不要让我笑了,我妹妹没有喝任何东西,但矿泉水和无法忍受空pyanok
。 - 明白了。好了,我们走吧。
他带我去一个不起眼的平房在城市的郊区,有灰尘的家具和窗户的窗帘拉紧。
- 而在良好的办公付出...或爱巢是嫁妆的一部分吗? - 我不能从螺栓抵抗
。 - 我没有结婚 - 伊万平静地回答道 - 而不是我的房子,人的使命离开了钥匙无人看管。你来自路面的休息,我会打电话给一些人。
背包飞到了沉重的椅子上,落在我的衬衫和牛仔裤的顶部。在BUFF,我过去游行到Vanka卫生间,他甚至没有导致眉毛,翻翻我。
灌洗追凑到困了,他的头被清除。伊万,加息,打电话给派出所和医院。
房间里已经不存在,但厨房绘制的现煮咖啡,我是乖乖地像老鼠在笛声的气味。
- 这是第一个城市 - 伊凡说,喝着黑色的液体,这是他煮,而不是咖啡,并没有看在紧紧裹住我的臀部的毛巾明显的兴趣,几乎涵盖她的胯部。
- 脑震荡,肋骨骨折,脾脏破裂。显然,他从高处摔下......去?
- 顺便说一句,你的工作在哪里,想要? - 在车上,我问一个同学
。 - 是的
。
我不能忍受的医院。死亡和痛苦,不育或没有墙壁,护士的气味,飞奔到走廊的业务视图。 BRRR。
值班医生抓住了我们ordinatorskoj冷淡地说:
- 对患者进行操作。你,其实,任何人吗?
- 姐姐,其实。这是有足够的理由来访问?
- 五分钟 - 杀进由医生。
玛莎是一个昂贵的私人房间有地毯和一台电视机。这仅仅是一个电视看它是什么。保罗面的合并成一个巨大的蓝色肿胀,咽喉藏在绷带,低于任何东西 - 在石膏紧身胸衣。医疗器械在铁鬼火站在病床旁边一个安慰的表情 - 一切都会好起来
。 - 玛莎 - 我轻声说, - 玛莎......是如何发生的?
这闷热的室内憋闷,有可能只想到衰老和死亡,夜船,老年痴呆症和堕胎作为从梯子上坠落的结果。
这些想法通常导致奸诈的眼泪,但我的眼睛干燥。我讨厌哭了。
- Krysko - 声音是无形的姐妹快要死了 - 我很害怕。我以为我会死没有再见对你说。
- 杜拉。玛莎,你塞着的老傻瓜 - 我的声音在颤抖背信弃义。 - 你敢离开我。
- 不要叫奥列格没有事实证明 - 簌簌玛莎。 - 你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大概叫Zheglova?
我姐姐认识我。即使经过十五年的住在一起,她知道我的骨头。
- 别担心 - 我平静地回答。 - 我有一个地方居住和睡眠。我不明白 - 奥列格?发生了什么事?你被困在一个车祸?
- 他是疯了。
我疯狂地看着肿胀的嘴唇姐姐,试图找到她的话另有深意。
- 会议rodstvennnyh拥抱结束了 - 我密切合作,以一名护士,一位年长的阿姨眼睛干涩和鲨鱼牙齿马的输出
。
在大厅,伊万看着我诧异。
- 这是可怕的殴打。据被打。
- 奇怪 - 说Zheglov - 值班医生说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梯子下跌。雅各布斯对旧事物的夹层了,我想扔不必要的。
- 玛莎是恐高症。她没洗的窗口,它总是让我。现在也许是一个特殊的服务。她是阶梯的第二个梯级 - 珠穆朗玛峰
。 我突然觉得血腥的味道,他的牙齿:她的舌头?
打父亲和衣柜的门,欢迎我去爱抚脊椎。
- 婊子 - 我发出嘘声。 - 他是打玛莎
。 - 丈夫
- 不,该死的,邻居
。 我进行了流和扭曲的猩红疯狂的愤怒从烧伤皮肤在他的后脑勺和他的牙齿疼痛难忍。
- 易 - 有序Zheglov。 - 没有歇斯底里。不能错?
- 号
- 澄清不拉。现在我们回到小屋。我会去工作,回来在晚上。丈夫会发现所有提出正确的问题。
山寨没有变化:同样尘土飞扬的窗帘,菜,在一个不锈钢水槽,寂静的角落长满青苔
。 为了不从角落里跑角落如虎,我开始清洗。 Draila,吸尘器,扔在洗床单。有时,他期待与希望的电话 - 他沉默了。
伊万来了将近九年。静静地扔在厨房的桌子上的钥匙,说:
- Tuhlyak
。 - ?
- 这是在塞浦路斯。立马五天前,被登记在机场,我坐上飞机。酒店说,顾客是在房间里,但此刻没有。手机断开。他的秘书说,订购门票两个,而是一票科捷利尼科夫Anatolievna玛利亚出现了无人认领。
- 它不能
! - 事实是,孩子
。 他打电话给我一次炼狱般的婴儿断头台parshivkoy,zasranka - 永不孩子
- 入住 - 我问悲哀。并认为这波动。
- 第
锁点击了门,我被单独留在这个城市他的童年。单独与他的记忆。
早上我开车去了第一个市级之一。值班医生已经是另外一个老人挑剔puzanchik。
- 危机已经过去,孩子。你姐姐还是会跳舞你的婚礼。
然而,在病房里,他给了我一切,都与同样的礼遇是不是空的:“明天来»
。
我去了Mashkina回家,我不知道为什么。
奇怪的是,眼睛没有光报警。犹豫了一阵后,我放弃了她的手,已经延伸到了门铃。
到了晚上,我再次去了马施克。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个城市,但坐在旁边的床上,听着姐妹cheeps一些有趣的工具,它借鉴了监控曲线。
玛莎尾流很少茫然地看着我,又睡着了。
两天后,我几乎相撞与她的丈夫在门口。奇怪的是 - 我马上认出了他。从奥列格令人窒息穿着昂贵的香水,并通过“波士”陈旧。仿佛他试图扼杀科隆酒的气味,淋在身体大量。
奥列格直奔主任医师的第一个办事处,我悄悄地走在后面。然后他到玛丽的房子。
欲言又止,我愣在了玻璃门。然后,他转身离开,以免脸,鼻子鼻子。这并不是说他认识我,但仍...
事实 围绕建筑物的角落不得不站在四十五分钟后,我看到奥列格的高大的身影。他出去到了门口,看着隐约在在室,那里躺着玛莎的二楼窗户,掏出车钥匙。黑色吉普插进轻声回应主机的电话。 Interesnenko。他在哪里画,一个充满爱的丈夫吗?科捷利尼科夫突然拉升,消失在门的后面。
伊万没有打电话,我mayalas无所事事,并前往医院。两天后,马施克是好多了,我想听到的答案,有些问题。例如,她住所有的这七年中,因为我的离去?
她沉默着,看向别处,但我的沉默她的公爵。
- 是不是太晚了真相?
- 比生命更好地后迟到
。
奥列格在四年前竞选与业务合作伙伴的麻烦。它飞到了地狱。他变得常常放弃,早上回家,提高了嗓门。然后 - 而不仅仅是声音。这是第一次我丈夫打玛莎的时候,她怀孕了。孩子是值得欢迎的,但它是不可能怀孕的姐姐很不高兴,这是治疗,是花费在医生和药品的财富。
奥列格回家的早晨,没有任何警告,将不会在家里睡觉。当玛莎问他在哪里,奥列格拉着妻子的手粗糙的脸,他的后脑勺撞到墙上。她失去了知觉 - 当我感悟到躺在血泊中。这是其一。
从医院回来后,奥列格的妻子来到他的感觉。龙恳求他的膝盖宽恕,停止饮用。但是这已经足够时间并不长 - 在一些一年半的女孩出现了,傲慢地叫你家的电话,并要求奥列格成为常态闻到奇怪的香水在枕头上,口红的衬衫
。
资料来源:
她住一个有趣的和不明确的,来到学校,在晚上朗读优美的诗歌,与朋友窃窃私语的手机上,并没有让我即使进入她的办公桌上肘部的一角。
妈妈严格地说:“大傻,不要怕麻烦玛丽学习” - 并拉起我的玩具
。 在7年的差异是不可抗拒的深渊。她的生活似乎闪闪发光,在阳光山顶 - 雪和难以捉摸,因为特别有吸引力。
玛莎冷冷地盯着我从时代的高度,偶尔会砍我的好奇,试图爬进她的记录或书籍分类“SCAT”。
我是可怕的,布线,示意我禁止磁铁。我一直在下降:在膝盖上的碎玻璃,只是一个篱笆。填缝我的脸上看不到养老金领取驾驶者 - 我涂狗屎猫玻璃机器,和一个特别讨厌的老男人谁打电话玛莎衣衫褴褛的羊,刮伤对汽车svezheotlakirovannoy漂亮的字避孕套,甚至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所学校是不是那样雄壮描绘在我的梦想:我觉得很难听老师的话几个小时,观察总不动。此外,在办公桌上的邻居是相同的焦躁不安,不可抑制的男孩,其中有共享的势力范围,以及迫切解决的问题 - “XY XY”
当我摔断了胳膊,捏手门衣柜赌博,“猎人与猎物”,对“胡”已积极朝我解决了问题,伊凡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助手在我的滑稽动作。班主任悄悄在学校我的母亲叹了口气恨我们俩,并要求严格每月两次,并承诺“影响力”。
一旦我们在四年级Vanka打乱了年度控制(以及提前一周课),溢出汞的消费阶层 - 学校被邀请到他的父亲。
他回到了阴沉,让我坚定地说:“你去学习和生活中的一所寄宿学校,只是不希望像其他人一样”闭门厨房妈妈的东西快速,充满激情地告诉了他,然后他听见噼里啪啦和振铃像一个贝壳撞上一堆汤匙,妈妈哭了。然后又和另一个。
君坐妾之每一个声音,然后父亲跳下厨房,砰的一声关上门。妈妈坐在地板上,膝盖在他卷起,并压面对茶巾,色有红色斑点。
- 妈妈,对不起 - 我轻声说。
- 没有,宝宝......来找他 - 她转过身去,在地上说
。 我走进主卧室,父亲改变了他的衣服,拉着背带西裤。
- 我恨你 - 我轻声说爸爸回来了。
父亲打了我的脸一转,使我的灯体印放回柜子里。他从来没有打我,而这种打击吹我的宇宙。
躺在地板上,我固执地重复:“我恨,恨......” - 然后跳起来,跑到她的房间,我浑身发抖,用气得发抖。玛莎什么都明白了没有的话,她就坐在我的床上,抱着我抱住了她。她是我的知己,在不满的海洋岛。我不觉得反感和疏远,而是迷茫......我什么欲望都没有摆脱我的妹妹。儿童重熔仇恨到爱情。
三年后,他的父亲的车失去了控制在雾中撞上了广告牌的支持,各地的铁柱扭曲,变成了一堆从扭曲的金属垃圾残留在内部。
在车上,除了他的父亲,我开着我的母亲,谁曾那天飞生病的祖母,但该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取消。
我的祖母生存了他的女儿整整三分钟,然后我说玛莎。我们俩了。玛莎取代了我的母亲。而早前想过她的谋杀,有时有益抛出内存让我紧张去耻辱猩红色污渍。
我拉出来的时候睡眠的手机响了。
“留在嘴唇上的骨灰,在我眼里,风的气息......” - 调定为Mashkin直线。
在早上4 - 余瞥手表,这是不从手取出的发光表盘,即使在夜间。这是严重的,彻底的人的姐姐并没有获得在早上我的电话号码困了,在一个合适的宿醉和愿望肯定谈脂肪。
- 是 - 我嘶哑地说
。 - 大傻 - 姐妹的声音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 - 我需要你。然后点击断开和操作信息“用户不在服务»。
11位,打破了指甲。我姐姐没有回答。再次,更多...烂。我混蛋从床上跳下来,摆脱睡眠的残余。牛仔裤,T恤,夹克,皮质柔软的背包,我习惯性地抛出用品:服装,设备,水,最喜欢的书(上飞机就必须睡觉,然后指望他们)。哦,是的,我需要钱。
票务服务乐呵呵地说:在两小时内下一个航班。确定。
机场充满了人类的嗡嗡声和喧嚣。在空气中,似乎有形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是否合理?几乎没有。
我还在出发前半小时。工作电话是完美的,有缺席许可,其次是解释性的回报。在头纺纱选项,会发生什么?
玛莎结婚了。这似乎很愉快,现在7岁。她的丈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我们只在婚礼上,这是我第一次会议的日期后,立即就越过了他。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学生MAI的,我的生活被动摇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和巨大的zapoloshnyh爱。现在,我甚至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 Mashkin丈夫,棕色或黑色的头发,她只知道一点,可以提取简短的电话交谈与他的妹妹。
呼吁生日和圣诞节,标准问候和陈腐的短语。她结婚后,我们的关系没有破裂,却成了其上一年几次被送往亲吻和压硬币的话细绳:“你是如何,猫咪”,“如果我能来,小姐”而 - 而原因不明的叫早服务
。
家乡遇到了小雨和雾多见于初秋。
我不觉得怀旧,而这一切其他狗屎蓝色的,叫他童年的忧伤。世界上只有一个妹妹。和伊万,我默默惨遭下降,舞会之后。
操作员轻轻地,几乎是情欲,并要求对方一会儿再打过去,希望我的理解。细胞玛莎是残疾,家里的电话沉默了。她的公寓门不高兴 - 燃烧的红眼报警。我们卖我们的父母的房间,当我的妹妹结婚 - 我需要住房在莫斯科;现在他们住的是豪华的砖砌建筑,举重,看守等..
酒店不想去,我不喜欢所有的这些操作,注册和演示文件。
我记得伊万的家庭电话。他被牢牢地嵌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我试图忘记。而他,这个城市,这个电话,他的嘴唇在我身上的舞会......
如果他移动,然后 - 汗。灼灼酒店,无特色的房间,可怜的表从烟头烧伤和污渍在做爱褪色的床单。
万尼亚的妹妹接过了电话。院长马上认出我的声音。而在另一“哦,是什么让”她忙着呼来唤去我自己的细胞,并告诉他随时调用。
在我的潜问题(无论是方便)先见之明地咯咯地笑 - 未婚
伊万说一次,急剧突然 - Zheglov。
是的,这是这样一个有趣的谈姓是我的同学。他睡着了,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员工ugolovki。出于某种原因,我已经麻木了,但我的沉默,只能我的老板,让眼睛的员工称为APC。
- 沙发 - 我怯生生地说Vankina学校的绰号。他看起来像一个沙发 - 一个健康的角度
- 大沙河。 - 声音没有任何表情,这(是诚实的),我预计
。 - 我无处可留
。 - 你在哪里?等一下,我会。
他的九个 -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Vanka - 飞22分钟。门开了,我一屁股坐在前座,在温暖的房间。
我总是呼来喝我们讨厌的,和伊万总是覆盖我,我的骑士和盾牌。而现在,在他的车,我感受到了同样的方式在20年前,在导演的办公室,这需要怎样的老师的门上厕所有一个题词排水的解释。
掩盖我回不倒翁buhtel可悲的是,这不是责备,我们想抹去的,但是乳胶漆耐抓住和溶剂找不到......嗯,这是Mashkin指甲油。
- 什么是风? - 他的问题都是干的,务实的。狼的眼睛,瞳孔收缩,扭曲和转动困了警察。我的专业活动的性质不断面临着内政部,我觉得这个观点了一千。
- 叫夜玛莎。我问来。而现在接了电话,门报警。
- 也许它去度假 - 建议伊万。
- 她喜欢去春来塞浦路斯,喜欢只有一个特定的酒店。玛莎保守的 - 不是我滚草
。 - 走开了一夜
? - 不要让我笑了,我妹妹没有喝任何东西,但矿泉水和无法忍受空pyanok
。 - 明白了。好了,我们走吧。
他带我去一个不起眼的平房在城市的郊区,有灰尘的家具和窗户的窗帘拉紧。
- 而在良好的办公付出...或爱巢是嫁妆的一部分吗? - 我不能从螺栓抵抗
。 - 我没有结婚 - 伊万平静地回答道 - 而不是我的房子,人的使命离开了钥匙无人看管。你来自路面的休息,我会打电话给一些人。
背包飞到了沉重的椅子上,落在我的衬衫和牛仔裤的顶部。在BUFF,我过去游行到Vanka卫生间,他甚至没有导致眉毛,翻翻我。
灌洗追凑到困了,他的头被清除。伊万,加息,打电话给派出所和医院。
房间里已经不存在,但厨房绘制的现煮咖啡,我是乖乖地像老鼠在笛声的气味。
- 这是第一个城市 - 伊凡说,喝着黑色的液体,这是他煮,而不是咖啡,并没有看在紧紧裹住我的臀部的毛巾明显的兴趣,几乎涵盖她的胯部。
- 脑震荡,肋骨骨折,脾脏破裂。显然,他从高处摔下......去?
- 顺便说一句,你的工作在哪里,想要? - 在车上,我问一个同学
。 - 是的
。
我不能忍受的医院。死亡和痛苦,不育或没有墙壁,护士的气味,飞奔到走廊的业务视图。 BRRR。
值班医生抓住了我们ordinatorskoj冷淡地说:
- 对患者进行操作。你,其实,任何人吗?
- 姐姐,其实。这是有足够的理由来访问?
- 五分钟 - 杀进由医生。
玛莎是一个昂贵的私人房间有地毯和一台电视机。这仅仅是一个电视看它是什么。保罗面的合并成一个巨大的蓝色肿胀,咽喉藏在绷带,低于任何东西 - 在石膏紧身胸衣。医疗器械在铁鬼火站在病床旁边一个安慰的表情 - 一切都会好起来
。 - 玛莎 - 我轻声说, - 玛莎......是如何发生的?
这闷热的室内憋闷,有可能只想到衰老和死亡,夜船,老年痴呆症和堕胎作为从梯子上坠落的结果。
这些想法通常导致奸诈的眼泪,但我的眼睛干燥。我讨厌哭了。
- Krysko - 声音是无形的姐妹快要死了 - 我很害怕。我以为我会死没有再见对你说。
- 杜拉。玛莎,你塞着的老傻瓜 - 我的声音在颤抖背信弃义。 - 你敢离开我。
- 不要叫奥列格没有事实证明 - 簌簌玛莎。 - 你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大概叫Zheglova?
我姐姐认识我。即使经过十五年的住在一起,她知道我的骨头。
- 别担心 - 我平静地回答。 - 我有一个地方居住和睡眠。我不明白 - 奥列格?发生了什么事?你被困在一个车祸?
- 他是疯了。
我疯狂地看着肿胀的嘴唇姐姐,试图找到她的话另有深意。
- 会议rodstvennnyh拥抱结束了 - 我密切合作,以一名护士,一位年长的阿姨眼睛干涩和鲨鱼牙齿马的输出
。
在大厅,伊万看着我诧异。
- 这是可怕的殴打。据被打。
- 奇怪 - 说Zheglov - 值班医生说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梯子下跌。雅各布斯对旧事物的夹层了,我想扔不必要的。
- 玛莎是恐高症。她没洗的窗口,它总是让我。现在也许是一个特殊的服务。她是阶梯的第二个梯级 - 珠穆朗玛峰
。 我突然觉得血腥的味道,他的牙齿:她的舌头?
打父亲和衣柜的门,欢迎我去爱抚脊椎。
- 婊子 - 我发出嘘声。 - 他是打玛莎
。 - 丈夫
- 不,该死的,邻居
。 我进行了流和扭曲的猩红疯狂的愤怒从烧伤皮肤在他的后脑勺和他的牙齿疼痛难忍。
- 易 - 有序Zheglov。 - 没有歇斯底里。不能错?
- 号
- 澄清不拉。现在我们回到小屋。我会去工作,回来在晚上。丈夫会发现所有提出正确的问题。
山寨没有变化:同样尘土飞扬的窗帘,菜,在一个不锈钢水槽,寂静的角落长满青苔
。 为了不从角落里跑角落如虎,我开始清洗。 Draila,吸尘器,扔在洗床单。有时,他期待与希望的电话 - 他沉默了。
伊万来了将近九年。静静地扔在厨房的桌子上的钥匙,说:
- Tuhlyak
。 - ?
- 这是在塞浦路斯。立马五天前,被登记在机场,我坐上飞机。酒店说,顾客是在房间里,但此刻没有。手机断开。他的秘书说,订购门票两个,而是一票科捷利尼科夫Anatolievna玛利亚出现了无人认领。
- 它不能
! - 事实是,孩子
。 他打电话给我一次炼狱般的婴儿断头台parshivkoy,zasranka - 永不孩子
- 入住 - 我问悲哀。并认为这波动。
- 第
锁点击了门,我被单独留在这个城市他的童年。单独与他的记忆。
早上我开车去了第一个市级之一。值班医生已经是另外一个老人挑剔puzanchik。
- 危机已经过去,孩子。你姐姐还是会跳舞你的婚礼。
然而,在病房里,他给了我一切,都与同样的礼遇是不是空的:“明天来»
。
我去了Mashkina回家,我不知道为什么。
奇怪的是,眼睛没有光报警。犹豫了一阵后,我放弃了她的手,已经延伸到了门铃。
到了晚上,我再次去了马施克。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个城市,但坐在旁边的床上,听着姐妹cheeps一些有趣的工具,它借鉴了监控曲线。
玛莎尾流很少茫然地看着我,又睡着了。
两天后,我几乎相撞与她的丈夫在门口。奇怪的是 - 我马上认出了他。从奥列格令人窒息穿着昂贵的香水,并通过“波士”陈旧。仿佛他试图扼杀科隆酒的气味,淋在身体大量。
奥列格直奔主任医师的第一个办事处,我悄悄地走在后面。然后他到玛丽的房子。
欲言又止,我愣在了玻璃门。然后,他转身离开,以免脸,鼻子鼻子。这并不是说他认识我,但仍...
事实 围绕建筑物的角落不得不站在四十五分钟后,我看到奥列格的高大的身影。他出去到了门口,看着隐约在在室,那里躺着玛莎的二楼窗户,掏出车钥匙。黑色吉普插进轻声回应主机的电话。 Interesnenko。他在哪里画,一个充满爱的丈夫吗?科捷利尼科夫突然拉升,消失在门的后面。
伊万没有打电话,我mayalas无所事事,并前往医院。两天后,马施克是好多了,我想听到的答案,有些问题。例如,她住所有的这七年中,因为我的离去?
她沉默着,看向别处,但我的沉默她的公爵。
- 是不是太晚了真相?
- 比生命更好地后迟到
。
奥列格在四年前竞选与业务合作伙伴的麻烦。它飞到了地狱。他变得常常放弃,早上回家,提高了嗓门。然后 - 而不仅仅是声音。这是第一次我丈夫打玛莎的时候,她怀孕了。孩子是值得欢迎的,但它是不可能怀孕的姐姐很不高兴,这是治疗,是花费在医生和药品的财富。
奥列格回家的早晨,没有任何警告,将不会在家里睡觉。当玛莎问他在哪里,奥列格拉着妻子的手粗糙的脸,他的后脑勺撞到墙上。她失去了知觉 - 当我感悟到躺在血泊中。这是其一。
从医院回来后,奥列格的妻子来到他的感觉。龙恳求他的膝盖宽恕,停止饮用。但是这已经足够时间并不长 - 在一些一年半的女孩出现了,傲慢地叫你家的电话,并要求奥列格成为常态闻到奇怪的香水在枕头上,口红的衬衫
。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