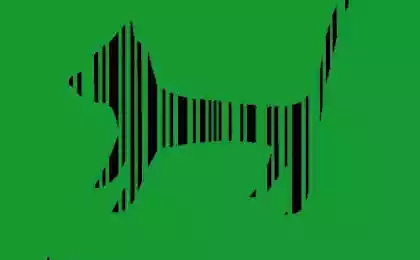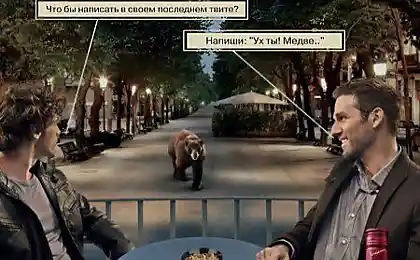671
Bratelnik
我bratelnik十三年前去世了。他还不五十元。我花了,并没有醒来的一天。这是他最后的绝招,他不时抛出来的时候,遭受比亲人的神经系统测试。
我们喜欢这个ohlamona,Rinatku我们的,他们是因为他害怕。在性格,他去batyu - 这属于人为之疯狂的品种。就在同泪是我bratelnik。
当我还是挺马尔采夫他为各种斯柯达称为Kotovski的(对什么都剃掉胡子,智能)。而当长大了,护士终于不再削减nalyso的Rinat突然接到一个华丽的卷发。然后,在所有前苏联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美国的安吉拉·戴维斯,当局追求,为此,有一些东西还是反对与他们战斗的东西在那里。在我弟弟的头发是完全一样的。并与扁平的鼻子 - 他是安吉拉·戴维斯活脱。所以他们叫他一段时间。
而当不守规矩的孩子长大的Rinat谁爱suprotivnikov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战斗机“取高良姜,”它被称为羊。好吧,绵羊 - 羊都没有,和弟弟在时间已经习惯了他的klikuhe并没有采取“我们良姜”,当他们叫。他与盖 - 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它是由最强的霜冻去裸,常常冰雪覆盖的头,这是颤抖像狗当你在大街上的某个地方。
当他在他的村庄已不再打架,他就开始在附近的村庄Moiseevku,九公里,去他的“IZH-木星”的冒险。村里的居民称为“盟友”,因为有许多德国人。他们有一个良好的zavklubom,和舞蹈在这里举行,几乎每天。这就是bratelnik和避免他的好斗精神。
而我却来自区中心,在那里他所生活和工作,我的父母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她弟弟家或划伤外貌,还是一个新的夏纳。
一旦它甚至在拍摄同一Moiseevke。显然,曾经想吓唬和劝阻他们的村庄和他们的女佣这个不请自来的毛茸茸的鞑靼人。但是,墨盒是一个单身汉。但不知何故Rinatka不知道,而且还在当地Moiseevskaya“权威”tselivshegosya他用猎枪褐色的羽毛。
Pyzhevoy负责在两到三米的距离前额右侧抨击,并把他在他的背上。
- 听着,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简单的一叠可以填写一个锥形! - 笑,他后来告诉我,同样otsvechivaya凹凸。然后,他变得严肃起来,轻轻地挤压肿胀光泽的额头。 - 而事实上,和眼睛能敲山羊!好了,什么都没有,我还是他的podlovlyu ...
他和后军有同样的shebutnoy,pokolobrodil同村的一两年,我几乎嫁给了来访的老师,甚至去结识她的父母在巴尔喀什。但是,peredratsya管理与未来的家庭和耻辱被放逐从他的家人没有接受失败的新娘。那天,我清楚的树桩,不敢跟他回回到自己的村庄,在巴尔喀什呆在家里。
一个bratelnik再次单独留在家中。无聊,想到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Pisegovym名为米尔扎(没有人真的不记得是谁和他是什么,俄罗斯,获得了辉煌的绰号,他绝不匹配它)去国外的流量。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赚更多的钱,让您在纳霍德卡,一个端口到那儿第一,码头工人,然后是水手。他们排在一起粉饰所有国营农场skotobazy在我们的国营农场的办公室。这是一直在做农家妇女 - 大约二十人,站在舞台上,用笑话和歌曲能爬周韧皮刷,蘸白,谷仓和Telyatnikov的土墙上。而这些Screwtape经理答应做的工作速度更快,用更少的钱。
总经理想知道它会救他,虽然半信半疑,但他同意了。而事实上,他们做到了!而这个秘密是,我拉住了在一个朋友的枪建设者区中心他的兄弟,但后者天的选手的帮助和粉刷部门中的所有基地。并在两层!
切钱不是孩子,他还清了农场,赚不醉无-TH-次,说明了自己的意图的严重性,并赶走了他的梦想。
从里纳特的第一个字母来了一个月。他简要地报告说,他们正在码头工人在纳霍德卡港,与他们的计划的开始部分是一致的。然后还有很长的信。
从他的弟弟在三个月内另一条消息来了。他从里写道,纳霍德卡他们米尔扎没有工作,没有采取他们的水手,但在所有波罗的海国家应能。再沉默 - 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
“我们的孩子的环游不见了!” - 决定村庄和所有的骄傲与自己的同胞。是啊,走了!我的母亲很担心,问我以某种方式寻找shaloputnogo兄弟。我去的埃基巴斯图兹市警察局刑事调查部(在Ekibas我曾在1980年),并写了一份声明中关于一个相对的损失。
里纳特发现Novokuibyshevsk殖民地。他坐在那里的流浪 - 那么它很容易。事实证明,缠绕在全国各地有住所的最后一个地方纳霍德卡。在他们里加米尔扎没有登记,成为一名水手远航模糊,因为早晨的薄雾在波罗的海,和他们第一次跌出并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梦想。
米尔扎满足 - 并去了什么地方得无影无踪,但在通缉名单上还宣称,和里纳特一年服后,回到家乡薄如Koschey,似乎posereznevshim。吃得太多他母亲的家的口粮,他仔细研究了他的老同学凯瑟琳德国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们已经开始共同生活。例如,里纳特开始,最后到成人完全平静下来,甚至停下来叫他拉姆。
但是,这些相同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姐妹罗莎结婚,并搬到与她的丈夫到BAM。他们通常定居,他们住在一个村庄里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北部和铁路上赚坏。他们拉到他寡居的时候我的母亲 - 护士与她的孙女。而自从八十年代末,村里开始来kirdyk(国营农场倒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自己的庭院),BAM决定mahanut和里纳特。
首先他送到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在完成农场(售罄众生之类的东西的遗迹)所有的工作去照顾自己。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叶,哪去了鄂木斯克(从那里一周火车到哈巴罗夫斯克),并...走了。奠定了一周过去了它的方式在一个漫长的旅程,我去了第二个。但他并没有出现在落叶。它不响,不写了。
他的妻子凯特,母亲和姐姐感到震惊:也许,在发生的方法是什么?知道他的爆发力的性格,我们认为公路某处受不了和就吵起来了。于是他们就把他甩下车。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危险还在后面我们的道路上孤独的旅行者?
并开展一个向警方供述一个人失踪。两个月后,他突然宣布自己的硬木。斯利姆,其长满卷曲lohmami到肩膀,但热闹。之后,大喜过望的女人ottaskali他的头发,吃饱喝足,bratelnik屈尊告诉它下跌多达两个月,为什么沉默了所有的时间。
在鄂木斯克,他在等待他的火车坐的长椅上站外手里拿着一瓶冰镇啤酒。我没有时间喝它,以及如何接近附着一些农民。我要了烟,说话。正如他所说的,他也要去哈巴罗夫斯克。然后,他拿出袋子打开一瓶伏特加酒,腌黄瓜曲线。他提出一喝就开始对桩基:“火车dopem的休息,甚至添加!”。弟兄吞噬栈,记住,即使点燃......还有 - 失败。
我醒来的时候同样的板凳上。该头嗡嗡作响,不能想。包包的东西是在长凳下的 - 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的夹克胸前的口袋中有钱,五百卢布 - 还有辣根睡着了。即使是在火车上哈巴罗夫斯克古怪klofelinschik护照票伸了出来(在那些年里,火车票仍然可以购买,收回没有护照)。谢谢你,虽然他没有拿起护照,溜回了自己的口袋哄骗他们的牺牲。
这种情况 - 即使是背靠背的车到村里200公里路程,让周围的帽子与家人联系。但是,这是不是一种选择。但是,你会怎么做?然后bratelnik,他们说,幸运的聋人。他无意中发现招聘人员(如运行铁路站) - 在一个私人作坊工作修理冰箱所需的机制。哥同意了,虽然条件几乎奴役。然而,两个月后,他再次赢得了在机票上,和一个小的“路边”的钱。
但我记得他不是这些你的冒险。里纳特一直灵活,比例匀称,很容易和快速地移动。而这也使他自然地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摇像疯了一样,在我们国家的俱乐部,打破了他的身体和四肢在最不可思议的角度,从字面上目瞪口呆。这是奇妙的东西!跳舞不再身边盯着他的PA,比他们忙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合作伙伴。
有一天,我是这样来到村里周末,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就跟着他Izsak Rinatkoy在另一个相邻到我们村,额尔齐斯河的地区中心。那么,这是为什么?是的,也许,喝啤酒......嗯,是的。额尔齐斯河起初,当有只开啤酒厂,啤酒是非常badsome。
他面前是一个一箭之遥 - 五公里。但在额尔齐斯河。横必须是在渡船上。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以及这些年去了SP-6,10多辆汽车。
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开着摩托车在轮渡的鼻子,站在一边,烟,吐泡沫的水 - 蒸汽警笛大哭大闹,并已经开始行动了。
然后从“伏尔加”,它代表了驾驶室下,有一个响亮的调“Lezginka”。两排机器(通常在忙,不过那个时候是免费的)之间的过道立即引起了骑兵的三重奏 - 由车臣的类型和举止开始投掷手来回,描绘这个美丽的,在一般情况下,舞。
但在他们的靓丽表现,唉,他没有收到。而作为任何渡轮podhlopyvali异构观众一个舞者,无论怎样怂恿呼喊“亚萨!” - 不是来自他们“Lezginka”,这就是它!
嗯,是的,是的,但我不知道我自己!当然,它发生在这些日子里,观众与车臣将立即开始战斗,因为“Lezginka”一些成为一种忌,为他人 - 侵略和bespredelschiny的象征。再次 - 这些天,当种族间关系恶化非常多。
不过,在这些年里,我还没有人对别人是激烈的,不妥协的分离来了,他们的土著人。而“Lezginka”的一切都只是美丽,壮观的舞蹈,这是高兴地涉足其实施中餐馆庆祝活动所有杂。当然,除非,他知道如何跳舞吧。
这些车臣人因某种原因不能。还是不想开放,因为它应该在这个舞蹈。
Rinatka轻蔑地眯着眼,喃喃地说:“是的,他们似乎有问题鸡蛋”他吐出了他的香烟海里,并在两跳,他发现自己的骑手之一。那些即使在意外停止。
一个Rinatka第一拉伸像重视,有轻微偏转好了所有我的身体回来,在一个方向全身心可识别手势,从自己侧身,另,踮起脚尖,去,去,摇晃音乐毛茸茸的头。欣喜车臣东西咽喉和不和谐的喊道,并开始狂跳时钟在他的手中。
在一个小补丁渡轮是车与人之间挤爬上车,桥驾驶室的身体,以更好地观察所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一切的“Lezginka”旋风纺像陀螺一样,我的兄弟,曾经在特殊pristukivaya高跟鞋多了,给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一古老的舞蹈中间,使现代节奏的音符。
在全速去渡口的对岸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有人喷着他的脸颊通红,并吹口哨,有人从情感过剩只是骂得驾驶室有人挖空手掌,如鼓。
但音乐停止播放,并出了一口气Rinatka回到登上渡船,这是我,以及所有着迷看他跳舞。
- 好吧,你给兄弟! - 我刚才说的。 - 你在哪里学跳舞吗?
- 哪里,哪里... - 一会儿Rinatka。 - 是的,在舞蹈。在部队,太。但总的来说我自己莫名其妙变成...
这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抓飞所有的笔记,并Rinatka任何舞蹈可以发挥也许是第一次。他有,显然,一个人才,他的一生中值得应用的,并没有发现。
他只有45,有一天,当凯瑟琳,妻子,没能叫醒他在上午。有不安,一旦我的心脏bratelnika突然停止。
十三年,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而在我的眼前都是令人难忘的一幕神奇评为额尔齐斯河中间“Lezginka”摆渡的可执行文件。
舞蹈,曾经被许多钟爱,并在我们这个时代诅咒...
(Sibirskie)

资料来源:
我们喜欢这个ohlamona,Rinatku我们的,他们是因为他害怕。在性格,他去batyu - 这属于人为之疯狂的品种。就在同泪是我bratelnik。
当我还是挺马尔采夫他为各种斯柯达称为Kotovski的(对什么都剃掉胡子,智能)。而当长大了,护士终于不再削减nalyso的Rinat突然接到一个华丽的卷发。然后,在所有前苏联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美国的安吉拉·戴维斯,当局追求,为此,有一些东西还是反对与他们战斗的东西在那里。在我弟弟的头发是完全一样的。并与扁平的鼻子 - 他是安吉拉·戴维斯活脱。所以他们叫他一段时间。
而当不守规矩的孩子长大的Rinat谁爱suprotivnikov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战斗机“取高良姜,”它被称为羊。好吧,绵羊 - 羊都没有,和弟弟在时间已经习惯了他的klikuhe并没有采取“我们良姜”,当他们叫。他与盖 - 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它是由最强的霜冻去裸,常常冰雪覆盖的头,这是颤抖像狗当你在大街上的某个地方。
当他在他的村庄已不再打架,他就开始在附近的村庄Moiseevku,九公里,去他的“IZH-木星”的冒险。村里的居民称为“盟友”,因为有许多德国人。他们有一个良好的zavklubom,和舞蹈在这里举行,几乎每天。这就是bratelnik和避免他的好斗精神。
而我却来自区中心,在那里他所生活和工作,我的父母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她弟弟家或划伤外貌,还是一个新的夏纳。
一旦它甚至在拍摄同一Moiseevke。显然,曾经想吓唬和劝阻他们的村庄和他们的女佣这个不请自来的毛茸茸的鞑靼人。但是,墨盒是一个单身汉。但不知何故Rinatka不知道,而且还在当地Moiseevskaya“权威”tselivshegosya他用猎枪褐色的羽毛。
Pyzhevoy负责在两到三米的距离前额右侧抨击,并把他在他的背上。
- 听着,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简单的一叠可以填写一个锥形! - 笑,他后来告诉我,同样otsvechivaya凹凸。然后,他变得严肃起来,轻轻地挤压肿胀光泽的额头。 - 而事实上,和眼睛能敲山羊!好了,什么都没有,我还是他的podlovlyu ...
他和后军有同样的shebutnoy,pokolobrodil同村的一两年,我几乎嫁给了来访的老师,甚至去结识她的父母在巴尔喀什。但是,peredratsya管理与未来的家庭和耻辱被放逐从他的家人没有接受失败的新娘。那天,我清楚的树桩,不敢跟他回回到自己的村庄,在巴尔喀什呆在家里。
一个bratelnik再次单独留在家中。无聊,想到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Pisegovym名为米尔扎(没有人真的不记得是谁和他是什么,俄罗斯,获得了辉煌的绰号,他绝不匹配它)去国外的流量。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赚更多的钱,让您在纳霍德卡,一个端口到那儿第一,码头工人,然后是水手。他们排在一起粉饰所有国营农场skotobazy在我们的国营农场的办公室。这是一直在做农家妇女 - 大约二十人,站在舞台上,用笑话和歌曲能爬周韧皮刷,蘸白,谷仓和Telyatnikov的土墙上。而这些Screwtape经理答应做的工作速度更快,用更少的钱。
总经理想知道它会救他,虽然半信半疑,但他同意了。而事实上,他们做到了!而这个秘密是,我拉住了在一个朋友的枪建设者区中心他的兄弟,但后者天的选手的帮助和粉刷部门中的所有基地。并在两层!
切钱不是孩子,他还清了农场,赚不醉无-TH-次,说明了自己的意图的严重性,并赶走了他的梦想。
从里纳特的第一个字母来了一个月。他简要地报告说,他们正在码头工人在纳霍德卡港,与他们的计划的开始部分是一致的。然后还有很长的信。
从他的弟弟在三个月内另一条消息来了。他从里写道,纳霍德卡他们米尔扎没有工作,没有采取他们的水手,但在所有波罗的海国家应能。再沉默 - 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
“我们的孩子的环游不见了!” - 决定村庄和所有的骄傲与自己的同胞。是啊,走了!我的母亲很担心,问我以某种方式寻找shaloputnogo兄弟。我去的埃基巴斯图兹市警察局刑事调查部(在Ekibas我曾在1980年),并写了一份声明中关于一个相对的损失。
里纳特发现Novokuibyshevsk殖民地。他坐在那里的流浪 - 那么它很容易。事实证明,缠绕在全国各地有住所的最后一个地方纳霍德卡。在他们里加米尔扎没有登记,成为一名水手远航模糊,因为早晨的薄雾在波罗的海,和他们第一次跌出并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梦想。
米尔扎满足 - 并去了什么地方得无影无踪,但在通缉名单上还宣称,和里纳特一年服后,回到家乡薄如Koschey,似乎posereznevshim。吃得太多他母亲的家的口粮,他仔细研究了他的老同学凯瑟琳德国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们已经开始共同生活。例如,里纳特开始,最后到成人完全平静下来,甚至停下来叫他拉姆。
但是,这些相同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姐妹罗莎结婚,并搬到与她的丈夫到BAM。他们通常定居,他们住在一个村庄里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北部和铁路上赚坏。他们拉到他寡居的时候我的母亲 - 护士与她的孙女。而自从八十年代末,村里开始来kirdyk(国营农场倒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自己的庭院),BAM决定mahanut和里纳特。
首先他送到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在完成农场(售罄众生之类的东西的遗迹)所有的工作去照顾自己。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叶,哪去了鄂木斯克(从那里一周火车到哈巴罗夫斯克),并...走了。奠定了一周过去了它的方式在一个漫长的旅程,我去了第二个。但他并没有出现在落叶。它不响,不写了。
他的妻子凯特,母亲和姐姐感到震惊:也许,在发生的方法是什么?知道他的爆发力的性格,我们认为公路某处受不了和就吵起来了。于是他们就把他甩下车。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危险还在后面我们的道路上孤独的旅行者?
并开展一个向警方供述一个人失踪。两个月后,他突然宣布自己的硬木。斯利姆,其长满卷曲lohmami到肩膀,但热闹。之后,大喜过望的女人ottaskali他的头发,吃饱喝足,bratelnik屈尊告诉它下跌多达两个月,为什么沉默了所有的时间。
在鄂木斯克,他在等待他的火车坐的长椅上站外手里拿着一瓶冰镇啤酒。我没有时间喝它,以及如何接近附着一些农民。我要了烟,说话。正如他所说的,他也要去哈巴罗夫斯克。然后,他拿出袋子打开一瓶伏特加酒,腌黄瓜曲线。他提出一喝就开始对桩基:“火车dopem的休息,甚至添加!”。弟兄吞噬栈,记住,即使点燃......还有 - 失败。
我醒来的时候同样的板凳上。该头嗡嗡作响,不能想。包包的东西是在长凳下的 - 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的夹克胸前的口袋中有钱,五百卢布 - 还有辣根睡着了。即使是在火车上哈巴罗夫斯克古怪klofelinschik护照票伸了出来(在那些年里,火车票仍然可以购买,收回没有护照)。谢谢你,虽然他没有拿起护照,溜回了自己的口袋哄骗他们的牺牲。
这种情况 - 即使是背靠背的车到村里200公里路程,让周围的帽子与家人联系。但是,这是不是一种选择。但是,你会怎么做?然后bratelnik,他们说,幸运的聋人。他无意中发现招聘人员(如运行铁路站) - 在一个私人作坊工作修理冰箱所需的机制。哥同意了,虽然条件几乎奴役。然而,两个月后,他再次赢得了在机票上,和一个小的“路边”的钱。
但我记得他不是这些你的冒险。里纳特一直灵活,比例匀称,很容易和快速地移动。而这也使他自然地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摇像疯了一样,在我们国家的俱乐部,打破了他的身体和四肢在最不可思议的角度,从字面上目瞪口呆。这是奇妙的东西!跳舞不再身边盯着他的PA,比他们忙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合作伙伴。
有一天,我是这样来到村里周末,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就跟着他Izsak Rinatkoy在另一个相邻到我们村,额尔齐斯河的地区中心。那么,这是为什么?是的,也许,喝啤酒......嗯,是的。额尔齐斯河起初,当有只开啤酒厂,啤酒是非常badsome。
他面前是一个一箭之遥 - 五公里。但在额尔齐斯河。横必须是在渡船上。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以及这些年去了SP-6,10多辆汽车。
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开着摩托车在轮渡的鼻子,站在一边,烟,吐泡沫的水 - 蒸汽警笛大哭大闹,并已经开始行动了。
然后从“伏尔加”,它代表了驾驶室下,有一个响亮的调“Lezginka”。两排机器(通常在忙,不过那个时候是免费的)之间的过道立即引起了骑兵的三重奏 - 由车臣的类型和举止开始投掷手来回,描绘这个美丽的,在一般情况下,舞。
但在他们的靓丽表现,唉,他没有收到。而作为任何渡轮podhlopyvali异构观众一个舞者,无论怎样怂恿呼喊“亚萨!” - 不是来自他们“Lezginka”,这就是它!
嗯,是的,是的,但我不知道我自己!当然,它发生在这些日子里,观众与车臣将立即开始战斗,因为“Lezginka”一些成为一种忌,为他人 - 侵略和bespredelschiny的象征。再次 - 这些天,当种族间关系恶化非常多。
不过,在这些年里,我还没有人对别人是激烈的,不妥协的分离来了,他们的土著人。而“Lezginka”的一切都只是美丽,壮观的舞蹈,这是高兴地涉足其实施中餐馆庆祝活动所有杂。当然,除非,他知道如何跳舞吧。
这些车臣人因某种原因不能。还是不想开放,因为它应该在这个舞蹈。
Rinatka轻蔑地眯着眼,喃喃地说:“是的,他们似乎有问题鸡蛋”他吐出了他的香烟海里,并在两跳,他发现自己的骑手之一。那些即使在意外停止。
一个Rinatka第一拉伸像重视,有轻微偏转好了所有我的身体回来,在一个方向全身心可识别手势,从自己侧身,另,踮起脚尖,去,去,摇晃音乐毛茸茸的头。欣喜车臣东西咽喉和不和谐的喊道,并开始狂跳时钟在他的手中。
在一个小补丁渡轮是车与人之间挤爬上车,桥驾驶室的身体,以更好地观察所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一切的“Lezginka”旋风纺像陀螺一样,我的兄弟,曾经在特殊pristukivaya高跟鞋多了,给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一古老的舞蹈中间,使现代节奏的音符。
在全速去渡口的对岸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有人喷着他的脸颊通红,并吹口哨,有人从情感过剩只是骂得驾驶室有人挖空手掌,如鼓。
但音乐停止播放,并出了一口气Rinatka回到登上渡船,这是我,以及所有着迷看他跳舞。
- 好吧,你给兄弟! - 我刚才说的。 - 你在哪里学跳舞吗?
- 哪里,哪里... - 一会儿Rinatka。 - 是的,在舞蹈。在部队,太。但总的来说我自己莫名其妙变成...
这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抓飞所有的笔记,并Rinatka任何舞蹈可以发挥也许是第一次。他有,显然,一个人才,他的一生中值得应用的,并没有发现。
他只有45,有一天,当凯瑟琳,妻子,没能叫醒他在上午。有不安,一旦我的心脏bratelnika突然停止。
十三年,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而在我的眼前都是令人难忘的一幕神奇评为额尔齐斯河中间“Lezginka”摆渡的可执行文件。
舞蹈,曾经被许多钟爱,并在我们这个时代诅咒...
(Sibirskie)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