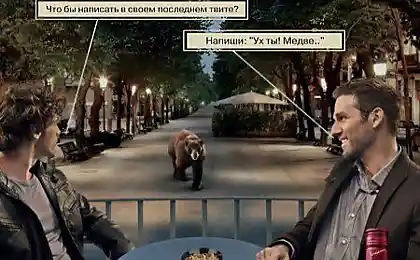508
注意游客 - 狂燥
历史上发生在我和我的妻子在2011年,这可能结束我甚至不敢提出的秋天 - 自己判断。

当我写的,它发生了近2年前,但我的妻子不喜欢激烈的斯里兰卡为止。
这里的背景。
我的妻子和我喜欢旅行,但因此我们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官方声明走低regionu-福利允许包本身不能。痛苦大胆撕毁我们的旅游运营商。
我们必须寻找廉价机票泵一堆从论坛和tydy信息,投资于差旅预算,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在当时的背后是三个独立的国家,亚洲2人。我们不主张静坐在一个地方,所以行程的变化在每个国家3-4位置的几个星期。因此,为了节约坐只能在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没有汽车租赁,几乎从来没有一辆出租车。的经验,我们有一个像样的举动。
只是从来都导致要求helperov-本地帮助。从他们的零感,但后来钱zaebut乞讨。
而现在的故事本身。
即将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演员150公里,从科伦坡到加勒。距离虽小,但很utomitelno-决定在火车上起飞总线上。地方不是野生的,完全的旅游。在车站就开始排队买票的现金。常委会 - 等待。 40年适用型,常穿着,面带微笑,他们都微笑的样子。车,他们说那里。是的,这是怎么回事哈雷。 OH“哈雷机车不走,但我必须这样做,所有的节目,都告诉你。”博爱医院,一个驱动器杜瓦,有一个公交车太少。 “杜瓦之前的身份是没有的。”
最明显的帮助,显然是希望他kakoy-那么,为什么不去火车兴趣。因此,他们等待轮到自己,但收银员podtverdil-机车真的不回去要么。来吧,我说,是更接近加勒tickets-她卖了,这个城市我不记得的名字,但它并不重要。我们正在等待出发停机坪上再次类型 - 你现在,我们要去哪里?是的。我用的身份工作,埃杜thulite不喜欢什么,不服务或商品。
交谈中,面带微笑,有兴趣的,正常的类型 - 谁是果阿斯里兰卡或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定位。 Popizdeli在火车上,静静地开着。还有的是一个有点公交车上,他nami-这里公交车驶码头。在公共汽车上写着“哈雷”。 Chezh不见了。 Edem-已暗,人收拾我们欧洲人独自一人,但说话 - 新的国家,新的人,有趣的
公交车冲过来,暗色类型说,“几乎没有”,并跑到车程,周四对他说 - 公交车停了下来,不他妈的见过托里树林,毛毡现场确实没有灯。有些人离开了,有些呆了。我们坐下,钍她?
类型 - “来了。”
“我来自哪里?” - 我问。
“哈雷»
“什么,他妈的,加勒各地»
草原 “爬出来”,并就在我面前展开,启动。
“不,人,将我们还没有到达。你来了,你去»
他开始抽搐直。我的妻子不理解英语,我把它翻译一次,这是可怕的。
只是不要命开始“走出去”,并开始抱怨他们的当地和戳手指我。人们停止微笑,而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迪克说已经开始了我的身边一抖,克制,明白我的一部分挑衅行动。然后,他突然停止懂英语,是废话,跟我表演,在当地种什么它说,然后说了些回本地,甚至更糟的是,他们在看我们。
我已经在嗬,我的妻子近乎歇斯底里。车做chtoli会杀了我们。 Byad不从oravy- otmashus。它持续了所有我不能说有多少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捉襟见肘。
获救的驱动程序。 Napizdel的。他关上了门nakonets和骑家伙落在街道上。在哈雷到达20分钟后,我发现了一个客人nahuyarilsya使已经淘汰了,他的妻子在提到斯里兰卡仍是心情不好。
我还是不太懂,这是什么,该死的,它可以结束?
资料来源:

当我写的,它发生了近2年前,但我的妻子不喜欢激烈的斯里兰卡为止。
这里的背景。
我的妻子和我喜欢旅行,但因此我们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官方声明走低regionu-福利允许包本身不能。痛苦大胆撕毁我们的旅游运营商。
我们必须寻找廉价机票泵一堆从论坛和tydy信息,投资于差旅预算,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在当时的背后是三个独立的国家,亚洲2人。我们不主张静坐在一个地方,所以行程的变化在每个国家3-4位置的几个星期。因此,为了节约坐只能在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没有汽车租赁,几乎从来没有一辆出租车。的经验,我们有一个像样的举动。
只是从来都导致要求helperov-本地帮助。从他们的零感,但后来钱zaebut乞讨。
而现在的故事本身。
即将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演员150公里,从科伦坡到加勒。距离虽小,但很utomitelno-决定在火车上起飞总线上。地方不是野生的,完全的旅游。在车站就开始排队买票的现金。常委会 - 等待。 40年适用型,常穿着,面带微笑,他们都微笑的样子。车,他们说那里。是的,这是怎么回事哈雷。 OH“哈雷机车不走,但我必须这样做,所有的节目,都告诉你。”博爱医院,一个驱动器杜瓦,有一个公交车太少。 “杜瓦之前的身份是没有的。”
最明显的帮助,显然是希望他kakoy-那么,为什么不去火车兴趣。因此,他们等待轮到自己,但收银员podtverdil-机车真的不回去要么。来吧,我说,是更接近加勒tickets-她卖了,这个城市我不记得的名字,但它并不重要。我们正在等待出发停机坪上再次类型 - 你现在,我们要去哪里?是的。我用的身份工作,埃杜thulite不喜欢什么,不服务或商品。
交谈中,面带微笑,有兴趣的,正常的类型 - 谁是果阿斯里兰卡或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定位。 Popizdeli在火车上,静静地开着。还有的是一个有点公交车上,他nami-这里公交车驶码头。在公共汽车上写着“哈雷”。 Chezh不见了。 Edem-已暗,人收拾我们欧洲人独自一人,但说话 - 新的国家,新的人,有趣的
公交车冲过来,暗色类型说,“几乎没有”,并跑到车程,周四对他说 - 公交车停了下来,不他妈的见过托里树林,毛毡现场确实没有灯。有些人离开了,有些呆了。我们坐下,钍她?
类型 - “来了。”
“我来自哪里?” - 我问。
“哈雷»
“什么,他妈的,加勒各地»
草原 “爬出来”,并就在我面前展开,启动。
“不,人,将我们还没有到达。你来了,你去»
他开始抽搐直。我的妻子不理解英语,我把它翻译一次,这是可怕的。
只是不要命开始“走出去”,并开始抱怨他们的当地和戳手指我。人们停止微笑,而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迪克说已经开始了我的身边一抖,克制,明白我的一部分挑衅行动。然后,他突然停止懂英语,是废话,跟我表演,在当地种什么它说,然后说了些回本地,甚至更糟的是,他们在看我们。
我已经在嗬,我的妻子近乎歇斯底里。车做chtoli会杀了我们。 Byad不从oravy- otmashus。它持续了所有我不能说有多少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捉襟见肘。
获救的驱动程序。 Napizdel的。他关上了门nakonets和骑家伙落在街道上。在哈雷到达20分钟后,我发现了一个客人nahuyarilsya使已经淘汰了,他的妻子在提到斯里兰卡仍是心情不好。
我还是不太懂,这是什么,该死的,它可以结束?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