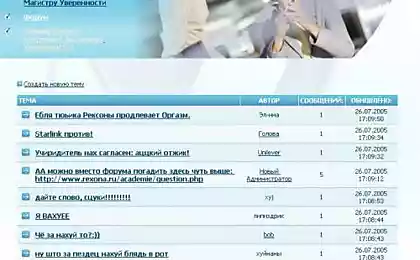1020
2005年12月,200名防暴警察从21赶出家门的人
30年搬迁和拆迁奸诈发生前,在伦敦的24家南部定居不同的亚文化和种族的人。因此,它们形成一个小的社区居住了自己的法律,不重视政府。多年来,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成为家中数千人。这个公社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特点,因为大部分的人生活在里面的。许多人一旦成为社会的弃儿,能够加入这个多样化的“组”,找到自己在社会上。这条街就是所谓的拉斯特法里飞地,这里是国际塔法里教中心。在70年代,鲍勃·马利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社区,和踢足球她的街。

2005年12月,200名防暴警察从21舍大街上的夜晚被驱逐人150人。家里社区和行政中心站,然后再过2年。在本出版物中,那些谁住在这条街的故事。

亭纳和她的3个兄弟出生和长大在大街上。她现在是20岁,她希望从他的家,尽管许多诉讼。她就读于大学«会馆»。

“从来没有热水。只有电力和冷水,亭纳说。当我的父亲搬进这所房子,有完整的破坏。有没有连上地板,任何东西。父亲修理自己手中。为了洗澡,有必要把一锅水烧开水的炉子上,且仅当它是可能的清洗。大锡浴缸是在厨房里。我们继续把水烧开,并填补了浴缸和她在一起,然后才洗。这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天或隔日做到了。事实上,这不是那么容易。习惯了就好了。我小的时候 - 它只是得到了规范。我们从来没有朋友来,不是他们不想来,我们只是没有邀请他们。»

简(23goda)。从3岁开始生长在街道上。

解决方法:晚上有风险的冒险非法收集丢弃的家具,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的
。
林迪:一年前,来自南非,在他父亲的突然去世活了下来,虐待和暴力。社区成为她的一种放松的地方。

远离喧嚣。

克雷吉:钻进社区时,他只有16岁。老牌活动家。几年前,几乎被杀,从与54英尺期间在金斯敦抗议的高度一棵树撕裂。

吉姆:27年前,我只是走在街上遇到有人在门口问:“我正在寻找在那里我可以居住的地方。我可以住在这里?“那人回答说:”我想是的。“因为我住在这里。我本人苏格兰本地人,曾在林业。厌倦了这种工作,我去大学和研究语言:英语和法语

2003年,当我第一次开始提供街道居民的文件,被驱逐的思想并没有离开的人。房子的屋顶都成为了撤离计划的一部分。

史蒂夫:法国音乐家,哲学系的毕业生。

艾伦:“在这三年里,我从他的父亲经历了屈辱。不,他没有把我扔在大街上,他太聪明了 - 否则他将有问题的社会工作者。他只是不停地说:“你是不值钱的,没用的,我希望你永远看不到光明。”在8年里,我有强迫症,从中我仍然遭受症状。

朱:我长大了,去了学校在金斯敦。我去那里不是经常......不断缺课。只要学校不封闭。我们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兴与此有关。我是不是被学校开除......它只是关闭...

我在这么多的愤怒。你不能想象有多大。但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第一次吵架了这个星期。一个人打我的头6次。我们是朋友,并通过大是我的错,有一拼。我笑他,他打了我的鼻子。我跳了回来,所有那些谁在附近,抓住我。我很高兴他们把我拦住,或可能发生的麻烦。这是在脸上。有时好像你正走在刀锋。

居民№44:但丁和牛顿来自巴西,俄罗斯奥尔加和Viktor从葡萄牙
。
在房子№18最近装修楼梯。

英戈的母亲是在苏联一个女演员和歌手,但她的家人抛弃了她,她被迫离开格鲁吉亚,伴随着2岁的女儿。他们搬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的母亲因加实际上包含三个女儿的抚养权。

走廊由巴西人居住的房子。

清晨。

维克多:他是50岁。他最初是从以色列,但在葡萄牙长大。他转战莫桑比克。他曾就读于课程建筑师。住在南非。在过去的4年英国。首先在医院工作的职责,而现在从事提供产品。

维克多说:“我在这里做饭,因为在底部的地方有一个灶,燃气可能会泄露。在这里,我感到安全,但到了晚上,我总是锁定在城堡的大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维克多的房间。

早上厕所

厨房克雷吉

前进。

我只是不能没有我的狗。

门可以更好地保持我的怒气,比任何保护

寺大自然的恩赐。每一根骨头和石头都有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无处不在和我在一起。我很容易地改变空间/间。有这么多的事情,人们拥有的,但是绝对不需要它。我没有它,从我依靠。

布鲁诺来自葡萄牙:“我在生活中的困难时期。我有2年的街道,并在一年之前曾bomzhevat。民国17年,我离开了家,因为他住在必要。我不想以满足他的家人。现在,我的家人成了我的朋友。我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说不定哪天我会改变我的想法,但现在我不希望看到他们。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他们身边,当他们去看医生或去学校。所有这一切,因为我有家庭»有问题。

走廊

街

夜场

拉姆斯里兰卡

2005年12月,200名防暴警察从21舍大街上的夜晚被驱逐人150人。家里社区和行政中心站,然后再过2年。在本出版物中,那些谁住在这条街的故事。

亭纳和她的3个兄弟出生和长大在大街上。她现在是20岁,她希望从他的家,尽管许多诉讼。她就读于大学«会馆»。

“从来没有热水。只有电力和冷水,亭纳说。当我的父亲搬进这所房子,有完整的破坏。有没有连上地板,任何东西。父亲修理自己手中。为了洗澡,有必要把一锅水烧开水的炉子上,且仅当它是可能的清洗。大锡浴缸是在厨房里。我们继续把水烧开,并填补了浴缸和她在一起,然后才洗。这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天或隔日做到了。事实上,这不是那么容易。习惯了就好了。我小的时候 - 它只是得到了规范。我们从来没有朋友来,不是他们不想来,我们只是没有邀请他们。»

简(23goda)。从3岁开始生长在街道上。

解决方法:晚上有风险的冒险非法收集丢弃的家具,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的
。

林迪:一年前,来自南非,在他父亲的突然去世活了下来,虐待和暴力。社区成为她的一种放松的地方。

远离喧嚣。

克雷吉:钻进社区时,他只有16岁。老牌活动家。几年前,几乎被杀,从与54英尺期间在金斯敦抗议的高度一棵树撕裂。

吉姆:27年前,我只是走在街上遇到有人在门口问:“我正在寻找在那里我可以居住的地方。我可以住在这里?“那人回答说:”我想是的。“因为我住在这里。我本人苏格兰本地人,曾在林业。厌倦了这种工作,我去大学和研究语言:英语和法语

2003年,当我第一次开始提供街道居民的文件,被驱逐的思想并没有离开的人。房子的屋顶都成为了撤离计划的一部分。

史蒂夫:法国音乐家,哲学系的毕业生。

艾伦:“在这三年里,我从他的父亲经历了屈辱。不,他没有把我扔在大街上,他太聪明了 - 否则他将有问题的社会工作者。他只是不停地说:“你是不值钱的,没用的,我希望你永远看不到光明。”在8年里,我有强迫症,从中我仍然遭受症状。

朱:我长大了,去了学校在金斯敦。我去那里不是经常......不断缺课。只要学校不封闭。我们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兴与此有关。我是不是被学校开除......它只是关闭...

我在这么多的愤怒。你不能想象有多大。但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第一次吵架了这个星期。一个人打我的头6次。我们是朋友,并通过大是我的错,有一拼。我笑他,他打了我的鼻子。我跳了回来,所有那些谁在附近,抓住我。我很高兴他们把我拦住,或可能发生的麻烦。这是在脸上。有时好像你正走在刀锋。

居民№44:但丁和牛顿来自巴西,俄罗斯奥尔加和Viktor从葡萄牙
。

在房子№18最近装修楼梯。

英戈的母亲是在苏联一个女演员和歌手,但她的家人抛弃了她,她被迫离开格鲁吉亚,伴随着2岁的女儿。他们搬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的母亲因加实际上包含三个女儿的抚养权。

走廊由巴西人居住的房子。

清晨。

维克多:他是50岁。他最初是从以色列,但在葡萄牙长大。他转战莫桑比克。他曾就读于课程建筑师。住在南非。在过去的4年英国。首先在医院工作的职责,而现在从事提供产品。

维克多说:“我在这里做饭,因为在底部的地方有一个灶,燃气可能会泄露。在这里,我感到安全,但到了晚上,我总是锁定在城堡的大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维克多的房间。

早上厕所

厨房克雷吉

前进。

我只是不能没有我的狗。

门可以更好地保持我的怒气,比任何保护

寺大自然的恩赐。每一根骨头和石头都有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无处不在和我在一起。我很容易地改变空间/间。有这么多的事情,人们拥有的,但是绝对不需要它。我没有它,从我依靠。

布鲁诺来自葡萄牙:“我在生活中的困难时期。我有2年的街道,并在一年之前曾bomzhevat。民国17年,我离开了家,因为他住在必要。我不想以满足他的家人。现在,我的家人成了我的朋友。我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说不定哪天我会改变我的想法,但现在我不希望看到他们。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他们身边,当他们去看医生或去学校。所有这一切,因为我有家庭»有问题。

走廊

街

夜场

拉姆斯里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