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7
小说“1984年”反乌托邦的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借来的阴谋“我们”
“我们 - 最幸福的算术平均值。”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 - 在文学历史上最黑暗antiutopian作品之一。你可能熟悉他,就算没有读过书。一些生动的画面体现了英国作家变得普遍,并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是提够臭名昭著的“大哥”在其谁都逃不掉的“真理部”,这成为一个代名词虚假政府宣传的注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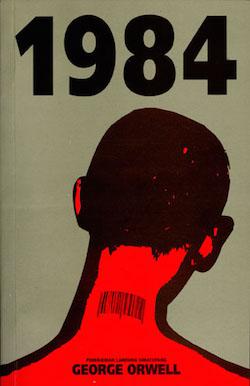
在奥威尔的世界描述了1984年,国家寻求确保大洋洲垄断的思想和市民的感受,通过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专业贴心。种姓社会猖獗的怀疑和谴责,“老大哥”的植入个人崇拜,最重视教年轻一代“正确”的意识形态。政府想出了一个“渐进”的语言(“新话”),这应该说是大洋洲的“快乐”的居民和灌输公民的神圣的双重思想“(”战争 - 是世界“,”缺乏知识 - 力量“等)。外交政策大洋洲侵略性和嗜血 - 该国不断在与邻国一场战争...什么都没有类似
?

不,这不是关于第三帝国或苏联,虽然笔者是相当透明地暗示了当时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后来他承认,他的启发,除其他事项外,他担任社会秩序的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小说“1984”出版于1949年,这一年,并在短短三年前在报纸«论坛»出现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批判的叶夫根尼·扎米亚京:“我们”,写于1920年
乔治·奥威尔和扎米亚京非常相似的作品 - 在首先排除大洋洲“老大哥”,在一个国家的第二章是“恩人”。不用说,“兄弟”和“恩人”董事会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而在1984年,乔治·奥威尔和第四千年扎米亚京的状态开始时试图摧毁个性的人,把他们变成听话露脸灰色质量,它的使命 - 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益。异议不是禁忌 - 它试图根除,作为一种现象。人物扎米亚京在奥威尔的小说“洗白”大脑使这个手术取出“幻想的中心”。两部作品的情节 - 一个男人,谁爱对方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使打不人道的制度。无论是英语还是俄语作家不离开的主角有机会击败系统 - 温斯顿·史密斯折磨被迫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和煽动性的观点,和A-503受到“剥夺想象”的过程,因此,他也背叛了盟友打击和崇拜我-330 ...

奇怪的是,与第一翻译“1984年”苏联的读者可能早在1950年达到(在本书小说问世于1957年)。或许从执政党的审查决定,作者提出的乐趣“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西方”,而不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异位扎米亚京是更可理解为“共产主义天堂”的建设者 -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权贵阶层的成员放弃了文学出版,“我们”,已经在小说中看到是的苏维埃美好未来的梦想无法接受的荒唐蠢事。在欧洲和美国几十年扎米亚京的作品享有一定的成功在苏联,因为它只能刊登在1988年,在重组改革,高度“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苏联公开性社会政治制度和局部反乌托邦小说出版的崩溃,重组年近七旬之前创建的,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还是来一个快乐的结局?
通过factroom.ru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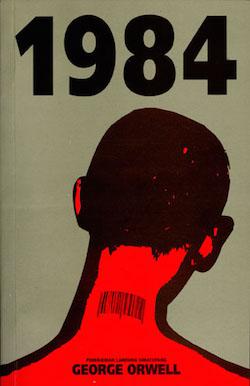
在奥威尔的世界描述了1984年,国家寻求确保大洋洲垄断的思想和市民的感受,通过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专业贴心。种姓社会猖獗的怀疑和谴责,“老大哥”的植入个人崇拜,最重视教年轻一代“正确”的意识形态。政府想出了一个“渐进”的语言(“新话”),这应该说是大洋洲的“快乐”的居民和灌输公民的神圣的双重思想“(”战争 - 是世界“,”缺乏知识 - 力量“等)。外交政策大洋洲侵略性和嗜血 - 该国不断在与邻国一场战争...什么都没有类似
?

不,这不是关于第三帝国或苏联,虽然笔者是相当透明地暗示了当时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后来他承认,他的启发,除其他事项外,他担任社会秩序的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小说“1984”出版于1949年,这一年,并在短短三年前在报纸«论坛»出现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批判的叶夫根尼·扎米亚京:“我们”,写于1920年
乔治·奥威尔和扎米亚京非常相似的作品 - 在首先排除大洋洲“老大哥”,在一个国家的第二章是“恩人”。不用说,“兄弟”和“恩人”董事会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而在1984年,乔治·奥威尔和第四千年扎米亚京的状态开始时试图摧毁个性的人,把他们变成听话露脸灰色质量,它的使命 - 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益。异议不是禁忌 - 它试图根除,作为一种现象。人物扎米亚京在奥威尔的小说“洗白”大脑使这个手术取出“幻想的中心”。两部作品的情节 - 一个男人,谁爱对方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使打不人道的制度。无论是英语还是俄语作家不离开的主角有机会击败系统 - 温斯顿·史密斯折磨被迫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和煽动性的观点,和A-503受到“剥夺想象”的过程,因此,他也背叛了盟友打击和崇拜我-330 ...

奇怪的是,与第一翻译“1984年”苏联的读者可能早在1950年达到(在本书小说问世于1957年)。或许从执政党的审查决定,作者提出的乐趣“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西方”,而不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异位扎米亚京是更可理解为“共产主义天堂”的建设者 -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权贵阶层的成员放弃了文学出版,“我们”,已经在小说中看到是的苏维埃美好未来的梦想无法接受的荒唐蠢事。在欧洲和美国几十年扎米亚京的作品享有一定的成功在苏联,因为它只能刊登在1988年,在重组改革,高度“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苏联公开性社会政治制度和局部反乌托邦小说出版的崩溃,重组年近七旬之前创建的,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还是来一个快乐的结局?
通过factroom.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