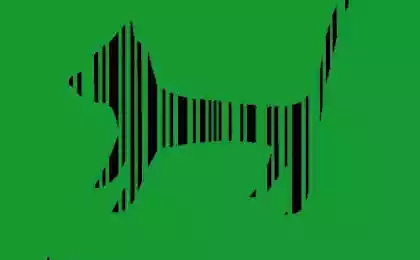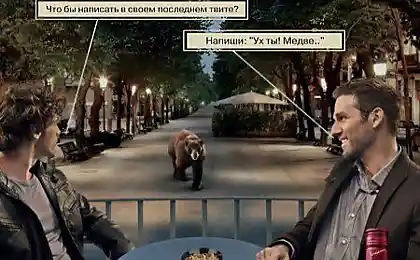976
约70
通过:germanych
1972年。阿尔巴特。附近的房子一个学号命名59。果戈理。但我的母亲给了我在学校的一个小盒子№58与深入研究德国(大中华区Afanasyevsky车道)。现在,学校是不是。和建筑被拆毁,以及学校的数量,这是建立在它的地方,改变。好吧,无所谓。因此,德国的特殊学校。语言开始从二年级学习。
我们如何生活?是的,通常。钢材十月党。在课堂上挂着“明星”画上的滤纸片和胶合的照片“链轮”成员的光芒。星星的指挥官改变周围 - 一周第二个星期,等我喜欢它,当轮到我是司令“链轮”。并不太喜欢它,当指挥官成为某种类型的女孩。
长凳我们的样本老体育馆,有斜面的顶部和...什么是叫这些木制的“门”被抛弃的时候,有必要摆脱党?如此之大,要拍自己的办公桌。并利用这些政党,也这是伟大的。
在从他的课德语课,我们去到顶部,“资深”地板。一旦在比赛中,我发现这是描绘斗争的吸墨纸:未知的弟子描绘战斗甲虫毛毡,毛毡屋顶还是一些东西。然后我的朋友和我不断尝试重现正是这种模式。
有一段时间,我去prodlёnku。在prodlёnke很有趣。一旦所有的课都做,每个人做他想要的东西。该女孩在一个圆圈,由纸型木偶戏任何假期都忙不停。主要是它是狼(该剧是有关的东西有多少狼在那里)。
但更多的时候,我放学后回家。并迅速取得的经验教训跑到街上。我们在街上游荡的朋友,爬在阁楼,屋顶,“森林”正在维修的建筑物,建筑物,车库。有一次,当我们坐在车库的屋顶和谈论的东西,一个人走了过去。我们赶上了他的左膀右臂制造“枪”,他瞄上了我们,说,“KKY!”然后眨眨眼睛,一边往前走着。和我们中的一个说,“你看到了吗?这是Vitsin!“Vitsin!然而,同样的makarom我看到尤里索洛明。在学校附近№59摄制的“路各各”我们一个小插曲 - 我们的孩子,和所有的邻国庭院 - 虔诚地看着他的大人,谁向我们走来的副官 - 在白卫队的形式(如我们当时以为) - 和说:“伙计们,走开,不要打扰,这里电影»设置。
阿May 9日,一个女孩的父亲所有的孩子带了一副肩章陆军中尉和我们把他们 - 真正的追! - 为了他的白衬衫,在他的头上,我们有蓝帽子“里拉”,这是“几乎像真实的东西。”而且我们展示的东西在舞台上。然后去在这个形式的步行路程。而且他们相信,我们都很羡慕。依旧会!我们有真正的肩章!
有时,用类我们去别的地方,例如,木偶Obraztsova。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的,很多有关。例如,我记得我的朋友和我Genka季托夫,如在深夜走过教堂,并开始谈论上帝。奇怪的是,我们争先恐后愤慨地说,由于它是如此的论文,没有神,当它是明确的傻瓜,他是。在这里,我们有过,年轻的1973年10月?该教堂有目前为Philippovsky胡同。
阿尔巴特小巷,同时逐步从老房子纯化。在1974年我们得到一个订单,我们搬进了新房子。我们被拆迁。在因为儿童在汽车的轮子掉落的高比例的新领域是一种学校系统配置:孩子不得不写信给学校未马路对面进行的方式。但是,妈妈送我去上学,这导致在街对面的方式,因为这是一所学校,他在那里学习德语。我记得,当我不得不打电话家庭住址,不知何故,我总觉得惭愧,我是“在错误的街上»。
此系统的配置,但是,不会被保存。当我们在四年级,一个男孩被打死。他直接在路边骑自行车。后轮脱落,自行车打滑,他倒在马路上。我回去带轮机。男孩下跌如此厉害,车轮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开车垃圾桶,那么这使他从字面上扁平头。于是他和埋葬,具有封闭头。我们跑了葬礼。然后,总是在屋前的葬礼,他们说了再见,乐队演奏,人们在哭。奇怪,但由于某些原因我还记得葬礼乐团的声音往往是在这里和那里听到的。在阿尔巴特我不记得了。
在三年级,我们学到的第二个转变。这是伟大的,因为它没有早起。一切都在学习,你还是在家里。而当你回来的学校是很空的。事实是不愉快的,当你学习,都在家里。在B类在课堂上,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楼,收集几乎所有的地方恶霸。然后,五人在这个类去坐牢(毕业后,当然),但在一般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班级男生去职业学校8日之后。
在三年级,我们在街上游荡。这是真的有一点不同的景观 - 不在家,但与此相反,几乎农村,虽然莫斯科。铅熔化起火,拍摄弹弓。一经推出就斯大林的乡间别墅,这是位于附近的其他袭击。他们爬上围栏。不知何故里面真正zarobeli剥离。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被抓到有会发生什么。
我有一个嗜好:由粘土城池和士兵雕塑。渐渐地,我获得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哦,我们安排了战斗。这种持续的迷恋一直到9年级。在了解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同学提出我们笑,如玩玩具士兵孩子。不过,很快从机构,我们了解到,他们自己在同一时刻在所有的木偶戏。然而,有些东西我向前跑。
我还喜欢阅读。区图书馆长的步行,试图去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基本上有一个关于创业英雄阴霾。一位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你看,你正在寻找一本书这么仔细,我想帮你”,并从一本厚厚的书由杰克·伦敦的表中删除给了我。我惊呆了杰克·伦敦没有那么多,从他对我来说,五年级说,给你。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以变得有趣。
更多我喜欢骑在博罗季诺全景,自小大力推崇拿破仑和一切与它连接。该博罗季诺全景我独自,与朋友和可能是一百倍。嗯,当然,我们去看电影。当然,我们走。走着走着,顺带也主要集中在建筑。在保护的时间,因为这样的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而不是在黑暗中爬在施工现场,爬上那里为推土机,挖掘机和起重机?在冬季,当然各种古怪的冬季娱乐。我记得,比如,像我们在山坡旁的道路修建了雪堡,并发射雪球从那里路过的车。一车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追我们。哦,我们什么斯基达德尔!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开始阅读“基度山恩仇记”,抓住冰淇淋。到了晚上,气温有所上升。生根喜爱。这太酷了 - 没必要去上学。每个人都在学校,和你回家baldeesh。当然,虽然,不喜欢吃药。而躺在床上不喜欢。
在学校里,课间休息,我们以“冲”总是带回家橙色的膝盖从磨在走廊地板上的胶泥。然后,他们开始玩捉迷藏。其中一个楼梯莫名其妙总是被关闭,我们必须改变渗透和播放,从地面跃起到地面。由于目前还没有什么突破 - 仍然不知道。尤其是当你考虑到领导跃升蒙住眼睛。
更多玩“大富翁”。事实并非如此,和自制。和金钱将借鉴。那么,在咀嚼口香糖包装纸太的过程。
我们的德语教师带领KID - 国际友谊俱乐部。有时她在那里中央KID派了几个人到先锋在列宁山宫殿。在先锋的宫殿,我们收到的信封从外国人谁想要与苏联的先驱对应。当然,外国人分别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我相当于一个波兰和一个德国人。德国罗兰命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罗腾堡的一些在他的两层楼的房子有五六个房间。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他的祖父参加过战争和死亡。我给他写了回来,我爷爷也转战来到所有伤员;信中问道:“哪里是你爷爷死了?”大多数德国人我还没有收到一个字母。波兰人还对应关系也相当迅速消退。说实话,我有点不是很感兴趣,对应他们。好了,我们互送明信片,以及讲述了家庭。还有什么?
一个同学决定把国际友谊的事情在商业基础上。他在KID以先锋宫沉溺于自己,拿起外国人的信,表面上是为了拿学校,他拿出日历,明信片和任何改变。然后,他抓住了它。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会议只进行“交易”。
和一个女孩(虽然不是来自我的课)对应了与罗马尼亚。一个罗写信给她:“送我一些紧身衣。”女孩开始思考:是什么意思罗马尼亚?毕竟,那么肯定我们甚至不能认为罗马尼亚要求送她最普通的运动裤。在一般情况下,所以我不觉得这个女孩打断了谈话。并不知我在罗马尼亚还是遗憾,她一直在等待来自苏联的紧身衣,可能。
嗯,这是一个童年是正常的。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主题。也就是说,当然,这是以前的,但不知何故不是很浮夸。并于1975年在库图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的房子正好相反,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开了一个石碑。不知怎的,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们会继续增加。我还记得,在1977年我去了五月在公交车上。当然,作为一个粗略的先驱我假装看窗外,并没有注意到。是的,我承认,我没有屈服的地方老男人和女人。而且我并不孤独。它曾经是先驱者的行为常见70年代一般规则(这甚至微型“混乱”是)。那么,在一般食品。然后我开始推人。我看到 - 老将。嗯,当然我有。他开始说:“看,坐,我喜欢你的泻血。”然后我得到了邪恶的,我把他的额头:“对我来说,血爷爷流下,因为他早已死于枪伤”老将几乎哽咽着愤慨。
你知道,我不记得他们的同龄人对退伍军人一些特殊的崇敬之情。它被认为由我们枯燥的整体性能的一部分。啊,5月9日好,那么就必须把学校设置的诗句,有必要邀请老兵,倾听他们告诉我们。它的枯燥和不感兴趣。如果我有一个人说,早在70年代末,我坐在在这些会议上专门纪念日的兴趣,那么我将被迫指责伪善的人。在所有的会议,我们从下枝收集。
然而,我记得 - 尽管它后来,在今年'81 - 从帆布帽子我唯一的女朋友缝补衣服,头饰是非常相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步兵。哦,我砍通过它。可惜的照片也无法生存。然后我给丑化另外一个,他带走了老师 - 喜欢,“你几乎法西斯恶棍戴帽子?”教室是他的盖帽。然而,我又往前跑。
我也第一次在学校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训。它是如此。我们的劳动派叫彼得L. Krasnobryzhev。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名字来源于他的父亲(或祖父),曾在红军和谁被授予红色马裤。彼得L.是不是傻子喝,使他脸上总是红。面对现实吧,对了,是有点让人想起演员列昂诺夫的。这有一个非常宏伟的人物,在我们极力灌输工作的热爱。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工作室总是开学校后,大家都去那里,做自己的一切,他希望用木头或金属的东西。我也经常有下降 - 锐化机枪他的粘土军队。而一旦一个人 - 年纪比我 - 决定做自己的明星警长在kovboytsev和印度人在院子里玩耍。他应该再由黄铜加工。那么,明星当然 - 六指出。在这部影片中关于印度人谁曾经是。由彼得·L.去。和星突然说。当他抓住了男孩,但他对替补的小脑袋不是抨击和尖叫,“啊,他妈的,那发明!犹太复国主义有滋生!我会他妈的,导演吧!“当然,我们都吓坏了所有。没有什么无法理解。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最重要的是,他被吓得当然谁磨星的男孩。在一般情况下,我记得从那时起警长的六个五角星最好不要磨。
而可笑的是在我们学校的教官是雅科夫莱维特。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辣味,然后我不明白。但我仍指着自己说,我们离不开三人组 - 劳动派,“铅笔”(美术老师),我们的物理学家斯大林(总是作为饮料,喜欢谈论斯大林)保持永远在一起,永远酒和教官不停地远离他们,不喝酒。然而,奇怪的不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彼得·L.和军事主任雅科夫一个战士带我们波罗底诺领域,类似的纪念碑。和所有他的掩体,这也是一个射击场和各种其他有趣的zagashnike非常美在高中像。和Peter L.,但是,把我们带到了工作和休息,在辛菲罗波尔的营地,在那里拨款由我们赚的一部分钱(我们其实一百卢布给双手近两个月,所以充满了喜悦裤子)。好吧,这件事情我离题。
我也不断地为孩子在任何体育俱乐部或步行俱乐部。也就是说田径,皮划艇,甚至 - 在先锋和学童的中央宫陶瓷
更多夏令营课程。但在这里一切都清楚了。游戏voynushki,白色和红色,德国人自己。我,顺便说一句,这些比赛总是发挥白色。我喜欢绷得很紧白片,涣散红人不喜欢。尤其是多少,我尊敬的队长奥韦奇金,并模仿他的游戏,直到难忘的蜱(宫颈)。在一个阵营,我当选为单位的承载。很多我喜欢这个东西 - 先走组。事实是不是很超前。的第一指挥官去了。但他身后的旗手权利。但他爱,当面对一些什么庄严日子承载特别准备,并分别收集:“火炬手团体聚集在先锋房”朋友于是故意惹恼了:“啊,再说了这样的横幅去排练,”和灵魂本身是好的 - 旗手支队。不只是因为!
在晚上的电影,然后跳舞。电影上的所有旧的选择,这样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即使你坐在扬声器本身附近。舞哦。每个人都“的女孩”。虽然不承认,但还是跳舞,只邀请每个 - “他们”。而当她被邀请的女孩,让他的头的广告 - 一个半圈到左边由下向上,并翻了个白眼,说:“好无聊再次那些愚蠢的舞蹈。”一次舞蹈先驱距离 - 也就是说,当你的手周围像匹诺曹捉襟见肘。推自己?你是什么!多一点我们。一位资深队肯定压。嗯,当然晚上的恐怖故事。同样,女孩晚上粘贴涂抹必要的。然而,他们也受膏。和女孩甚至更好吧。狡猾的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在去先锋了几天露营帐篷。和天气为雨天,讨厌。但是,我们吃,因为这个领域有厨房。而一旦太阳出来吃饭前 - 只是有乐趣的灵魂。然后,厨师给我和另外三个家伙说,“就拿锅炉把水在里面。”在野战炊事锅炉 - 像煤气罐卡车,但辉煌。好吧,我们采取了拖。和去村里的列。我不得不去绕过路上,因为直躺在白菜领域。嗯,一列我们四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空锅炉。我们斟。就拿 - 他混蛋,不升。好了,疯了沉重。什么都不做,半年抛。不管怎样沉重。更多的演员。在一般情况下,它留下多少能够拖动 - 我们12年的地方,不是运动员,坦率地说 - 那就是,几乎在最底层。然后再想如何去。在路上绕过很远。我们决定用白菜场直收。尽管这一切,白菜,等机会来拖动锅炉是不可见的。 Napryamki淹没。和白菜已经是巨大的。而雨只在上午。所有的湿场,但仍然每卷心菜,片,一升水两个或三个。在这里,我们通过实地prёmsya,敲白菜和水倒在我们。在所有的污垢,像魔鬼。我笑了,没有节制。我们中的一个说:“我们将带来的,刚好够到设备的水域洗泥”。
来源:
1972年。阿尔巴特。附近的房子一个学号命名59。果戈理。但我的母亲给了我在学校的一个小盒子№58与深入研究德国(大中华区Afanasyevsky车道)。现在,学校是不是。和建筑被拆毁,以及学校的数量,这是建立在它的地方,改变。好吧,无所谓。因此,德国的特殊学校。语言开始从二年级学习。
我们如何生活?是的,通常。钢材十月党。在课堂上挂着“明星”画上的滤纸片和胶合的照片“链轮”成员的光芒。星星的指挥官改变周围 - 一周第二个星期,等我喜欢它,当轮到我是司令“链轮”。并不太喜欢它,当指挥官成为某种类型的女孩。
长凳我们的样本老体育馆,有斜面的顶部和...什么是叫这些木制的“门”被抛弃的时候,有必要摆脱党?如此之大,要拍自己的办公桌。并利用这些政党,也这是伟大的。
在从他的课德语课,我们去到顶部,“资深”地板。一旦在比赛中,我发现这是描绘斗争的吸墨纸:未知的弟子描绘战斗甲虫毛毡,毛毡屋顶还是一些东西。然后我的朋友和我不断尝试重现正是这种模式。
有一段时间,我去prodlёnku。在prodlёnke很有趣。一旦所有的课都做,每个人做他想要的东西。该女孩在一个圆圈,由纸型木偶戏任何假期都忙不停。主要是它是狼(该剧是有关的东西有多少狼在那里)。
但更多的时候,我放学后回家。并迅速取得的经验教训跑到街上。我们在街上游荡的朋友,爬在阁楼,屋顶,“森林”正在维修的建筑物,建筑物,车库。有一次,当我们坐在车库的屋顶和谈论的东西,一个人走了过去。我们赶上了他的左膀右臂制造“枪”,他瞄上了我们,说,“KKY!”然后眨眨眼睛,一边往前走着。和我们中的一个说,“你看到了吗?这是Vitsin!“Vitsin!然而,同样的makarom我看到尤里索洛明。在学校附近№59摄制的“路各各”我们一个小插曲 - 我们的孩子,和所有的邻国庭院 - 虔诚地看着他的大人,谁向我们走来的副官 - 在白卫队的形式(如我们当时以为) - 和说:“伙计们,走开,不要打扰,这里电影»设置。
阿May 9日,一个女孩的父亲所有的孩子带了一副肩章陆军中尉和我们把他们 - 真正的追! - 为了他的白衬衫,在他的头上,我们有蓝帽子“里拉”,这是“几乎像真实的东西。”而且我们展示的东西在舞台上。然后去在这个形式的步行路程。而且他们相信,我们都很羡慕。依旧会!我们有真正的肩章!
有时,用类我们去别的地方,例如,木偶Obraztsova。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的,很多有关。例如,我记得我的朋友和我Genka季托夫,如在深夜走过教堂,并开始谈论上帝。奇怪的是,我们争先恐后愤慨地说,由于它是如此的论文,没有神,当它是明确的傻瓜,他是。在这里,我们有过,年轻的1973年10月?该教堂有目前为Philippovsky胡同。
阿尔巴特小巷,同时逐步从老房子纯化。在1974年我们得到一个订单,我们搬进了新房子。我们被拆迁。在因为儿童在汽车的轮子掉落的高比例的新领域是一种学校系统配置:孩子不得不写信给学校未马路对面进行的方式。但是,妈妈送我去上学,这导致在街对面的方式,因为这是一所学校,他在那里学习德语。我记得,当我不得不打电话家庭住址,不知何故,我总觉得惭愧,我是“在错误的街上»。
此系统的配置,但是,不会被保存。当我们在四年级,一个男孩被打死。他直接在路边骑自行车。后轮脱落,自行车打滑,他倒在马路上。我回去带轮机。男孩下跌如此厉害,车轮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开车垃圾桶,那么这使他从字面上扁平头。于是他和埋葬,具有封闭头。我们跑了葬礼。然后,总是在屋前的葬礼,他们说了再见,乐队演奏,人们在哭。奇怪,但由于某些原因我还记得葬礼乐团的声音往往是在这里和那里听到的。在阿尔巴特我不记得了。
在三年级,我们学到的第二个转变。这是伟大的,因为它没有早起。一切都在学习,你还是在家里。而当你回来的学校是很空的。事实是不愉快的,当你学习,都在家里。在B类在课堂上,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楼,收集几乎所有的地方恶霸。然后,五人在这个类去坐牢(毕业后,当然),但在一般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班级男生去职业学校8日之后。
在三年级,我们在街上游荡。这是真的有一点不同的景观 - 不在家,但与此相反,几乎农村,虽然莫斯科。铅熔化起火,拍摄弹弓。一经推出就斯大林的乡间别墅,这是位于附近的其他袭击。他们爬上围栏。不知何故里面真正zarobeli剥离。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被抓到有会发生什么。
我有一个嗜好:由粘土城池和士兵雕塑。渐渐地,我获得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哦,我们安排了战斗。这种持续的迷恋一直到9年级。在了解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同学提出我们笑,如玩玩具士兵孩子。不过,很快从机构,我们了解到,他们自己在同一时刻在所有的木偶戏。然而,有些东西我向前跑。
我还喜欢阅读。区图书馆长的步行,试图去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基本上有一个关于创业英雄阴霾。一位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你看,你正在寻找一本书这么仔细,我想帮你”,并从一本厚厚的书由杰克·伦敦的表中删除给了我。我惊呆了杰克·伦敦没有那么多,从他对我来说,五年级说,给你。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以变得有趣。
更多我喜欢骑在博罗季诺全景,自小大力推崇拿破仑和一切与它连接。该博罗季诺全景我独自,与朋友和可能是一百倍。嗯,当然,我们去看电影。当然,我们走。走着走着,顺带也主要集中在建筑。在保护的时间,因为这样的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而不是在黑暗中爬在施工现场,爬上那里为推土机,挖掘机和起重机?在冬季,当然各种古怪的冬季娱乐。我记得,比如,像我们在山坡旁的道路修建了雪堡,并发射雪球从那里路过的车。一车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追我们。哦,我们什么斯基达德尔!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开始阅读“基度山恩仇记”,抓住冰淇淋。到了晚上,气温有所上升。生根喜爱。这太酷了 - 没必要去上学。每个人都在学校,和你回家baldeesh。当然,虽然,不喜欢吃药。而躺在床上不喜欢。
在学校里,课间休息,我们以“冲”总是带回家橙色的膝盖从磨在走廊地板上的胶泥。然后,他们开始玩捉迷藏。其中一个楼梯莫名其妙总是被关闭,我们必须改变渗透和播放,从地面跃起到地面。由于目前还没有什么突破 - 仍然不知道。尤其是当你考虑到领导跃升蒙住眼睛。
更多玩“大富翁”。事实并非如此,和自制。和金钱将借鉴。那么,在咀嚼口香糖包装纸太的过程。
我们的德语教师带领KID - 国际友谊俱乐部。有时她在那里中央KID派了几个人到先锋在列宁山宫殿。在先锋的宫殿,我们收到的信封从外国人谁想要与苏联的先驱对应。当然,外国人分别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我相当于一个波兰和一个德国人。德国罗兰命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罗腾堡的一些在他的两层楼的房子有五六个房间。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他的祖父参加过战争和死亡。我给他写了回来,我爷爷也转战来到所有伤员;信中问道:“哪里是你爷爷死了?”大多数德国人我还没有收到一个字母。波兰人还对应关系也相当迅速消退。说实话,我有点不是很感兴趣,对应他们。好了,我们互送明信片,以及讲述了家庭。还有什么?
一个同学决定把国际友谊的事情在商业基础上。他在KID以先锋宫沉溺于自己,拿起外国人的信,表面上是为了拿学校,他拿出日历,明信片和任何改变。然后,他抓住了它。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会议只进行“交易”。
和一个女孩(虽然不是来自我的课)对应了与罗马尼亚。一个罗写信给她:“送我一些紧身衣。”女孩开始思考:是什么意思罗马尼亚?毕竟,那么肯定我们甚至不能认为罗马尼亚要求送她最普通的运动裤。在一般情况下,所以我不觉得这个女孩打断了谈话。并不知我在罗马尼亚还是遗憾,她一直在等待来自苏联的紧身衣,可能。
嗯,这是一个童年是正常的。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主题。也就是说,当然,这是以前的,但不知何故不是很浮夸。并于1975年在库图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的房子正好相反,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开了一个石碑。不知怎的,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们会继续增加。我还记得,在1977年我去了五月在公交车上。当然,作为一个粗略的先驱我假装看窗外,并没有注意到。是的,我承认,我没有屈服的地方老男人和女人。而且我并不孤独。它曾经是先驱者的行为常见70年代一般规则(这甚至微型“混乱”是)。那么,在一般食品。然后我开始推人。我看到 - 老将。嗯,当然我有。他开始说:“看,坐,我喜欢你的泻血。”然后我得到了邪恶的,我把他的额头:“对我来说,血爷爷流下,因为他早已死于枪伤”老将几乎哽咽着愤慨。
你知道,我不记得他们的同龄人对退伍军人一些特殊的崇敬之情。它被认为由我们枯燥的整体性能的一部分。啊,5月9日好,那么就必须把学校设置的诗句,有必要邀请老兵,倾听他们告诉我们。它的枯燥和不感兴趣。如果我有一个人说,早在70年代末,我坐在在这些会议上专门纪念日的兴趣,那么我将被迫指责伪善的人。在所有的会议,我们从下枝收集。
然而,我记得 - 尽管它后来,在今年'81 - 从帆布帽子我唯一的女朋友缝补衣服,头饰是非常相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步兵。哦,我砍通过它。可惜的照片也无法生存。然后我给丑化另外一个,他带走了老师 - 喜欢,“你几乎法西斯恶棍戴帽子?”教室是他的盖帽。然而,我又往前跑。
我也第一次在学校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训。它是如此。我们的劳动派叫彼得L. Krasnobryzhev。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名字来源于他的父亲(或祖父),曾在红军和谁被授予红色马裤。彼得L.是不是傻子喝,使他脸上总是红。面对现实吧,对了,是有点让人想起演员列昂诺夫的。这有一个非常宏伟的人物,在我们极力灌输工作的热爱。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工作室总是开学校后,大家都去那里,做自己的一切,他希望用木头或金属的东西。我也经常有下降 - 锐化机枪他的粘土军队。而一旦一个人 - 年纪比我 - 决定做自己的明星警长在kovboytsev和印度人在院子里玩耍。他应该再由黄铜加工。那么,明星当然 - 六指出。在这部影片中关于印度人谁曾经是。由彼得·L.去。和星突然说。当他抓住了男孩,但他对替补的小脑袋不是抨击和尖叫,“啊,他妈的,那发明!犹太复国主义有滋生!我会他妈的,导演吧!“当然,我们都吓坏了所有。没有什么无法理解。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最重要的是,他被吓得当然谁磨星的男孩。在一般情况下,我记得从那时起警长的六个五角星最好不要磨。
而可笑的是在我们学校的教官是雅科夫莱维特。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辣味,然后我不明白。但我仍指着自己说,我们离不开三人组 - 劳动派,“铅笔”(美术老师),我们的物理学家斯大林(总是作为饮料,喜欢谈论斯大林)保持永远在一起,永远酒和教官不停地远离他们,不喝酒。然而,奇怪的不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彼得·L.和军事主任雅科夫一个战士带我们波罗底诺领域,类似的纪念碑。和所有他的掩体,这也是一个射击场和各种其他有趣的zagashnike非常美在高中像。和Peter L.,但是,把我们带到了工作和休息,在辛菲罗波尔的营地,在那里拨款由我们赚的一部分钱(我们其实一百卢布给双手近两个月,所以充满了喜悦裤子)。好吧,这件事情我离题。
我也不断地为孩子在任何体育俱乐部或步行俱乐部。也就是说田径,皮划艇,甚至 - 在先锋和学童的中央宫陶瓷
更多夏令营课程。但在这里一切都清楚了。游戏voynushki,白色和红色,德国人自己。我,顺便说一句,这些比赛总是发挥白色。我喜欢绷得很紧白片,涣散红人不喜欢。尤其是多少,我尊敬的队长奥韦奇金,并模仿他的游戏,直到难忘的蜱(宫颈)。在一个阵营,我当选为单位的承载。很多我喜欢这个东西 - 先走组。事实是不是很超前。的第一指挥官去了。但他身后的旗手权利。但他爱,当面对一些什么庄严日子承载特别准备,并分别收集:“火炬手团体聚集在先锋房”朋友于是故意惹恼了:“啊,再说了这样的横幅去排练,”和灵魂本身是好的 - 旗手支队。不只是因为!
在晚上的电影,然后跳舞。电影上的所有旧的选择,这样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即使你坐在扬声器本身附近。舞哦。每个人都“的女孩”。虽然不承认,但还是跳舞,只邀请每个 - “他们”。而当她被邀请的女孩,让他的头的广告 - 一个半圈到左边由下向上,并翻了个白眼,说:“好无聊再次那些愚蠢的舞蹈。”一次舞蹈先驱距离 - 也就是说,当你的手周围像匹诺曹捉襟见肘。推自己?你是什么!多一点我们。一位资深队肯定压。嗯,当然晚上的恐怖故事。同样,女孩晚上粘贴涂抹必要的。然而,他们也受膏。和女孩甚至更好吧。狡猾的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在去先锋了几天露营帐篷。和天气为雨天,讨厌。但是,我们吃,因为这个领域有厨房。而一旦太阳出来吃饭前 - 只是有乐趣的灵魂。然后,厨师给我和另外三个家伙说,“就拿锅炉把水在里面。”在野战炊事锅炉 - 像煤气罐卡车,但辉煌。好吧,我们采取了拖。和去村里的列。我不得不去绕过路上,因为直躺在白菜领域。嗯,一列我们四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空锅炉。我们斟。就拿 - 他混蛋,不升。好了,疯了沉重。什么都不做,半年抛。不管怎样沉重。更多的演员。在一般情况下,它留下多少能够拖动 - 我们12年的地方,不是运动员,坦率地说 - 那就是,几乎在最底层。然后再想如何去。在路上绕过很远。我们决定用白菜场直收。尽管这一切,白菜,等机会来拖动锅炉是不可见的。 Napryamki淹没。和白菜已经是巨大的。而雨只在上午。所有的湿场,但仍然每卷心菜,片,一升水两个或三个。在这里,我们通过实地prёmsya,敲白菜和水倒在我们。在所有的污垢,像魔鬼。我笑了,没有节制。我们中的一个说:“我们将带来的,刚好够到设备的水域洗泥”。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