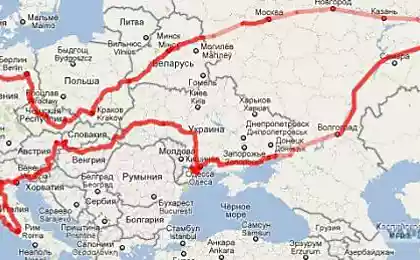504
这一天我废话。
1977年。我趴在SVD,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缓存。更确切地说 - 扎伊尔共和国。像,当她打电话。说谎和最拥护党和政府的不干预政策,即,假装我们这里真的不是:马克杯彩绘山水,光学封顶。在右侧仪表的机枪手,甚至在你的屁股布什prikopat。美纹优雅,如果不是短语偶尔交换自己相信任何人在这里。我能说什么,一个家庭的疣猪并不传递给我们的,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非洲“妓女”的字面吓得他们半米我们的头盔。
除等待八小时。而不是事实,就会出现。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把“虫”了一个小时。如果有人不知道 - 机械闹钟,定时启动的旧洗衣机,静静的嗡嗡声和振动在约定的时间。小睡了一小时,由一对垫的传播忽视的地方 - 然后再次沉默
我打瞌睡,梦中,我记得,在SP66传奇狭窄的圈子里,然后我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肩膀,轻轻地使纯俄语,痛斥:
- Odnokursnichek,帽,掩饰,不发光
!
主啊,我搞砸了。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躺下五分钟,他踢了他的伙伴,谁甚至没有醒来。如果可能的话,很快,谨慎地离开了照明角度。对象,顺便说一下,那天没去,然后换另一年勃列日涅夫祝贺所有苏联的假期。
从那以后,我每年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的团聚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名字命名的,仔细凝视着白齿微笑的同学。然后我喝醉了垃圾和可怕的黑色从前的学生持久请求从黄棕色包抽一根烟跟我不时“联盟 - 阿波罗”。为了这一天向前,任何人hohotnёt,并承认同十几个香烟,把我的头盔左侧包,仍然使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小故障,那一天,当我搞砸了......
©帽

资料来源:
除等待八小时。而不是事实,就会出现。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把“虫”了一个小时。如果有人不知道 - 机械闹钟,定时启动的旧洗衣机,静静的嗡嗡声和振动在约定的时间。小睡了一小时,由一对垫的传播忽视的地方 - 然后再次沉默
我打瞌睡,梦中,我记得,在SP66传奇狭窄的圈子里,然后我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肩膀,轻轻地使纯俄语,痛斥:
- Odnokursnichek,帽,掩饰,不发光
!
主啊,我搞砸了。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躺下五分钟,他踢了他的伙伴,谁甚至没有醒来。如果可能的话,很快,谨慎地离开了照明角度。对象,顺便说一下,那天没去,然后换另一年勃列日涅夫祝贺所有苏联的假期。
从那以后,我每年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的团聚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名字命名的,仔细凝视着白齿微笑的同学。然后我喝醉了垃圾和可怕的黑色从前的学生持久请求从黄棕色包抽一根烟跟我不时“联盟 - 阿波罗”。为了这一天向前,任何人hohotnёt,并承认同十几个香烟,把我的头盔左侧包,仍然使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小故障,那一天,当我搞砸了......
©帽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