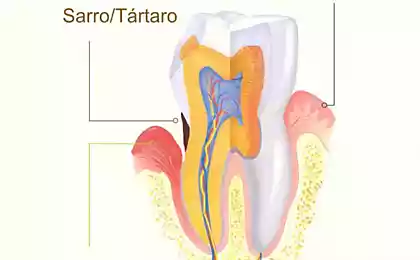1511
保罗·米勒的回归
保罗第一次访问网络中的12年。在14日,他曾作为一个网页设计师。 26累了,决定不上网了一年的生活。再换

我错了。
一年前,我离开了互联网。我以为是我的工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我认为,这没啥意思。我认为他是“破坏了我的灵魂»。
一年已经过去了,因为我“sёrfil在网络上”或“检查邮件”或“laykal”象征性的东西,而不是通常的“大拇指”。我学会了被断开,按计划,我是自由的互联网。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切是如何解决我的问题。我将是开明的,更“真实”。更完美。
事实上,现在晚上8点我就醒了。我睡了一整天,醒来语音邮件来自朋友和同事8条留言。我去了我平时的咖啡厅吃午餐,游戏尼克斯,我的两个文件和纽约人的副本。现在我明白了“玩具总动员”在希望他自己动手写,会产生在我生命中的洞察力,我无法达到合格瞪大了眼,闪烁的光标闪烁的文字赘述。
我不想达到这个保罗在我的年度之旅的终点。
在2012年初我26岁,我很疲惫。我想从现代生活中逃脱 - 传入
的无尽循环 电子邮件,将信息从万维网的不断流动,消音我的理智。我想逃离。
我认为互联网是neestesstvennym状态对我们来说,对人民,或至少对我来说。也许我太沉迷于处理或太冲动来限制自己。我总是利用互联网12年,不能想象我的生活没有他14。我从报童到了网页设计师,然后进行处理,在不到10年的作家(技术作家)。我住的连续性和连接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下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生活提供。 “现实生活”,可以这么说,等我在网络浏览器的另一面。
我的计划是要摆脱工作,搬到他父母的家里,看书,写书,并躺在之间的沙发上。在一举,我会克服一切危机来接近我。我发现这个地方保罗远远超出了噪音,并会成为自己最好的版本。
但由于某些原因,濒临要支付我的互联网服务。我可以留在纽约,并分享他们的发现与全球广播自己的生活不受互联网网民,其塔高分配的智慧。
我作为一个技术作家的目标要知道,互联网对我做了多年。了解互联网,研究它“在距离”。我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会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成为更好的人。一旦我们理解互联网如何败坏了我们,我们终于能够承受这个。
23:59 2012年4月30日我把你的以太网电缆,禁用无线网络连接和更换smarfton一个简单的“拨号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我觉得自由。
几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在人群60000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临时抱佛脚到纽约市的林间空地,由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拉比知道互联网的危险。认真。赛场外,我看到一名男子挥舞着我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的一种呵护。他很高兴能与我见面。我决定远离互联网的原因有很多类似他的信仰,表达对现代世界的关注。
“他重新编程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敏感性,” - 说的拉比之一。 - “它破坏了我们的耐心。原来孩子进入点击蔬菜»。
这一定是惊人的。
我有一个梦想
它开始好了,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有限的自己,有乐趣。我的生活一直充满突发事件:会议,飞盘,周期旅行和希腊文学。如果没有它如何发生的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写了一半他的小说中,几乎每个星期发了一篇文章给的边缘。在我的老板的头几个月中一个我表示轻微的失望,因为我写的,这从来没有发生之前或之后。
在我做出退学15磅没有任何努力。我买了新衣服。人们不停地告诉我,我怎么好看起来,我是多么高兴看着。在其中一项考试,我的治疗师字面上拍了拍自己的后背。
我有点无聊,有点寂寞,但发现在他们的生活奇迹般的变化。在8月,我写道:“无聊和缺乏动力强迫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比如写或花时间与其他人。”我完全相信,我有一切尽在掌握,一切谈论它。
经过我的头清除,增加了注意力。在我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月10页的“奥德赛”是苦役。现在,我可以读一坐100页,如果我轻松阅读着迷,甚至几百个。
我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个想法,为此,小的博客文章,而是一个新的演示文稿的大小。从网络文化的电波暗室已经出现了,我发现我的想法发展新的方向。我觉得不同的,有点古怪,我喜欢它。
从他们最喜爱的智能手机中解脱出来,我只好走出壳艰难的社会局势。事实证明,没有他不断的分心,我更加关注其他人。我再也不能继续在Twitter上的关系 - 我必须找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姐姐以前白白试图说服我,而我是听她的只有一半,现在崇拜我们的谈话。她说,我悬在心理,更能够照顾它 - 好了,我变得不那么白痴比我
此外,我不知道如何将它涉及到了休息,但我哭一边看“孤星泪»。
在那些最初的几个月里,它似乎是我的假设被证实。互联网让我从真正的自我,是最好的,保罗。我坚持叉子插入插座和照明灯。
残酷的现实
当我离开了互联网,我认为我的杂志上的文章会是这样的:“我今天正在使用的纸质地图,它是rzhachno!”或“纸书?这是什么?!“或”有没有人已经下载了维基百科开车吗?“。这并没有发生。
大多数今年的实际问题还没有受到重视。我没有问题,在纽约的方向和在其他地方我一直在购买纸质地图。原来,这纸书真的很不错。我没有比较机票价格,而只是所谓的三角洲,并把他们提供的。
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我所学到的东西,你可以学习如何上网,没有它 - 没有必要去上了一年的网上饮食要认识到你的妹妹有感情
最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帖子。这一年,我开始了一个邮政信箱(12430),我不能告诉你他是多么的快乐带给我的,被堵塞的读者来信。它是有形的东西,而这不能传达的电子明信片。
迷人,字迹工整一个女孩写在这张纸上:“谢谢你从互联网上退休了。”并非是一种侮辱,但作为一种恭维。这封信是很给我。但后来我觉得不好,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响应书。
然后,出于某种原因,甚至前往邮局开始为我工作。我开始害怕了信件,并准备送他们回去。事实证明,一个十几封信每周COG用了一天几百个电子邮件相媲美。因此,这发生在我生活的其他领域。需要好书的动机看是否有互联网作为一种替代与否是我。退出房子的会议与人民要求一样多的勇气,有多少,通常。
在2012年来临之际,我学会了错误的决定以新的方式,没有互联网。我放弃了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寻找新的缺陷。而不是把无聊和缺乏学习动机和创造力,我转向了被动消费与社会隔离的一面。
在新的一年里我没有骑自行车经常发生。我的飞盘收集灰尘。几个星期以来我没有跟人见面。我最喜欢的地方 - 一个沙发。我填补他的脚放在茶几上,玩游戏,听有声读物。我选择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游戏,如无主之地2或3滑板,而我的大脑有声读物,或者干脆沉默下放松。
人们谁是需要其他
所以,道德选择不这么改有没有互联网。对于像纸质地图,购物实事是不是那么难习惯。人们仍然乐意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没有了互联网这是真的很难找到人。拨打电话是比较困难的,而不是发送电子邮件。它更容易发送短信或满足在视频聊天比来有人回家。这并不是说,这些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我克服了这些开头,但未能坚持到底。
这很难说真正发生了变化。我想,那些最初的几个月是如此的好,因为我觉得没有从互联网上的压力。我的自由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当我停下来看看他的情况下生活“,我不使用互联网”,是网络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规,并开始显示我最坏的一面。
我可以留在家里好几天的时间。我的电话就用完了,没有人能找到我。在某些时候,父母累了想不管我有没有,他们就打发我妹妹来我家。在互联网上,很容易让人信服,我活得很好,很容易与同事沟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么多嵌着写嘲笑的虚假概念页的“朋友在Facebook»,但我可以告诉你,”每个Facebook的»聊胜于无。我最好的“朋友在距离”,是唯一一个与我每周都召集了好几年了,搬到了中国,今年,从那以后,我没有说过他。我最好的朋友,谁住在纽约,就融化在我的工作,虽然我不能跟上我们的计划崩溃。
我放弃了生命的流动。
今年三月,我讽刺地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被称为“理论化万维网”。这是充满研究生和其他科学家对看起来像女性主义在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现实的定义复杂报表行事。起初我有点飘飘然,因为我认为他们只处理理论意味着互联网在旁边,虽然我是学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在我跟内森Jurgenson(弥敦道Jurgenson),一个理论家谁协助筹办会议。他提请注意的是,有许多虚拟的“真实”,是充满了真正的“虚拟”。当我们使用手机或电脑,我们依然有血有肉的人,占用空间和时间。当我们我们在该领域的地方跳过,下降从他们的小玩意某个遥远,互联网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Tvitnu这件事时,我回去?”。
我的计划是要离开互联网,从而找到“真正的”保罗,请与“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但真正的保罗和现实世界已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我不是说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拒绝改变,而事实上,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家庭时间
几个星期前我去科罗拉多与他的兄弟,以满足之前,它移动到卡塔尔与空军。他有一个小的孩子,五个月polnoschёchka命名KASIA(Kacia),我看到了只有在通过邮寄到我的嫂子亲切地发送照片。我和我的兄弟花了一天,他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机场。惊呆了,我看着他吻别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是不公平的,他不得不离开。他是一个英雄,他的孩子,我讨厌的事实,他将不得不离开他们6个月。
我的同事斯蒂芬·乔丹和我会见了在科罗拉多州去在客场之旅回到纽约。当时的想法是压缩在一个小的纪录片我多年,并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对发生在我身上的讨论,什么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花了一点时间与孩子,试图尽全力帮助他的嫂子,是超的叔叔。然后,我们不得不离开。
在路上,约旦和斯蒂芬问我问题。 “你觉得你太辛苦自己呢?” - “是的。” “这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一年?” - “号” “你要什么,当您返回到Internet做什么?” - “我想尝试其他»
。
我们在亨廷顿,西弗吉尼亚州做了一个站,以满足我的英雄,多边形的贾斯汀·麦克尔罗伊(贾斯汀·麦克尔罗伊)。我遇到了内森Jurgenson在华盛顿举行。我想了很多我能做什么以及在网络中的那些东西在它被击败。我问的意见。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能责怪互联网,或任何情况下我的问题。我仍然有我的许多重点,我必须照顾:家人,朋友,工作和培训。我不能保证我会坚持他们的回报 - 最有可能的,不会,是诚实的。但至少我知道,互联网是不是责备。我会知道谁是负责一切,谁可以修复它。
周二,我们此行的最后一晚,我们停止了从纽约流向取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图片Manhettenovskogo天际线的河。这是一个寒冷,晴朗的夜晚,我靠在桥站不住脚的栏杆,并试图采取拍摄一个舒适的位置。我是如此接近纽约,因此接近完成。我渴望他的公寓宁静的孤独和有点害怕回去隔离。两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互联网。我觉得自己打败了。我觉得我又放下了手。但我知道,互联网 - 这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
中午12点,2013年5月1日
我看了很多博客文章,杂志文章和书籍互联网让我们寂寞,或愚蠢,或愚蠢的,孤独的,一旦他开始相信他们。我想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对我做了,”我无法抗拒。但是,互联网 - 它不是个人的比赛,它的东西,大家一起做,对方。互联网里的人都。
在我在科罗拉多州的最后一天,我旁边,他的五年侄女Kazayey坐了下来(Keziah,哦,这些名字 - 约每),并试图向她解释什么是互联网。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很多在Skype上谈论与他们的祖父母。我问她是否有兴趣,为什么今年我没叫她在Skype上。她感兴趣的
“我还以为你不想” - 她说
。 随着泪水在他的眼里,我画了她,什么互联网。提请计算机,电话和电视机与细线连接它们。 “这些线 - 互联网”我给她看了我的电脑上画一条线,并删除它。
“我花了一年时间,而无需使用互联网” - 我对她说。 - “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给你回电话»
。 当我上网,我可能不会正确地使用它。也许我会采取分散注意力的时间或不要点击这些链接。我不会有太多的时间阅读,写作或自伟大的美国科幻小说。
但至少我会和你联系。
来源您的文字链接...

我错了。
一年前,我离开了互联网。我以为是我的工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我认为,这没啥意思。我认为他是“破坏了我的灵魂»。
一年已经过去了,因为我“sёrfil在网络上”或“检查邮件”或“laykal”象征性的东西,而不是通常的“大拇指”。我学会了被断开,按计划,我是自由的互联网。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切是如何解决我的问题。我将是开明的,更“真实”。更完美。
事实上,现在晚上8点我就醒了。我睡了一整天,醒来语音邮件来自朋友和同事8条留言。我去了我平时的咖啡厅吃午餐,游戏尼克斯,我的两个文件和纽约人的副本。现在我明白了“玩具总动员”在希望他自己动手写,会产生在我生命中的洞察力,我无法达到合格瞪大了眼,闪烁的光标闪烁的文字赘述。
我不想达到这个保罗在我的年度之旅的终点。
在2012年初我26岁,我很疲惫。我想从现代生活中逃脱 - 传入
的无尽循环 电子邮件,将信息从万维网的不断流动,消音我的理智。我想逃离。
我认为互联网是neestesstvennym状态对我们来说,对人民,或至少对我来说。也许我太沉迷于处理或太冲动来限制自己。我总是利用互联网12年,不能想象我的生活没有他14。我从报童到了网页设计师,然后进行处理,在不到10年的作家(技术作家)。我住的连续性和连接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下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生活提供。 “现实生活”,可以这么说,等我在网络浏览器的另一面。
我的计划是要摆脱工作,搬到他父母的家里,看书,写书,并躺在之间的沙发上。在一举,我会克服一切危机来接近我。我发现这个地方保罗远远超出了噪音,并会成为自己最好的版本。
但由于某些原因,濒临要支付我的互联网服务。我可以留在纽约,并分享他们的发现与全球广播自己的生活不受互联网网民,其塔高分配的智慧。
我作为一个技术作家的目标要知道,互联网对我做了多年。了解互联网,研究它“在距离”。我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会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成为更好的人。一旦我们理解互联网如何败坏了我们,我们终于能够承受这个。
23:59 2012年4月30日我把你的以太网电缆,禁用无线网络连接和更换smarfton一个简单的“拨号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我觉得自由。
几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在人群60000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临时抱佛脚到纽约市的林间空地,由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拉比知道互联网的危险。认真。赛场外,我看到一名男子挥舞着我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的一种呵护。他很高兴能与我见面。我决定远离互联网的原因有很多类似他的信仰,表达对现代世界的关注。
“他重新编程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敏感性,” - 说的拉比之一。 - “它破坏了我们的耐心。原来孩子进入点击蔬菜»。
这一定是惊人的。
我有一个梦想
它开始好了,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有限的自己,有乐趣。我的生活一直充满突发事件:会议,飞盘,周期旅行和希腊文学。如果没有它如何发生的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写了一半他的小说中,几乎每个星期发了一篇文章给的边缘。在我的老板的头几个月中一个我表示轻微的失望,因为我写的,这从来没有发生之前或之后。
在我做出退学15磅没有任何努力。我买了新衣服。人们不停地告诉我,我怎么好看起来,我是多么高兴看着。在其中一项考试,我的治疗师字面上拍了拍自己的后背。
我有点无聊,有点寂寞,但发现在他们的生活奇迹般的变化。在8月,我写道:“无聊和缺乏动力强迫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比如写或花时间与其他人。”我完全相信,我有一切尽在掌握,一切谈论它。
经过我的头清除,增加了注意力。在我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月10页的“奥德赛”是苦役。现在,我可以读一坐100页,如果我轻松阅读着迷,甚至几百个。
我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个想法,为此,小的博客文章,而是一个新的演示文稿的大小。从网络文化的电波暗室已经出现了,我发现我的想法发展新的方向。我觉得不同的,有点古怪,我喜欢它。
从他们最喜爱的智能手机中解脱出来,我只好走出壳艰难的社会局势。事实证明,没有他不断的分心,我更加关注其他人。我再也不能继续在Twitter上的关系 - 我必须找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姐姐以前白白试图说服我,而我是听她的只有一半,现在崇拜我们的谈话。她说,我悬在心理,更能够照顾它 - 好了,我变得不那么白痴比我
此外,我不知道如何将它涉及到了休息,但我哭一边看“孤星泪»。
在那些最初的几个月里,它似乎是我的假设被证实。互联网让我从真正的自我,是最好的,保罗。我坚持叉子插入插座和照明灯。
残酷的现实
当我离开了互联网,我认为我的杂志上的文章会是这样的:“我今天正在使用的纸质地图,它是rzhachno!”或“纸书?这是什么?!“或”有没有人已经下载了维基百科开车吗?“。这并没有发生。
大多数今年的实际问题还没有受到重视。我没有问题,在纽约的方向和在其他地方我一直在购买纸质地图。原来,这纸书真的很不错。我没有比较机票价格,而只是所谓的三角洲,并把他们提供的。
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我所学到的东西,你可以学习如何上网,没有它 - 没有必要去上了一年的网上饮食要认识到你的妹妹有感情
最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帖子。这一年,我开始了一个邮政信箱(12430),我不能告诉你他是多么的快乐带给我的,被堵塞的读者来信。它是有形的东西,而这不能传达的电子明信片。
迷人,字迹工整一个女孩写在这张纸上:“谢谢你从互联网上退休了。”并非是一种侮辱,但作为一种恭维。这封信是很给我。但后来我觉得不好,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响应书。
然后,出于某种原因,甚至前往邮局开始为我工作。我开始害怕了信件,并准备送他们回去。事实证明,一个十几封信每周COG用了一天几百个电子邮件相媲美。因此,这发生在我生活的其他领域。需要好书的动机看是否有互联网作为一种替代与否是我。退出房子的会议与人民要求一样多的勇气,有多少,通常。
在2012年来临之际,我学会了错误的决定以新的方式,没有互联网。我放弃了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寻找新的缺陷。而不是把无聊和缺乏学习动机和创造力,我转向了被动消费与社会隔离的一面。
在新的一年里我没有骑自行车经常发生。我的飞盘收集灰尘。几个星期以来我没有跟人见面。我最喜欢的地方 - 一个沙发。我填补他的脚放在茶几上,玩游戏,听有声读物。我选择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游戏,如无主之地2或3滑板,而我的大脑有声读物,或者干脆沉默下放松。
人们谁是需要其他
所以,道德选择不这么改有没有互联网。对于像纸质地图,购物实事是不是那么难习惯。人们仍然乐意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没有了互联网这是真的很难找到人。拨打电话是比较困难的,而不是发送电子邮件。它更容易发送短信或满足在视频聊天比来有人回家。这并不是说,这些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我克服了这些开头,但未能坚持到底。
这很难说真正发生了变化。我想,那些最初的几个月是如此的好,因为我觉得没有从互联网上的压力。我的自由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当我停下来看看他的情况下生活“,我不使用互联网”,是网络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规,并开始显示我最坏的一面。
我可以留在家里好几天的时间。我的电话就用完了,没有人能找到我。在某些时候,父母累了想不管我有没有,他们就打发我妹妹来我家。在互联网上,很容易让人信服,我活得很好,很容易与同事沟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么多嵌着写嘲笑的虚假概念页的“朋友在Facebook»,但我可以告诉你,”每个Facebook的»聊胜于无。我最好的“朋友在距离”,是唯一一个与我每周都召集了好几年了,搬到了中国,今年,从那以后,我没有说过他。我最好的朋友,谁住在纽约,就融化在我的工作,虽然我不能跟上我们的计划崩溃。
我放弃了生命的流动。
今年三月,我讽刺地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被称为“理论化万维网”。这是充满研究生和其他科学家对看起来像女性主义在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现实的定义复杂报表行事。起初我有点飘飘然,因为我认为他们只处理理论意味着互联网在旁边,虽然我是学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在我跟内森Jurgenson(弥敦道Jurgenson),一个理论家谁协助筹办会议。他提请注意的是,有许多虚拟的“真实”,是充满了真正的“虚拟”。当我们使用手机或电脑,我们依然有血有肉的人,占用空间和时间。当我们我们在该领域的地方跳过,下降从他们的小玩意某个遥远,互联网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Tvitnu这件事时,我回去?”。
我的计划是要离开互联网,从而找到“真正的”保罗,请与“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但真正的保罗和现实世界已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我不是说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拒绝改变,而事实上,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家庭时间
几个星期前我去科罗拉多与他的兄弟,以满足之前,它移动到卡塔尔与空军。他有一个小的孩子,五个月polnoschёchka命名KASIA(Kacia),我看到了只有在通过邮寄到我的嫂子亲切地发送照片。我和我的兄弟花了一天,他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机场。惊呆了,我看着他吻别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是不公平的,他不得不离开。他是一个英雄,他的孩子,我讨厌的事实,他将不得不离开他们6个月。
我的同事斯蒂芬·乔丹和我会见了在科罗拉多州去在客场之旅回到纽约。当时的想法是压缩在一个小的纪录片我多年,并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对发生在我身上的讨论,什么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花了一点时间与孩子,试图尽全力帮助他的嫂子,是超的叔叔。然后,我们不得不离开。
在路上,约旦和斯蒂芬问我问题。 “你觉得你太辛苦自己呢?” - “是的。” “这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一年?” - “号” “你要什么,当您返回到Internet做什么?” - “我想尝试其他»
。
我们在亨廷顿,西弗吉尼亚州做了一个站,以满足我的英雄,多边形的贾斯汀·麦克尔罗伊(贾斯汀·麦克尔罗伊)。我遇到了内森Jurgenson在华盛顿举行。我想了很多我能做什么以及在网络中的那些东西在它被击败。我问的意见。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能责怪互联网,或任何情况下我的问题。我仍然有我的许多重点,我必须照顾:家人,朋友,工作和培训。我不能保证我会坚持他们的回报 - 最有可能的,不会,是诚实的。但至少我知道,互联网是不是责备。我会知道谁是负责一切,谁可以修复它。
周二,我们此行的最后一晚,我们停止了从纽约流向取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图片Manhettenovskogo天际线的河。这是一个寒冷,晴朗的夜晚,我靠在桥站不住脚的栏杆,并试图采取拍摄一个舒适的位置。我是如此接近纽约,因此接近完成。我渴望他的公寓宁静的孤独和有点害怕回去隔离。两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互联网。我觉得自己打败了。我觉得我又放下了手。但我知道,互联网 - 这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
中午12点,2013年5月1日
我看了很多博客文章,杂志文章和书籍互联网让我们寂寞,或愚蠢,或愚蠢的,孤独的,一旦他开始相信他们。我想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对我做了,”我无法抗拒。但是,互联网 - 它不是个人的比赛,它的东西,大家一起做,对方。互联网里的人都。
在我在科罗拉多州的最后一天,我旁边,他的五年侄女Kazayey坐了下来(Keziah,哦,这些名字 - 约每),并试图向她解释什么是互联网。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很多在Skype上谈论与他们的祖父母。我问她是否有兴趣,为什么今年我没叫她在Skype上。她感兴趣的
“我还以为你不想” - 她说
。 随着泪水在他的眼里,我画了她,什么互联网。提请计算机,电话和电视机与细线连接它们。 “这些线 - 互联网”我给她看了我的电脑上画一条线,并删除它。
“我花了一年时间,而无需使用互联网” - 我对她说。 - “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给你回电话»
。 当我上网,我可能不会正确地使用它。也许我会采取分散注意力的时间或不要点击这些链接。我不会有太多的时间阅读,写作或自伟大的美国科幻小说。
但至少我会和你联系。
来源您的文字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