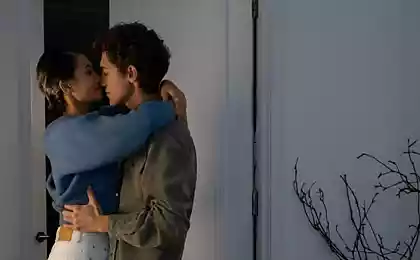625
摄影记者伊戈尔*加夫里洛夫:生命措手不及
伊戈尔*加夫里洛夫–一个活着的传奇的苏联新闻摄影。 他的工作是令人惊叹,每个照片是生活,不被复盖,以及猝不及防。 许多辉煌的照片提交人没有公布在的时间仅仅是因为他太可信。
对于伊戈尔主流的分析报告。 主要目的工作拍摄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搜索其他曾在俄罗斯,曾在50个国家拍摄的几乎所有的热点的国家,在七天之后爆炸,飞越了反应器的切尔诺贝利。
专业精神、热爱他们的工作,并正确的原则所做工作的伊戈尔*重要的和得到国际承认。 摄影师的图片,发表在国际杂志:巴黎Matsh Le照片,斯特恩,Spiegel,独立的,艾丽,发挥男孩和其他许多人。 提名的标题是"最好的摄影师一年的"时代杂志。 获胜者的世界新闻照片奖。
在版的"俄罗斯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时50镜头的拍摄者在不同时期的生活–从学生年的到最近在世界各地旅行。 伊戈尔讲的每个画面−简而言之,地方详细说明,但是某个地方,并与离题纳入更一般的主题。
它变成了一个伤感的故事,迫使以看看照片的相当不同的角度。
公共
晚的80-90年代初。 社区。 看起来像一个装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那里建造的临时peregorodki描绘了一些生活。 但它是一个真正的公寓。
我被要求采取主题的社区。 我不是在这个公寓是,和紧张我所有的朋友谁知道或有朋友住在社区公寓。 但是,这绝对让我吃惊。 在该框架的一个双人间一个家庭。 那个角落坐着一个母亲,我们脚下是她的女儿,非常可爱。 他们只是razmorozili这个大房间里胶合板分区彼此分离。 但razmorozili不到天花板上,而中间,因此有可能爬上这座墙,并从那里来做出这样一个框架。 记住,灰尘的是不是擦了,我认为,六个月或一年,我的眼泪出的整体在某些网、灰尘、边界。
一个时代的象征
我们有足够的住年前,当人们来到店里看见绝对是空架子。 这是开始第90或第89.
"你去哪里了吗?"
框架的最不幸的命运。 我做了它在乌克兰西部,在Ivano-Frankivsk的。 在那些日子里,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人从苏联集团,大量的记者。 我去新闻中心的酒店看到这个场景在巴士站。 只是有几次点击。 我被攻击的一些军队,开始喊到整个Ivano-Frankivsk,我诽谤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为什么我拍的残疾人,我从哪里来的。
在"光"框架是不印制,并尽我可能会提供的,它从未收到。 总编辑的杂志"苏照"自己用自己的双手的框架的三次集合被送到一些国际摄影比赛–"Interpress-照片"世界新闻照片,附带他们的行动不偏不倚的审查。
风吹出的调整。 在"苏照"聚集了全厅的莫斯科的编辑摄影师,讨论的主题—如何使之现代化杂志。 我把这张照片的话:"只是一些照片打印"。 并响应我听说:"伊戈尔,在那里,你之前为什么你这样的镜头并没有带来在"苏联的照片"吗?"
一个孤独的,但明智的
这个胜利的日子,关于年76-77. 这样的场景是形成上堤。 我认为最明智的是一个中间是单身,他正忙着喝啤酒,吃三明治。 和这些仍然是未知是什么将这样做。
地震发生在亚美尼亚
人的名单找到并管理对识别。 他们挂在玻璃新闻中心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在一些zdanitse,并且在这里人们所有的时间来阅读。

首席工程师的一个缝纫厂。 它挖出来从瓦砾中被摧毁的厂2.5小时,这一切的时候我是站在摇曳板上的突出束。 很明显,对于两个半小时我就能够采取了很多照片,但某种力量让我在这个不安全的地方。 三,四拍摄–我已经退出他的位置。 没有什么可以删除。 然而,这是一个最好的镜头在这里,在这个系列。 那是谁帮我吗? 我倾向于认为他。 好吧,也许它只是发生了。
我到的时候在莫斯科的照片表明灯,给了名义上的逆转而冷静的照片。 和我非常伤害。
我希望这将打印照片并更强大。 我送它所有的"时间"和"时间"被释放与主要报告的数字。 和他们提名我为这个报告最好的记者的一年。
第一次国际竞争的理发师在莫斯科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女孩在照片模型的竞争,他们干的头发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海报。 有趣的是,这张照片在杂志上发表"Ogonek"在多年以前改革,但一些kadrirovanie的。 主要艺术家从内阁大剪刀一个长度为20厘米的话"你的,呃,加夫里洛夫"切海报。
Vysotsky的葬礼
塔甘卡,对剧院。 葬礼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 我站在棺材在剧院两个小时,不能离开。 博览会是错误的,当时来到广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只有现在,就在今年,我意识到实际上的葬礼弗拉基米尔*Vysotsky是第一个未经批准的集会在苏联。 第一次全国范围内不服从当局,当人们来了,没人打电话,没有人为的冲击,如在示范在7月或1日,他们来了。
太松
拘留中心在莫斯科Altuf'evskoe高速公路。 我拍摄了有好几次,每次–以极大的兴趣。 好了,我能说什么? 与巨大的痛苦是太华而不实的。 没有疼痛-那不是特别的。 但遗憾的儿童。 那里收集所有离家出走,找到了,在火车站、在街道上。
他当时剪,头虱跳他、三米,从他。 我几乎没有时间来耸耸肩,认为他的所有合理的,直到它被删除。
浪费的生产
70,莫斯科。 不信神的车道。 相反,窗口,对其人民通过菜,只有用的标签,在一个水坑,有一家商店"矿泉水"是相当有名的在莫斯科举行。 为了通过菜,得到的钱,走在前面,并购买葡萄酒和啤酒那也都是出售,人们在这个行业和参与。
生命之后,阿富汗
80年代末的郊区。 这是一个康复医院的士兵返回阿富汗。 还有这里的男孩。 医院–500人,他们刚刚从那里回来,看到死亡。 他们是很难的工作人员。
最好的照片1990年在美洲
月6日,1990年,第一年的工作,该杂志的"时间"−除去的装饰的这座城市之前,7月。 这是最后一月7日,当时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示范。 该框架是印在"时间",然后,他成为了最好的照片的一年,在美国健康的书,我拥有它。 接下来的一天什么都不是。 所有最后一个示范,去游行。 段落。
照片是不值得的悲伤所造成,为了这张照片
我是射击东西在格鲁吉亚–突然雪崩在斯瓦涅季的。 一个男性天鹅是在底部时雪崩来,倒在他的村庄和高山的道路,我们一起去到现场的悲剧。 我们的路上花了三个或四天。 来了–整个村子被摧毁。 我开始采取关闭。 有没有人在街头,没有绝对的。 突然我看到了这种残余的房子提出了这些人民--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被携带小杯茶茶或伏特加酒。 该名男子在他的胸口画像死者在雪崩他相对的。 我的理解是,我可以做足够的用于这种僵硬的框架。 他们去了。 我知道在哪里这样做,你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等待。 在这里他们来了,我把相机给你的眼睛,一段时间按。 完全沉默的山脉。 和这个男人看着我。 我身后就是我的天鹅,我到了,所以我把我的手放在肩并说,"他不喜欢你拍的照片"。
我不要拍更多,没有一个单一的框架。 女人的哭泣,哭泣,在他的膝盖上扔雪铲,孩子站在一边这么奇怪,有一顶帽子,一只眼睛紧,和一个男人。 我没有删除。 当它结束了,男人过来找我,并邀请我参加葬礼在防空洞。 其他的邀请到这样的事件没有被接受,但我邀请所示尊重。
孩子们在笼子里
在第一次出版的杂志"Ogonek"从地方不是那么遥远–作为前苏联这类材料不打印。 它Sudskogo殖民地,对少年罪犯。 四天我做了一个材料,在一般情况下,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名气和大量的奖牌,发表在独立杂志的英语,多本书籍已经出版。 然后有了数字照相机,我不能在显示器上见,我是否有一个阴影下跌。 我有这个树荫下,并希望。 这是在洞,一人坐在盯着我,虽然我没请他来看。
道路死亡
开始的旅程来的帕米尔高原,80年代初。 这是一个最困难的旅行。 我们沿着路霍罗格–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这条道路是所谓死亡的道路上。 有高地,4,5–5千米的道路蜿蜒曲折的悬崖。 并且传输我们飞的汽车。 如果不是因为卫兵...他们都互相帮助,因为他们明白,停止你在这条路上的夜晚,你可能不会醒来。
天气非飞行
这是"多莫杰多沃"的机场、70研究。 我从火车到终端的建筑内。 天气很坏和飞机不飞,这样所有neuletevshih解决在机场和周围。 该名男子在照片是不是走了,他睡这里结束的这列火车"的办法"。
第一次
这是未来的中尉,在第一个航班。 这是他的意见。 第一次教练和他在一起,他坐在第一倍。 这在我看来,奥伦堡飞行学校和鄂木斯克–在一般情况下,在那些部分。
建设未来
这是萨哈林,1974年。 我去练习的学生摄影师建筑队。 在这张照片我的朋友和同学。 和那个有条腿是不清楚他们已经是叶戈尔,是正确的,现在的领导人之一"传"。 它们在暖气管道铺设电缆,一端的另一种转移。
与报复的所有权利
科西嘉的。 我走过通过科西嘉的车头的科西嘉黑手党。 我们开车到山区。 有些种类的诗人、艺术家、作家非常不错的人,我们跟他们喝酒。 我走到离该公司,看到这两个丰富多彩的人。 这是村民们在高山脉。 我说法语的非常严重。 他们有另一种方言。 好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如何更好问:"你有什么在这里是一个报仇吗?"。 和他们中的一个立即翻过来回拉脱下他的衬衫,一把手枪和使用的语言:"我们在这里,仇杀总是准备好了。 这里的恩怨–请。" 然后笑着甜蜜。出版
也很有趣: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学的农村生活的—照片的文章
惊人的城镇上的悬崖的边缘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cameralabs.org/10274-zhizn-pojmannaya-vrasplokh-snimki-legendarnogo-sovetskogo-fotozhurnalista-igorya-gavrilova
对于伊戈尔主流的分析报告。 主要目的工作拍摄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搜索其他曾在俄罗斯,曾在50个国家拍摄的几乎所有的热点的国家,在七天之后爆炸,飞越了反应器的切尔诺贝利。
专业精神、热爱他们的工作,并正确的原则所做工作的伊戈尔*重要的和得到国际承认。 摄影师的图片,发表在国际杂志:巴黎Matsh Le照片,斯特恩,Spiegel,独立的,艾丽,发挥男孩和其他许多人。 提名的标题是"最好的摄影师一年的"时代杂志。 获胜者的世界新闻照片奖。
在版的"俄罗斯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时50镜头的拍摄者在不同时期的生活–从学生年的到最近在世界各地旅行。 伊戈尔讲的每个画面−简而言之,地方详细说明,但是某个地方,并与离题纳入更一般的主题。
它变成了一个伤感的故事,迫使以看看照片的相当不同的角度。
公共

晚的80-90年代初。 社区。 看起来像一个装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那里建造的临时peregorodki描绘了一些生活。 但它是一个真正的公寓。
我被要求采取主题的社区。 我不是在这个公寓是,和紧张我所有的朋友谁知道或有朋友住在社区公寓。 但是,这绝对让我吃惊。 在该框架的一个双人间一个家庭。 那个角落坐着一个母亲,我们脚下是她的女儿,非常可爱。 他们只是razmorozili这个大房间里胶合板分区彼此分离。 但razmorozili不到天花板上,而中间,因此有可能爬上这座墙,并从那里来做出这样一个框架。 记住,灰尘的是不是擦了,我认为,六个月或一年,我的眼泪出的整体在某些网、灰尘、边界。
一个时代的象征

我们有足够的住年前,当人们来到店里看见绝对是空架子。 这是开始第90或第89.
"你去哪里了吗?"

框架的最不幸的命运。 我做了它在乌克兰西部,在Ivano-Frankivsk的。 在那些日子里,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人从苏联集团,大量的记者。 我去新闻中心的酒店看到这个场景在巴士站。 只是有几次点击。 我被攻击的一些军队,开始喊到整个Ivano-Frankivsk,我诽谤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为什么我拍的残疾人,我从哪里来的。
在"光"框架是不印制,并尽我可能会提供的,它从未收到。 总编辑的杂志"苏照"自己用自己的双手的框架的三次集合被送到一些国际摄影比赛–"Interpress-照片"世界新闻照片,附带他们的行动不偏不倚的审查。
风吹出的调整。 在"苏照"聚集了全厅的莫斯科的编辑摄影师,讨论的主题—如何使之现代化杂志。 我把这张照片的话:"只是一些照片打印"。 并响应我听说:"伊戈尔,在那里,你之前为什么你这样的镜头并没有带来在"苏联的照片"吗?"
一个孤独的,但明智的

这个胜利的日子,关于年76-77. 这样的场景是形成上堤。 我认为最明智的是一个中间是单身,他正忙着喝啤酒,吃三明治。 和这些仍然是未知是什么将这样做。
地震发生在亚美尼亚

人的名单找到并管理对识别。 他们挂在玻璃新闻中心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在一些zdanitse,并且在这里人们所有的时间来阅读。

首席工程师的一个缝纫厂。 它挖出来从瓦砾中被摧毁的厂2.5小时,这一切的时候我是站在摇曳板上的突出束。 很明显,对于两个半小时我就能够采取了很多照片,但某种力量让我在这个不安全的地方。 三,四拍摄–我已经退出他的位置。 没有什么可以删除。 然而,这是一个最好的镜头在这里,在这个系列。 那是谁帮我吗? 我倾向于认为他。 好吧,也许它只是发生了。
我到的时候在莫斯科的照片表明灯,给了名义上的逆转而冷静的照片。 和我非常伤害。
我希望这将打印照片并更强大。 我送它所有的"时间"和"时间"被释放与主要报告的数字。 和他们提名我为这个报告最好的记者的一年。
第一次国际竞争的理发师在莫斯科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女孩在照片模型的竞争,他们干的头发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海报。 有趣的是,这张照片在杂志上发表"Ogonek"在多年以前改革,但一些kadrirovanie的。 主要艺术家从内阁大剪刀一个长度为20厘米的话"你的,呃,加夫里洛夫"切海报。
Vysotsky的葬礼

塔甘卡,对剧院。 葬礼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 我站在棺材在剧院两个小时,不能离开。 博览会是错误的,当时来到广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只有现在,就在今年,我意识到实际上的葬礼弗拉基米尔*Vysotsky是第一个未经批准的集会在苏联。 第一次全国范围内不服从当局,当人们来了,没人打电话,没有人为的冲击,如在示范在7月或1日,他们来了。
太松
拘留中心在莫斯科Altuf'evskoe高速公路。 我拍摄了有好几次,每次–以极大的兴趣。 好了,我能说什么? 与巨大的痛苦是太华而不实的。 没有疼痛-那不是特别的。 但遗憾的儿童。 那里收集所有离家出走,找到了,在火车站、在街道上。
他当时剪,头虱跳他、三米,从他。 我几乎没有时间来耸耸肩,认为他的所有合理的,直到它被删除。
浪费的生产

70,莫斯科。 不信神的车道。 相反,窗口,对其人民通过菜,只有用的标签,在一个水坑,有一家商店"矿泉水"是相当有名的在莫斯科举行。 为了通过菜,得到的钱,走在前面,并购买葡萄酒和啤酒那也都是出售,人们在这个行业和参与。
生命之后,阿富汗

80年代末的郊区。 这是一个康复医院的士兵返回阿富汗。 还有这里的男孩。 医院–500人,他们刚刚从那里回来,看到死亡。 他们是很难的工作人员。
最好的照片1990年在美洲

月6日,1990年,第一年的工作,该杂志的"时间"−除去的装饰的这座城市之前,7月。 这是最后一月7日,当时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示范。 该框架是印在"时间",然后,他成为了最好的照片的一年,在美国健康的书,我拥有它。 接下来的一天什么都不是。 所有最后一个示范,去游行。 段落。
照片是不值得的悲伤所造成,为了这张照片

我是射击东西在格鲁吉亚–突然雪崩在斯瓦涅季的。 一个男性天鹅是在底部时雪崩来,倒在他的村庄和高山的道路,我们一起去到现场的悲剧。 我们的路上花了三个或四天。 来了–整个村子被摧毁。 我开始采取关闭。 有没有人在街头,没有绝对的。 突然我看到了这种残余的房子提出了这些人民--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被携带小杯茶茶或伏特加酒。 该名男子在他的胸口画像死者在雪崩他相对的。 我的理解是,我可以做足够的用于这种僵硬的框架。 他们去了。 我知道在哪里这样做,你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等待。 在这里他们来了,我把相机给你的眼睛,一段时间按。 完全沉默的山脉。 和这个男人看着我。 我身后就是我的天鹅,我到了,所以我把我的手放在肩并说,"他不喜欢你拍的照片"。
我不要拍更多,没有一个单一的框架。 女人的哭泣,哭泣,在他的膝盖上扔雪铲,孩子站在一边这么奇怪,有一顶帽子,一只眼睛紧,和一个男人。 我没有删除。 当它结束了,男人过来找我,并邀请我参加葬礼在防空洞。 其他的邀请到这样的事件没有被接受,但我邀请所示尊重。
孩子们在笼子里

在第一次出版的杂志"Ogonek"从地方不是那么遥远–作为前苏联这类材料不打印。 它Sudskogo殖民地,对少年罪犯。 四天我做了一个材料,在一般情况下,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名气和大量的奖牌,发表在独立杂志的英语,多本书籍已经出版。 然后有了数字照相机,我不能在显示器上见,我是否有一个阴影下跌。 我有这个树荫下,并希望。 这是在洞,一人坐在盯着我,虽然我没请他来看。
道路死亡

开始的旅程来的帕米尔高原,80年代初。 这是一个最困难的旅行。 我们沿着路霍罗格–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这条道路是所谓死亡的道路上。 有高地,4,5–5千米的道路蜿蜒曲折的悬崖。 并且传输我们飞的汽车。 如果不是因为卫兵...他们都互相帮助,因为他们明白,停止你在这条路上的夜晚,你可能不会醒来。
天气非飞行

这是"多莫杰多沃"的机场、70研究。 我从火车到终端的建筑内。 天气很坏和飞机不飞,这样所有neuletevshih解决在机场和周围。 该名男子在照片是不是走了,他睡这里结束的这列火车"的办法"。
第一次

这是未来的中尉,在第一个航班。 这是他的意见。 第一次教练和他在一起,他坐在第一倍。 这在我看来,奥伦堡飞行学校和鄂木斯克–在一般情况下,在那些部分。
建设未来

这是萨哈林,1974年。 我去练习的学生摄影师建筑队。 在这张照片我的朋友和同学。 和那个有条腿是不清楚他们已经是叶戈尔,是正确的,现在的领导人之一"传"。 它们在暖气管道铺设电缆,一端的另一种转移。
与报复的所有权利

科西嘉的。 我走过通过科西嘉的车头的科西嘉黑手党。 我们开车到山区。 有些种类的诗人、艺术家、作家非常不错的人,我们跟他们喝酒。 我走到离该公司,看到这两个丰富多彩的人。 这是村民们在高山脉。 我说法语的非常严重。 他们有另一种方言。 好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如何更好问:"你有什么在这里是一个报仇吗?"。 和他们中的一个立即翻过来回拉脱下他的衬衫,一把手枪和使用的语言:"我们在这里,仇杀总是准备好了。 这里的恩怨–请。" 然后笑着甜蜜。出版
也很有趣: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学的农村生活的—照片的文章
惊人的城镇上的悬崖的边缘
P.S.记住,仅仅通过改变他们的消费—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了。 ©
资料来源:cameralabs.org/10274-zhizn-pojmannaya-vrasplokh-snimki-legendarnogo-sovetskogo-fotozhurnalista-igorya-gavril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