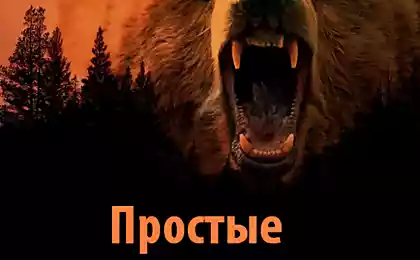1125
Zhidobanderovets职业。
离开塞瓦斯托波尔黯然。随着城市,这是值得欢迎的,有礼貌,干净的悲伤。美丽的海滨城市,我记得他在90年代初,当他来到这里度假,与他的父母一个月。这个镇是那么封闭,并通过检查站后,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秘密交流。然后,我们住在上停泊的船舶机舱,通过塞瓦斯托波尔,军事荣耀地的无尽的古迹徘徊;海滩,全景,摩天轮,乘船游览。而就在当天的城市是最美丽的烟花汇演是我所见过的在我的生活中,当焰火飞腾而起来自全国各地的船舶和反映在海面上。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它,并尝试弹出一个陌生城市的记忆,因为我曾见过他在过去两个星期。
随着法西斯主义出生在人们的印象?到那时,人们开始看到不同政见者最大的敌人?当泡沫开始在口中以收集?谁哭第一,当一个相当体面的人群乡亲开始吟诵:燃烧吧,她是个女巫!她所有的烦恼!
它是如此吧。人们愿意打破我们分开,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想给他们自由。
我花时间在占领后得到的经验,这是一个犹太人在柏林30年代的经历。当你意识到,如果人们在这个城市将实现你是谁,没有人会救不了你。警方与他们,与他们的祖母,商店,出租车司机,在咖啡馆和餐馆酒吧招待......在哥萨克的街道去检查登记或醉意自卫迷在城市街道和海湾的知识。
朋友们,我有很多谁正在做的事情,即使是在一个封锁的接触坚强和勇敢的家伙。帮助部分蔓延至少有一些可靠的信息,在刚刚结束的争取和平。但是,如果我的话,我知道,我不会给他们打电话求援。换句话说他们。我们毕竟是少数。我们抓住了。
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女朋友打电话。她说,她的朋友在家里的收音机和规定,收获,第二天我们的军队。一个地方的人,文尼察之一,来自俄罗斯的记者。现在,他们打破了门SS支队(自卫塞瓦斯托波尔)。有朋友问:怎么办?我不知道。地址,但我单独去那里 - 这是愚蠢的。同样,我呼吁熟悉的活动家。
- 怎么做
? - 祷告 - 告诉我 - 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然后,我们可以来提供资金。兑换绑架的受害者。这是正常的做法。今天,我有两个救援,殴打,但更重要的是活着的。
人被绑架。总是写一遍有人已经消失。在入口克里米亚女孩的话,有人失去了一位邻居,有人被打......一位朋友写道,他已宣布狩猎在城市...
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磁带的口袋里。以防万一。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通过在纳希莫夫广场餐厅罗马的服务员。我们有一个咬那里抓vayfay。我和我的朋友罗马和玛利亚从基辅。玛莎谈在Skype上与他的父亲,不忘谨慎。简单谈一下心情在城市。进入在两名警察的形式和两个Kazatchkov。当被问及文件。这些家伙表现出护照基辅居留证,我,虽然,有一本护照,命名不同的名字,他说雅尔塔,并没有采取护照。礼貌地坚持我们被放在一只猴子,并采取到的Leninsky区警察局。在路上,我的肱二头肌的区域把我的护照在扭曲的服装。我们到了。我们是通过门和棱子领着他到四楼。男孩子们在走廊里,我第一次被传唤作证。
(折叠)
我骗了很多,一个蓬勃发展。而生活在雅尔塔他艰难的命运,以及有关的山寨维修海边,其父母刚刚完成了贷款,等待夏天到了,现在羊肉。完全拒绝给指纹 - 东正教的信仰不允许。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搜索甚至被迫脱下我们的鞋子。全指法,手却没有触及。尽管时间已晚,授牌的协议上别人的名字,sfotkali电话,拿了卡从变焦,并决定放手。
我们被安全带到玛莎,并且被要求等待另一个底部。对于孩子的亲属都已经到了,我从罪恶消失。
这时,风暴在隔壁房间罗马,他写道:
"卢礼貌地沟通(那句“他妈的婊子,关在迈丹会大喊”只有一次响起刻录机上的一名中尉)同样的中尉问我,问我出去一会儿。我要拿起尸体在同一时间,我说他不会跑掉的任何地方。两分钟后,他冲出房间与您的手机,然后有第二个字符!他表示短信的朋友,谁知道,我们是在克里米亚,并说:“什么时候会搞垮列宁纪念碑”(这是一个笑话)。该人士要求我的笔记本电脑(在长kriptovat盘家伙的个人资料查找)请...然后他们看到基辅对电脑里的照片迈丹,和塞瓦斯托波尔和列宁的人!第二,第三,第四个字符!在便衣,礼貌,给这个问题:“你是谁?”推夹克和微笑挑衅。而如果没有nouta和电话半小时坐在隔壁办公室。他们叫我全部用智能字符不超过长臂猿和中尉在一起。 “谁说了算?你们有多少人?称取?比注资? (用于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不得不站在他们面前,在什么出生并显示所有你厘米它还可以扩展到欧洲,不要触摸,询问在他们面前挥舞。?)"
罗马发现的笔记本电脑,在那里我开始在电枢/ h时,一些海报股份(文艺晚会的一天!舍甫琴科)和图片视频。有警察和俄罗斯联邦,或FSB明确GRU代表。罗马跌至傻子,什么都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不记得名字,并有数字,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
但看到亲戚塞瓦斯托波尔仍然不敢,你们别打。
痛苦地感到羞愧的人谁忘记自己是被其他人包围。
公投后,我去了基辅。塞瓦斯托波尔抓获rashisty和同情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烧书(接近UKR,通道)和乌克兰的国旗。而事实上,俄罗斯不会帮助他们,使事情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俄罗斯全部落到了制裁,美国,zhidobanderovtsev各阶层,宗教和几代人。大家谁想要的自由。
不久,他们开始燃烧女巫。
尼古拉Bazarkin STRONG>
我知道科尔。他五年前走过美洲搭便车到加拿大智利南部。十八个月像。与所有我找到了共同语言。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而原谅我,我长大了妓女。我不相信媒体,和科尔 - 相信
。
通常,它是揭示时刻。在克里米亚,阴部和绑架的记者。它总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错了事,肮脏和犯罪,并尽量不留下痕迹。或者当他们感到深深的错误。所以,我必须这样做,并呼吁直言不讳。俄罗斯人支持普京 - 纳粹,就像大多数克里米亚居民(虽然后者通常是某种形式的纳粹和铁锹之间的野生交叉) em>的
来源 npubop.livejournal.com/
随着法西斯主义出生在人们的印象?到那时,人们开始看到不同政见者最大的敌人?当泡沫开始在口中以收集?谁哭第一,当一个相当体面的人群乡亲开始吟诵:燃烧吧,她是个女巫!她所有的烦恼!
它是如此吧。人们愿意打破我们分开,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想给他们自由。
我花时间在占领后得到的经验,这是一个犹太人在柏林30年代的经历。当你意识到,如果人们在这个城市将实现你是谁,没有人会救不了你。警方与他们,与他们的祖母,商店,出租车司机,在咖啡馆和餐馆酒吧招待......在哥萨克的街道去检查登记或醉意自卫迷在城市街道和海湾的知识。
朋友们,我有很多谁正在做的事情,即使是在一个封锁的接触坚强和勇敢的家伙。帮助部分蔓延至少有一些可靠的信息,在刚刚结束的争取和平。但是,如果我的话,我知道,我不会给他们打电话求援。换句话说他们。我们毕竟是少数。我们抓住了。
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女朋友打电话。她说,她的朋友在家里的收音机和规定,收获,第二天我们的军队。一个地方的人,文尼察之一,来自俄罗斯的记者。现在,他们打破了门SS支队(自卫塞瓦斯托波尔)。有朋友问:怎么办?我不知道。地址,但我单独去那里 - 这是愚蠢的。同样,我呼吁熟悉的活动家。
- 怎么做
? - 祷告 - 告诉我 - 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然后,我们可以来提供资金。兑换绑架的受害者。这是正常的做法。今天,我有两个救援,殴打,但更重要的是活着的。
人被绑架。总是写一遍有人已经消失。在入口克里米亚女孩的话,有人失去了一位邻居,有人被打......一位朋友写道,他已宣布狩猎在城市...
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磁带的口袋里。以防万一。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通过在纳希莫夫广场餐厅罗马的服务员。我们有一个咬那里抓vayfay。我和我的朋友罗马和玛利亚从基辅。玛莎谈在Skype上与他的父亲,不忘谨慎。简单谈一下心情在城市。进入在两名警察的形式和两个Kazatchkov。当被问及文件。这些家伙表现出护照基辅居留证,我,虽然,有一本护照,命名不同的名字,他说雅尔塔,并没有采取护照。礼貌地坚持我们被放在一只猴子,并采取到的Leninsky区警察局。在路上,我的肱二头肌的区域把我的护照在扭曲的服装。我们到了。我们是通过门和棱子领着他到四楼。男孩子们在走廊里,我第一次被传唤作证。
(折叠)
我骗了很多,一个蓬勃发展。而生活在雅尔塔他艰难的命运,以及有关的山寨维修海边,其父母刚刚完成了贷款,等待夏天到了,现在羊肉。完全拒绝给指纹 - 东正教的信仰不允许。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搜索甚至被迫脱下我们的鞋子。全指法,手却没有触及。尽管时间已晚,授牌的协议上别人的名字,sfotkali电话,拿了卡从变焦,并决定放手。
我们被安全带到玛莎,并且被要求等待另一个底部。对于孩子的亲属都已经到了,我从罪恶消失。
这时,风暴在隔壁房间罗马,他写道:
"卢礼貌地沟通(那句“他妈的婊子,关在迈丹会大喊”只有一次响起刻录机上的一名中尉)同样的中尉问我,问我出去一会儿。我要拿起尸体在同一时间,我说他不会跑掉的任何地方。两分钟后,他冲出房间与您的手机,然后有第二个字符!他表示短信的朋友,谁知道,我们是在克里米亚,并说:“什么时候会搞垮列宁纪念碑”(这是一个笑话)。该人士要求我的笔记本电脑(在长kriptovat盘家伙的个人资料查找)请...然后他们看到基辅对电脑里的照片迈丹,和塞瓦斯托波尔和列宁的人!第二,第三,第四个字符!在便衣,礼貌,给这个问题:“你是谁?”推夹克和微笑挑衅。而如果没有nouta和电话半小时坐在隔壁办公室。他们叫我全部用智能字符不超过长臂猿和中尉在一起。 “谁说了算?你们有多少人?称取?比注资? (用于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不得不站在他们面前,在什么出生并显示所有你厘米它还可以扩展到欧洲,不要触摸,询问在他们面前挥舞。?)"
罗马发现的笔记本电脑,在那里我开始在电枢/ h时,一些海报股份(文艺晚会的一天!舍甫琴科)和图片视频。有警察和俄罗斯联邦,或FSB明确GRU代表。罗马跌至傻子,什么都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不记得名字,并有数字,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
但看到亲戚塞瓦斯托波尔仍然不敢,你们别打。
痛苦地感到羞愧的人谁忘记自己是被其他人包围。
公投后,我去了基辅。塞瓦斯托波尔抓获rashisty和同情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烧书(接近UKR,通道)和乌克兰的国旗。而事实上,俄罗斯不会帮助他们,使事情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俄罗斯全部落到了制裁,美国,zhidobanderovtsev各阶层,宗教和几代人。大家谁想要的自由。
不久,他们开始燃烧女巫。
尼古拉Bazarkin STRONG>
我知道科尔。他五年前走过美洲搭便车到加拿大智利南部。十八个月像。与所有我找到了共同语言。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而原谅我,我长大了妓女。我不相信媒体,和科尔 - 相信
。
通常,它是揭示时刻。在克里米亚,阴部和绑架的记者。它总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错了事,肮脏和犯罪,并尽量不留下痕迹。或者当他们感到深深的错误。所以,我必须这样做,并呼吁直言不讳。俄罗斯人支持普京 - 纳粹,就像大多数克里米亚居民(虽然后者通常是某种形式的纳粹和铁锹之间的野生交叉) em>的
来源 npubop.livejourn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