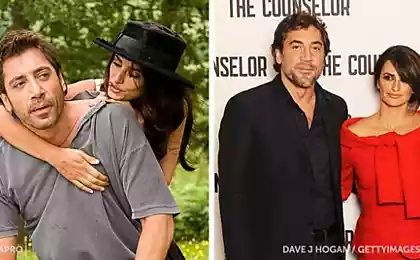1016
哈维尔·巴登
当我看到自己在杂志的封面,我意识到,世界已经疯了。
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在阿尔·帕西诺。如果说电话铃声响起,并在结束时,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玩,我想我只是发疯。

我实现了这一梦想成真当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显示艾尔帕西诺我的电影“夜幕降临前”。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在大约三是西班牙人时间帕西诺从纽约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喜欢我的工作。
没有保费不能让你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只是为了让观众来电影院的“奥斯卡”是必要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成了挺好用英语交谈 - 不够好,使之清楚,这种语言永远是我的母亲。当我说西班牙语中的“我爱”或“我恨”,所以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脑海,但是当我用英语说,在我的脑海空虚同样的事情。
我不开车,和周围的一切似乎是某种不寻常。每个人,但我。
当Cohens叫我“老无所依”,我告诉他们,“你看,我不是你想谁是演员,我不开车,几乎没有说英语,恨暴力的各种形式。”他们笑了,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你和»
在我的头发,在“老无所依”都笑了起来,有的甚至问我怎么不累穿这假发。但实际上,这是我自己的头发。
只有两个在那里我拿着武器的电影。在第一阶段,“珀迪塔杜兰戈”我在1996年出现,这是很暴力的电影,之后我发誓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当11年后,在Coens已经邀请我在“老无所依”中扮演的,我想憋了半天,也没有说“是”,但Coens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我从来不认为科恩两个人。当他们的工作,他们成为一体 - 有两个头的怪物。而这些头散赞美对方,从不争辩。当他们对你说的,他们说,作为一个人。
我注意到,人们为之,我认为有才华 - 如米洛斯·福尔曼,亚历杭德罗·Amenabar的Coens和伍迪·艾伦 - 工作原理相同: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是想做到这一点 - 这一切
。
主要的事情在电影 - 一个故事。因此,考虑一切。我认为,主要的东西 - 你怎么知道它
。
在我的童年有政治和暴力太多说话,我叔叔花了很多年的监禁,因为他是佛朗哥政权的激烈的对手。但我喜欢生活在这方面的知识。
在某些时候,你必须最后用你的意见决定。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你的生活中间。
当以6岁,我带着在“私生子”费尔南多·费尔南 - 戈麦斯一个小角色(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 - 君子),有一个场景,一个人开玩笑地威胁我带了一把枪。根据剧本,我不得不笑,但我哭了起来。然后导演说:“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我仍然喜欢它。”那一天,我意识到,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跟导演争论。
我开始打橄榄球的时候我九岁,并发挥到23。自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在我的橄榄球打得时间瘦一点的人谁差点就在球的领域。现在,他们穿像瞪羚,而这一切看起来更像赛车。但是橄榄球也变得更加有趣。
打橄榄球在西班牙 - 就像是在日本斗牛士
。
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行业,为什么荒唐没有去非洲 - 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但答案很简单:我是一个忧郁症,忧郁症患者从坏的救星去
。
像许多害羞的人,谁似乎没有人害羞,我很害羞。
我相信,一旦人们真的是小猴子。至少,每天早晨,当我照镜子时,我把问候达尔文。在这种时候,它是特别明显正确性。
真正的美在于丑 - 这就是我告诉自己每一天
。
我不是一个奢侈品。黑鱼子酱,我 - 煎两个鸡蛋,土豆和火腿。而这一切 - 在大板
有一次,我是当事人的王,现在我是一个老男人。一对夫妇的鸡尾酒,我越什么都不需要。
二十年来,我们都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十四确实到发出25,但更接近五十,看来,我们开始感到难过的事情了33遗憾。但是,我意识到:地狱与所有这些怜悯的
在每个人有他,他应该是什么谁之间的不断斗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观察到这场战斗。
我们的星球将是最好的一切可能的世界,如果所有的人都在他们做什么诚实的。如果我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诚实的演员。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水管工,我希望,我将是一个诚实的水暖工。
我做一部电影,只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更多的,我可以。
有人曾经说过,一个演员和疯子之间的区别在于,演员是一个返程票,并只在一个疯子。我同意这一点。
最简单的 - 是发挥人谁还活着。这是责任,可以很容易你发疯的程度。
演员 - 如西红柿在市场上,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而我同样的西红柿。但我不关心要花多少钱的西红柿。
我不希望表现出过于频繁的医生他的阴茎。
我宁愿在沉默中灭亡。死亡的所有其他情况下,我不在乎少得多。
最重要的是我还记得有一天,我的父亲去世了。
他的父亲离开了家庭,当我很年轻,我带来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有一个妇女教育。
人们认为,如果你能看到两位演员彼此相爱,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彼此相爱。甚至没有人认为我们只是付钱的话,并在设置一个必然重复:“发挥它努力,你混蛋,我不相信»
电影 - !这只是一部电影,只要你不这样做一部电影,每个人都会说,哇
作为著名的 - 就是这样的废话。感谢上帝,在一顶帽子和墨镜,我还可以走动无法识别的任何地方。
我喜欢它,当生命点到我在做什么的渺小。
我唱的好 - 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脖子
。
有时我发现自己在这样的事实,他不会介意有布拉德·皮特的身体。
我想记住笑。
不,我不是布拉德·皮特。
来源
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在阿尔·帕西诺。如果说电话铃声响起,并在结束时,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玩,我想我只是发疯。

我实现了这一梦想成真当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显示艾尔帕西诺我的电影“夜幕降临前”。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在大约三是西班牙人时间帕西诺从纽约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喜欢我的工作。
没有保费不能让你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只是为了让观众来电影院的“奥斯卡”是必要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成了挺好用英语交谈 - 不够好,使之清楚,这种语言永远是我的母亲。当我说西班牙语中的“我爱”或“我恨”,所以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脑海,但是当我用英语说,在我的脑海空虚同样的事情。
我不开车,和周围的一切似乎是某种不寻常。每个人,但我。
当Cohens叫我“老无所依”,我告诉他们,“你看,我不是你想谁是演员,我不开车,几乎没有说英语,恨暴力的各种形式。”他们笑了,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你和»
在我的头发,在“老无所依”都笑了起来,有的甚至问我怎么不累穿这假发。但实际上,这是我自己的头发。
只有两个在那里我拿着武器的电影。在第一阶段,“珀迪塔杜兰戈”我在1996年出现,这是很暴力的电影,之后我发誓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当11年后,在Coens已经邀请我在“老无所依”中扮演的,我想憋了半天,也没有说“是”,但Coens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我从来不认为科恩两个人。当他们的工作,他们成为一体 - 有两个头的怪物。而这些头散赞美对方,从不争辩。当他们对你说的,他们说,作为一个人。
我注意到,人们为之,我认为有才华 - 如米洛斯·福尔曼,亚历杭德罗·Amenabar的Coens和伍迪·艾伦 - 工作原理相同: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是想做到这一点 - 这一切
。
主要的事情在电影 - 一个故事。因此,考虑一切。我认为,主要的东西 - 你怎么知道它
。
在我的童年有政治和暴力太多说话,我叔叔花了很多年的监禁,因为他是佛朗哥政权的激烈的对手。但我喜欢生活在这方面的知识。
在某些时候,你必须最后用你的意见决定。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你的生活中间。
当以6岁,我带着在“私生子”费尔南多·费尔南 - 戈麦斯一个小角色(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 - 君子),有一个场景,一个人开玩笑地威胁我带了一把枪。根据剧本,我不得不笑,但我哭了起来。然后导演说:“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我仍然喜欢它。”那一天,我意识到,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跟导演争论。
我开始打橄榄球的时候我九岁,并发挥到23。自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在我的橄榄球打得时间瘦一点的人谁差点就在球的领域。现在,他们穿像瞪羚,而这一切看起来更像赛车。但是橄榄球也变得更加有趣。
打橄榄球在西班牙 - 就像是在日本斗牛士
。
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行业,为什么荒唐没有去非洲 - 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但答案很简单:我是一个忧郁症,忧郁症患者从坏的救星去
。
像许多害羞的人,谁似乎没有人害羞,我很害羞。
我相信,一旦人们真的是小猴子。至少,每天早晨,当我照镜子时,我把问候达尔文。在这种时候,它是特别明显正确性。
真正的美在于丑 - 这就是我告诉自己每一天
。
我不是一个奢侈品。黑鱼子酱,我 - 煎两个鸡蛋,土豆和火腿。而这一切 - 在大板
有一次,我是当事人的王,现在我是一个老男人。一对夫妇的鸡尾酒,我越什么都不需要。
二十年来,我们都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十四确实到发出25,但更接近五十,看来,我们开始感到难过的事情了33遗憾。但是,我意识到:地狱与所有这些怜悯的
在每个人有他,他应该是什么谁之间的不断斗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观察到这场战斗。
我们的星球将是最好的一切可能的世界,如果所有的人都在他们做什么诚实的。如果我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诚实的演员。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水管工,我希望,我将是一个诚实的水暖工。
我做一部电影,只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更多的,我可以。
有人曾经说过,一个演员和疯子之间的区别在于,演员是一个返程票,并只在一个疯子。我同意这一点。
最简单的 - 是发挥人谁还活着。这是责任,可以很容易你发疯的程度。
演员 - 如西红柿在市场上,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而我同样的西红柿。但我不关心要花多少钱的西红柿。
我不希望表现出过于频繁的医生他的阴茎。
我宁愿在沉默中灭亡。死亡的所有其他情况下,我不在乎少得多。
最重要的是我还记得有一天,我的父亲去世了。
他的父亲离开了家庭,当我很年轻,我带来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有一个妇女教育。
人们认为,如果你能看到两位演员彼此相爱,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彼此相爱。甚至没有人认为我们只是付钱的话,并在设置一个必然重复:“发挥它努力,你混蛋,我不相信»
电影 - !这只是一部电影,只要你不这样做一部电影,每个人都会说,哇
作为著名的 - 就是这样的废话。感谢上帝,在一顶帽子和墨镜,我还可以走动无法识别的任何地方。
我喜欢它,当生命点到我在做什么的渺小。
我唱的好 - 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脖子
。
有时我发现自己在这样的事实,他不会介意有布拉德·皮特的身体。
我想记住笑。
不,我不是布拉德·皮特。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