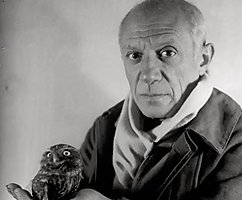纳塔利娅炎: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是不是生活
 Bashny.Net
Bashny.Net
近二十年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是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的大脑俄罗斯科学院。 着名的研究员研究了如何大脑的工作健康和生病的人。
纳塔利娅*别赫捷列夫撰写的大约400科学作品的,她发现,在该领域的机制思想、记忆、情绪和组织的人类的大脑。

发表一个简化版本的采访时的杂志"Domovoy"(N6(43)日,2004年)Maria Wardenga
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我说,会议的这需要对我个人。 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他也是医生,oncoimmunology的。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谈论信仰。 他说,你知道,我就越学科更多的强化的想法的神圣起源的世界。" 你同意这种痛苦可以克服的,只有通过信念吗?
我理解,虽然我不确定这个问题。 科学也不能从什么角度看是不拮抗剂的信仰。
另一个问题是,科学本身在某一点上开始了反对本身的宗教。 而这一点,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奇怪的,因为其目前的状态只需证明的真实性原则阐述,例如,在圣经。
但是你自己的科学课和这样的微妙问题作为人类的大脑,已有一些关系到未来以上帝吗? 或者是完全独立从事专业活动的一个进程?
他们有关的分析方法的事件。 事实上,我不是种类型的科学家要求,我不能措施,根本不存在。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同事。 我总是说,科学的方法的星星。 道路入未知的。 例如,在这种情况下可的书面证据的基础上的其它重建的历史的战争吗? 它是证实的证词,同一事件不是一个反思的时间和严重的文档? 我不是捍卫福音不需要保护—我说的就是在这种情况有关的系统了解的奇怪的,非凡的事情,例如许多证词的人人看见了,听见其他人在一个国家的临床死亡。 这种现象证实了许多患者和证据的惊人地一致,在调查的病人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目的地。 很多妇女在分娩过程中经历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临时的身体和观察自己从远处...
科学知识的违反,尤其是终止的活动的机构的视觉和听觉的必然结果在违反的,别的视线和听证会。 怎么,然后,在离开时将身体你看到和听到吗? 假设某个国家垂死的大脑。 但如何解释的一致性的统计数据:只有7-10%的总人数的有经验的临床死亡记和可以告诉关于"现象的出身"...
在你看来,这就证明了这一格言,"许多是所谓的,但少数人选择"?
我不准备得到一个答案。 我根本就没有。 但科学家必须首先,清楚地设置自己。 不要害怕。 今天很明显的是,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是不是生活。 但生物死亡的死亡灵魂—这就是问题的问题。 我先把它放在他面前的会议期间与万加...
你的愿望研究这个现象后个人会议与万加有发生任何改变吗?
我诚实地告诉王有关研究的目的,他的访问。 她顺便说一下,没有冒犯。 但希望对其进行研究之后,我们的会议,我个人没有出现。
你只是必须确保没有未知的超级大脑? 或是它为自己确定,这个问题的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现实?
我会回答你。 尽管事实上,我已经专门讨论我的生活的研究人类大脑的,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头没有来证明,其结构使原籍的男子从哺乳动物。 只是达到某一点,这个问题的范围之外我的科学和人类的利益。
你是感兴趣我怎么会来的信心。 这个时刻已经没有关系的个性,万加,也不是科学。 这事发生,后一趟万加—这只是恰好—我很有经验。
我幸存下来的背叛的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迫害在该研究所的实验性的药,我的领导和他在那里宣布,他决定离开新的大脑研究所,以及最糟糕—该死的我的两个亲人她丈夫和他的儿子,从他的第一次婚姻。 他们死了非常可悲的是,几乎同时:亚历克斯是自杀,和她的丈夫没有遭受他的死亡和死于同一天晚上。 那时我真的变了。
换句话说,仅仅经历的痛苦,导致一些新现实的理解吗?
也许这是如此。 但不是痛苦本身,但事实上,这种经验完全超出范围已知的我解释一下世界。
例如,有没有办法我可以找到一个解释的事实,我的丈夫站在我这边然后在一个梦想,要求帮助出版的手稿他的书,我还没有阅读,它不会了解到没有他。 这不是第一次这样的经历在我的生活(前我父亲的逮捕在1937年,我也看到了一个梦想,然后反映在现实),但在这里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想想发生了什么。 当然,这种新现实的稻草人。 但是然后我帮助我的朋友,牧师,校长在皇村的父亲的根纳季...
顺便说一下,我强烈建议不要谈论这样的经历。 我不是一个非常对这个安理会听取了甚至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在本书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用来编写关于任何其他观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所有变化! —我认真开始关注这个理事会。
你知道,我的童年过得极的反宗教时期。 在那些日子里,例如,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杂志"Bezbozhnik",其重点是多么黑暗奶奶,切断手指,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和明智的孙女在这些情况下,抹片检查手指碘。 如你所知,在网络然后青霉素被发现...
和一个很长的时间,甚至当我开始到国外旅行,我一直在教堂,把它们仅仅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我真的很喜欢它从一个艺术性的观点。 但是我不能想象,它将永远不会接近我在另一个办法...
和你在这方面理解福音说:"没有人会相信否则不是根据会的创造者"?
很明显的是,信仰不能也不影响下的其他人或者通过只有一个情绪,甚至也不是因为逻辑推理。 在精神的道路—太单薄的问题。 没有一个实例是不合适的。
怎么你今天,所有收到科学的荣誉和奖项,认为该短语"在开始时是这个词"吗?
在开始一切的思想。 想到一个人。 我说这不是在否认的重要性的世界的进化理论,虽然我个人喜欢不同的看法。 显然另一个。 如果你有脑子的话—如你所愿—一切真的开始。
该词的创造者。 这样的吗?
我会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众所周知的,创造性的方式更高的紧张活动。 建立可见看不见的始终是一个伟大的行动,无论是音乐创作或诗歌...你的意见,可能从这个位置来理解的过程中创造的世界? 问题是,学者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权利否认当地的事实,他们不适合进入他的世界观。 从我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它使得更有意义,重新考虑的位置。
从访谈不同年份
大脑的潜力
我总是感到惊讶,当有人试图判断有多少百分比下载了人类的大脑。我花了我的生活与工作的人的大脑,以及所有的方法的大脑研究,我知道,但我找不出谁以及它如何计数。
我们知道大脑是这样设计的,不管它可能发生的大脑一定aktiviziruyutsya。 他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还有最小化的地区的大脑将要参与。 情况的大脑不会失去的选项,不会发生。 这一次巴甫洛夫证明。 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这很好,这是最好的生存机构的大脑。
—你认为这个"计算机"坐落在我们头骨的,有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能性?
—是的,但我不喜欢当人类大脑的与计算机上。 事实上,它的创建使得我甚至不能想象有什么要求的生活可能已出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装置。 大脑那么多,它从来没有停止惊奇。
多么奇怪的声音:不考虑我自己的智能...
—我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母亲,她穿过营地,严重虐待。 她告诉我:"对上帝的份上,不要误会我,我不认为自己是聪明。 你非常能干的"。 由于她的,我和封锁,忍受和毕业。 它是,形象地说,把我的头是什么,它应该是,—"存储器矩阵"。 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说:也许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生活体验。 所有涉及科学、可以理解的。 因此,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一些食谱提高记忆你能给我们读者?
为了用于存储器是更好的,这是必要的运动。 正如有的练习,以加强肌肉的手臂、腿部、背部、颈部、腹部,还有练习,以加强存储器。 他们是非常简单的、公共的,他们可以在任何环境。
例如,许多人的爱情获得了大量的笔记本电脑,个人日记笔记本电脑。 为什么不是火车你的记忆中,并不要试着去记忆的核心所有的电话号码他们的朋友和熟人? 这不是意外早期学校儿童被迫学习非常的心脏。 包括学习没有任何实践,因此所谓的"死语言"中,人们不再说话。
把所有的教学方法。 我们总是非常批评,并最终消除。 并与它扔在垃圾桶里很好的锻炼的存储器。 记忆是非常有用的研究任何外国语言,以了解每天至少有五十个新词。
关于预言的梦想
作为一项规则,梦想没有关系的未来,所以睡不应该认真对待。 但在我的生命中,有几个梦想是预言。 其中一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下降的详细信息。 这是一个梦想着死亡的我的母亲。 妈妈还活着,很好,搁在南部,不久前我接到一个很好的字母。 在梦中,我睡着了在下午,我有一个梦想来到我的邮递员用的一封电报,其中它报道说,母亲死亡。 我要去一个葬礼上遇见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之前,招呼他们,利用他们的名字—这都是在一个梦想。 当我醒来的时候告诉我丈夫对我的梦想,他说,"你是一个专家在该地区的大脑相信梦想?"
总之,尽管事实上,我坚定地认为,我已经飞到我妈妈谈过我了 相反,我让自己被劝阻。 好了,十天后,一切都发生,正是因为这是在我的梦想。 此外,最小的细节。 例如,我早已忘记这个词SEL它我只是从来不需要它。 在梦里我一直在寻找村庄的理事会,并且在现实中我必须要看它—这就是故事。 这是我个人,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还有许多其他实例中的预言梦想,以及甚至科学发现在睡眠。 例如,发现由门捷列夫周期性系统的要素。
它不能解释。 最好不要吹毛求疵,并说这一直是目前没有科学的解释的方式不能有假定未来是给我们提前,它已经存在。 我们可以的,至少在梦里,取得联系,或者与更高的心灵或上帝的人有知识关于这个未来。 更具体的措词我喜欢等待的,因为成功的技术领域的大脑科学的是如此之大,也许会是什么东西,将揭示这一问题。出版
资料来源:/用户/1077
纳塔利娅*别赫捷列夫撰写的大约400科学作品的,她发现,在该领域的机制思想、记忆、情绪和组织的人类的大脑。

发表一个简化版本的采访时的杂志"Domovoy"(N6(43)日,2004年)Maria Wardenga
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我说,会议的这需要对我个人。 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他也是医生,oncoimmunology的。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谈论信仰。 他说,你知道,我就越学科更多的强化的想法的神圣起源的世界。" 你同意这种痛苦可以克服的,只有通过信念吗?
我理解,虽然我不确定这个问题。 科学也不能从什么角度看是不拮抗剂的信仰。
另一个问题是,科学本身在某一点上开始了反对本身的宗教。 而这一点,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奇怪的,因为其目前的状态只需证明的真实性原则阐述,例如,在圣经。
但是你自己的科学课和这样的微妙问题作为人类的大脑,已有一些关系到未来以上帝吗? 或者是完全独立从事专业活动的一个进程?
他们有关的分析方法的事件。 事实上,我不是种类型的科学家要求,我不能措施,根本不存在。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同事。 我总是说,科学的方法的星星。 道路入未知的。 例如,在这种情况下可的书面证据的基础上的其它重建的历史的战争吗? 它是证实的证词,同一事件不是一个反思的时间和严重的文档? 我不是捍卫福音不需要保护—我说的就是在这种情况有关的系统了解的奇怪的,非凡的事情,例如许多证词的人人看见了,听见其他人在一个国家的临床死亡。 这种现象证实了许多患者和证据的惊人地一致,在调查的病人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目的地。 很多妇女在分娩过程中经历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临时的身体和观察自己从远处...
科学知识的违反,尤其是终止的活动的机构的视觉和听觉的必然结果在违反的,别的视线和听证会。 怎么,然后,在离开时将身体你看到和听到吗? 假设某个国家垂死的大脑。 但如何解释的一致性的统计数据:只有7-10%的总人数的有经验的临床死亡记和可以告诉关于"现象的出身"...
在你看来,这就证明了这一格言,"许多是所谓的,但少数人选择"?
我不准备得到一个答案。 我根本就没有。 但科学家必须首先,清楚地设置自己。 不要害怕。 今天很明显的是,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是不是生活。 但生物死亡的死亡灵魂—这就是问题的问题。 我先把它放在他面前的会议期间与万加...
你的愿望研究这个现象后个人会议与万加有发生任何改变吗?
我诚实地告诉王有关研究的目的,他的访问。 她顺便说一下,没有冒犯。 但希望对其进行研究之后,我们的会议,我个人没有出现。
你只是必须确保没有未知的超级大脑? 或是它为自己确定,这个问题的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现实?
我会回答你。 尽管事实上,我已经专门讨论我的生活的研究人类大脑的,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头没有来证明,其结构使原籍的男子从哺乳动物。 只是达到某一点,这个问题的范围之外我的科学和人类的利益。
你是感兴趣我怎么会来的信心。 这个时刻已经没有关系的个性,万加,也不是科学。 这事发生,后一趟万加—这只是恰好—我很有经验。
我幸存下来的背叛的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迫害在该研究所的实验性的药,我的领导和他在那里宣布,他决定离开新的大脑研究所,以及最糟糕—该死的我的两个亲人她丈夫和他的儿子,从他的第一次婚姻。 他们死了非常可悲的是,几乎同时:亚历克斯是自杀,和她的丈夫没有遭受他的死亡和死于同一天晚上。 那时我真的变了。
换句话说,仅仅经历的痛苦,导致一些新现实的理解吗?
也许这是如此。 但不是痛苦本身,但事实上,这种经验完全超出范围已知的我解释一下世界。
例如,有没有办法我可以找到一个解释的事实,我的丈夫站在我这边然后在一个梦想,要求帮助出版的手稿他的书,我还没有阅读,它不会了解到没有他。 这不是第一次这样的经历在我的生活(前我父亲的逮捕在1937年,我也看到了一个梦想,然后反映在现实),但在这里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想想发生了什么。 当然,这种新现实的稻草人。 但是然后我帮助我的朋友,牧师,校长在皇村的父亲的根纳季...
顺便说一下,我强烈建议不要谈论这样的经历。 我不是一个非常对这个安理会听取了甚至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在本书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用来编写关于任何其他观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所有变化! —我认真开始关注这个理事会。
你知道,我的童年过得极的反宗教时期。 在那些日子里,例如,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杂志"Bezbozhnik",其重点是多么黑暗奶奶,切断手指,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和明智的孙女在这些情况下,抹片检查手指碘。 如你所知,在网络然后青霉素被发现...
和一个很长的时间,甚至当我开始到国外旅行,我一直在教堂,把它们仅仅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我真的很喜欢它从一个艺术性的观点。 但是我不能想象,它将永远不会接近我在另一个办法...
和你在这方面理解福音说:"没有人会相信否则不是根据会的创造者"?
很明显的是,信仰不能也不影响下的其他人或者通过只有一个情绪,甚至也不是因为逻辑推理。 在精神的道路—太单薄的问题。 没有一个实例是不合适的。
怎么你今天,所有收到科学的荣誉和奖项,认为该短语"在开始时是这个词"吗?
在开始一切的思想。 想到一个人。 我说这不是在否认的重要性的世界的进化理论,虽然我个人喜欢不同的看法。 显然另一个。 如果你有脑子的话—如你所愿—一切真的开始。
该词的创造者。 这样的吗?
我会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众所周知的,创造性的方式更高的紧张活动。 建立可见看不见的始终是一个伟大的行动,无论是音乐创作或诗歌...你的意见,可能从这个位置来理解的过程中创造的世界? 问题是,学者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权利否认当地的事实,他们不适合进入他的世界观。 从我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它使得更有意义,重新考虑的位置。
从访谈不同年份
大脑的潜力
我总是感到惊讶,当有人试图判断有多少百分比下载了人类的大脑。我花了我的生活与工作的人的大脑,以及所有的方法的大脑研究,我知道,但我找不出谁以及它如何计数。
我们知道大脑是这样设计的,不管它可能发生的大脑一定aktiviziruyutsya。 他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还有最小化的地区的大脑将要参与。 情况的大脑不会失去的选项,不会发生。 这一次巴甫洛夫证明。 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这很好,这是最好的生存机构的大脑。
—你认为这个"计算机"坐落在我们头骨的,有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能性?
—是的,但我不喜欢当人类大脑的与计算机上。 事实上,它的创建使得我甚至不能想象有什么要求的生活可能已出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装置。 大脑那么多,它从来没有停止惊奇。
多么奇怪的声音:不考虑我自己的智能...
—我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母亲,她穿过营地,严重虐待。 她告诉我:"对上帝的份上,不要误会我,我不认为自己是聪明。 你非常能干的"。 由于她的,我和封锁,忍受和毕业。 它是,形象地说,把我的头是什么,它应该是,—"存储器矩阵"。 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说:也许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生活体验。 所有涉及科学、可以理解的。 因此,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一些食谱提高记忆你能给我们读者?
为了用于存储器是更好的,这是必要的运动。 正如有的练习,以加强肌肉的手臂、腿部、背部、颈部、腹部,还有练习,以加强存储器。 他们是非常简单的、公共的,他们可以在任何环境。
例如,许多人的爱情获得了大量的笔记本电脑,个人日记笔记本电脑。 为什么不是火车你的记忆中,并不要试着去记忆的核心所有的电话号码他们的朋友和熟人? 这不是意外早期学校儿童被迫学习非常的心脏。 包括学习没有任何实践,因此所谓的"死语言"中,人们不再说话。
把所有的教学方法。 我们总是非常批评,并最终消除。 并与它扔在垃圾桶里很好的锻炼的存储器。 记忆是非常有用的研究任何外国语言,以了解每天至少有五十个新词。
关于预言的梦想
作为一项规则,梦想没有关系的未来,所以睡不应该认真对待。 但在我的生命中,有几个梦想是预言。 其中一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下降的详细信息。 这是一个梦想着死亡的我的母亲。 妈妈还活着,很好,搁在南部,不久前我接到一个很好的字母。 在梦中,我睡着了在下午,我有一个梦想来到我的邮递员用的一封电报,其中它报道说,母亲死亡。 我要去一个葬礼上遇见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之前,招呼他们,利用他们的名字—这都是在一个梦想。 当我醒来的时候告诉我丈夫对我的梦想,他说,"你是一个专家在该地区的大脑相信梦想?"
总之,尽管事实上,我坚定地认为,我已经飞到我妈妈谈过我了 相反,我让自己被劝阻。 好了,十天后,一切都发生,正是因为这是在我的梦想。 此外,最小的细节。 例如,我早已忘记这个词SEL它我只是从来不需要它。 在梦里我一直在寻找村庄的理事会,并且在现实中我必须要看它—这就是故事。 这是我个人,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还有许多其他实例中的预言梦想,以及甚至科学发现在睡眠。 例如,发现由门捷列夫周期性系统的要素。
它不能解释。 最好不要吹毛求疵,并说这一直是目前没有科学的解释的方式不能有假定未来是给我们提前,它已经存在。 我们可以的,至少在梦里,取得联系,或者与更高的心灵或上帝的人有知识关于这个未来。 更具体的措词我喜欢等待的,因为成功的技术领域的大脑科学的是如此之大,也许会是什么东西,将揭示这一问题。出版
资料来源:/用户/1077
标签
另请参见
心身生活
灵魂的目标。实现它的目的。
草药包按摩医治身体和灵魂
按摩草袋
该展览展示了人体皮肤无
作为一个战士 - 是有一个士兵的精神。士兵们没有灵魂 - 杀手。用灵魂的战士 - 战士
出生后的生活带出来的情感连接
10可能形式的生活
为什么六万年前,外科医生正在做的环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