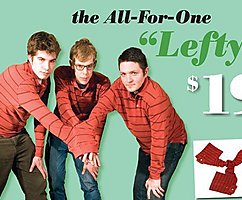当我处理Vovka
 Bashny.Net
Bashny.Net
我们的加息后,我的屁股被烧毁,并Vovka只是洒一对夫妇的手指肿了。
- 过敏。祖母说。 - 你打赌。至少有三公斤巧克力skhuyarili 2吻。为了有腹泻冷冻和眼睛的额头povylazili。应该有这样贪婪地落到巧克力。父亲,拿Motik邻居,并推动对医生的。我们还是看一下手指和这个疯的。但愿裂缝或裂纹。这将是你这个混蛋破获更好。
当然,我想推力与他的祖父。我喜欢骑在摇篮里。 Odenesh头盔在他的头上,natyanesh篷布,并提出,如果在一个战斗机飞行。但爷爷对我说的家伙的脑袋,不是一个战士,就去邻居。这将是更好的,他把我和他在一起......
Vova在床上的奶奶的房间,生病了。那么,怎么病了?除了他的手指没伤。是不是一切正常了皮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撒有红色斑点,和我去所有的绿色点。
- 你的眼睛不会在额头上更多的爬?我感兴趣的Vovka。
- 号负责沃夫克 - 但chyo已经开始伤害
。 - 一泻了吗?我想,我没有威胁,我不只是洒,但Vovka担心。
奶奶去了分钟一个小时邻居,希望这一次,我们不会将燃烧的房子,并没有飞走进入太空。因为如果房子会燃烧,这是我们塞上煤燃烧的屁股,这是一个经历白痴,因为不允许有更小的空间。屁股煤,我们不希望,我们是不会的空间。
我决定,只要爷爷去请医生,可能发生的麻烦。至于我能想象,爷爷和奶奶对我们根本不在乎。如果我们其中一人死亡,它会更容易。所以,我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决定,Vovka善待自己。我参加了一个急救箱的柜子,把从那里棉,绷带和泽伦卡。我的行为在我看来顺理成章。泽伦卡我要画在点绷带眼罩是来医生没有出来,羊毛紧密的屁股,这将是腹泻不obgadil巴布金床的案前。 Vovka困惑我的计划,但我的理由解释说,这一绷带,这样眼睛就不会失控,腹泻和泽伦卡过敏羊毛。所有的科学。首先我塞棉花内裤。在我看来一点,我加了纱布。然后,他摇了摇眼睛用绷带。你是过敏覆盖。我把棉絮斑,并开始作画。 10分钟后,我累了。景点非常多,非常小的。我拿着明智的决定采取,易油漆,不会磨折每个单独。几分钟后,有人做过。沃夫克是和干燥...
在院子里有一个崩溃的摩托车。医生赶到时,我才意识到,和得意坐下来等待,想象它是惊讶,说这是正确的对待它没有任何关系。所有主要的治疗进行,只是将手指将探索。
门开了,一个女医生走了进来,他的祖母。我决定等他在大厅的荣耀和走出了房间,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 这chёy你有手?我狐疑地问奶奶,暂停在我的身边,但她听到的答案没有来。医生走进房间Vovka ...
Ç尖叫 - 亲爱的妈妈!东西摔在地上。奶奶狐疑地看着我,跑了进来。
- 哦,你是一名儿科医生自制!奶奶跳出了房间,并跑到厨房。
我小心翼翼地凝视着房间,看到趴在地上vrachihu。不是偶然的,我想。奶奶飞进了房间,用毛巾和一杯水。开始喷上vrachihu和煽动她用毛巾。微弱的声音里面告诉你,什么是错的,但不强求。医生睁开眼睛,问,指着Vovka - 什么是与他?
在这里,外婆大概还记得我,因为她环顾四周,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苍蝇拍。她伸出手,看着我温柔地说, - 到这儿来,我的好。希波克拉底你自制。
我把它拿给了几句话,我故意退了回去。然后内心的声音吩咐 - 跑!我跑了。我跑尽我所能,与踹开前门崩溃。 Ç轰然从字面上看,因为当时我的祖父试图进入房子,携带在他的怀里一大瓶,而不是一个,打破在衣柜里的锤子。他通过在村里买了它,抢走时vrachihu。据我所知,瓶摔断。因为当我跑下楼到街上,妈妈和爷爷不明白这是什么...
当医生走进房间,在她面前放着一个绿色的怪物,有着巨大的屁股,包扎双眼。看到眼前这肯定感到震惊,她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奶奶追着他,一切都是相同的更硬,并准备在道德上,虽然不是医生。因此,它不是特别吃惊,就跑去打水,以节省vrachihu。我坐了至少一个小时的木桩。圣诞老人在院子里喊来了我的脚,将其插入,而不是木制的,我会一直无法运行。更妙的是,他将新买的奶瓶,并会保留我到她。
Vovka证实过敏和伤痕累累的手指,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实。他的眼睛没有出来,也没有腹泻。唯一不好的一点是,这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天走向绿色,更轻的一天。
我没打一样。爷爷说,最有可能的废话了我从来不敲门。不经意间可能会持续脑子飞了出去,然后我的父母会采取准确,奶奶跟爷爷没有白费脑筋,我还没有休息。但我是一个星期锁在房间里,被软禁,这将每周至少他们可以放松我。为了我的反对意见认为,孩子不能没有新鲜的空气,爷爷说 - 我每天跟你说过好几次在房间里放屁,我会吸入以后,伟大的户外,那么你将失去意识的过量的氧气。
好了,所以下周就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关键短语在这里 - 将有...
©澈类似的东西
资料来源:
- 过敏。祖母说。 - 你打赌。至少有三公斤巧克力skhuyarili 2吻。为了有腹泻冷冻和眼睛的额头povylazili。应该有这样贪婪地落到巧克力。父亲,拿Motik邻居,并推动对医生的。我们还是看一下手指和这个疯的。但愿裂缝或裂纹。这将是你这个混蛋破获更好。
当然,我想推力与他的祖父。我喜欢骑在摇篮里。 Odenesh头盔在他的头上,natyanesh篷布,并提出,如果在一个战斗机飞行。但爷爷对我说的家伙的脑袋,不是一个战士,就去邻居。这将是更好的,他把我和他在一起......
Vova在床上的奶奶的房间,生病了。那么,怎么病了?除了他的手指没伤。是不是一切正常了皮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撒有红色斑点,和我去所有的绿色点。
- 你的眼睛不会在额头上更多的爬?我感兴趣的Vovka。
- 号负责沃夫克 - 但chyo已经开始伤害
。 - 一泻了吗?我想,我没有威胁,我不只是洒,但Vovka担心。
奶奶去了分钟一个小时邻居,希望这一次,我们不会将燃烧的房子,并没有飞走进入太空。因为如果房子会燃烧,这是我们塞上煤燃烧的屁股,这是一个经历白痴,因为不允许有更小的空间。屁股煤,我们不希望,我们是不会的空间。
我决定,只要爷爷去请医生,可能发生的麻烦。至于我能想象,爷爷和奶奶对我们根本不在乎。如果我们其中一人死亡,它会更容易。所以,我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决定,Vovka善待自己。我参加了一个急救箱的柜子,把从那里棉,绷带和泽伦卡。我的行为在我看来顺理成章。泽伦卡我要画在点绷带眼罩是来医生没有出来,羊毛紧密的屁股,这将是腹泻不obgadil巴布金床的案前。 Vovka困惑我的计划,但我的理由解释说,这一绷带,这样眼睛就不会失控,腹泻和泽伦卡过敏羊毛。所有的科学。首先我塞棉花内裤。在我看来一点,我加了纱布。然后,他摇了摇眼睛用绷带。你是过敏覆盖。我把棉絮斑,并开始作画。 10分钟后,我累了。景点非常多,非常小的。我拿着明智的决定采取,易油漆,不会磨折每个单独。几分钟后,有人做过。沃夫克是和干燥...
在院子里有一个崩溃的摩托车。医生赶到时,我才意识到,和得意坐下来等待,想象它是惊讶,说这是正确的对待它没有任何关系。所有主要的治疗进行,只是将手指将探索。
门开了,一个女医生走了进来,他的祖母。我决定等他在大厅的荣耀和走出了房间,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 这chёy你有手?我狐疑地问奶奶,暂停在我的身边,但她听到的答案没有来。医生走进房间Vovka ...
Ç尖叫 - 亲爱的妈妈!东西摔在地上。奶奶狐疑地看着我,跑了进来。
- 哦,你是一名儿科医生自制!奶奶跳出了房间,并跑到厨房。
我小心翼翼地凝视着房间,看到趴在地上vrachihu。不是偶然的,我想。奶奶飞进了房间,用毛巾和一杯水。开始喷上vrachihu和煽动她用毛巾。微弱的声音里面告诉你,什么是错的,但不强求。医生睁开眼睛,问,指着Vovka - 什么是与他?
在这里,外婆大概还记得我,因为她环顾四周,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苍蝇拍。她伸出手,看着我温柔地说, - 到这儿来,我的好。希波克拉底你自制。
我把它拿给了几句话,我故意退了回去。然后内心的声音吩咐 - 跑!我跑了。我跑尽我所能,与踹开前门崩溃。 Ç轰然从字面上看,因为当时我的祖父试图进入房子,携带在他的怀里一大瓶,而不是一个,打破在衣柜里的锤子。他通过在村里买了它,抢走时vrachihu。据我所知,瓶摔断。因为当我跑下楼到街上,妈妈和爷爷不明白这是什么...
当医生走进房间,在她面前放着一个绿色的怪物,有着巨大的屁股,包扎双眼。看到眼前这肯定感到震惊,她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奶奶追着他,一切都是相同的更硬,并准备在道德上,虽然不是医生。因此,它不是特别吃惊,就跑去打水,以节省vrachihu。我坐了至少一个小时的木桩。圣诞老人在院子里喊来了我的脚,将其插入,而不是木制的,我会一直无法运行。更妙的是,他将新买的奶瓶,并会保留我到她。
Vovka证实过敏和伤痕累累的手指,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实。他的眼睛没有出来,也没有腹泻。唯一不好的一点是,这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天走向绿色,更轻的一天。
我没打一样。爷爷说,最有可能的废话了我从来不敲门。不经意间可能会持续脑子飞了出去,然后我的父母会采取准确,奶奶跟爷爷没有白费脑筋,我还没有休息。但我是一个星期锁在房间里,被软禁,这将每周至少他们可以放松我。为了我的反对意见认为,孩子不能没有新鲜的空气,爷爷说 - 我每天跟你说过好几次在房间里放屁,我会吸入以后,伟大的户外,那么你将失去意识的过量的氧气。
好了,所以下周就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关键短语在这里 - 将有...
©澈类似的东西
资料来源:
标签
另请参见
我们永远不会住在勃列日涅夫
正如我们骗业务:启示工人
如何击退Desheli
方向盘后面
美国陆军 - 二十世纪最大的神话
只要你还记得俄罗斯
日记金发
最愚蠢的法律
HRENOVPAPASHA
所有国家的蒙昧主义,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