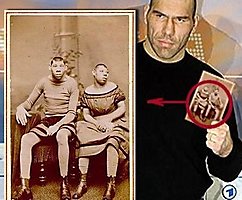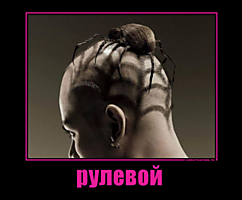这是什么?获得“奥斯卡”
 Bashny.Net
Bashny.Net
这是什么:是个侏儒,冻结在山中,获得“奥斯卡”生存雷击,以满足北极熊,改变地面和在月球上行走。

警告!
该材料的含量只适合成年人意欲(18以上)。
它是什么:要在月球上行走
巴兹·奥尔德林,73岁,宇航员
月亮“土壤”可与细碎的滑石进行比较。灰尘的顶层是很松散。在灰尘厚得多一个半厘米的深度 - 仿佛把持用水泥。事实上,没有颗粒粘接 - 简单,不像地球,有空气分子的分子之间没有灰尘
。
当你把你的脚上的灰尘,脚打印得到非常清楚,而不是抹黑。先走一步,我vzmetayutsya的尘面前,她扔下小半圆。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 - 地球本身上的灰尘没有这样做。月尘做任何事情不喜欢:在真空中,它属于完全同步,右侧形成一个半圆
。
我,我可以,我试着表达自己的话的经历,但美中不足的是,月球是不同的 - 什么也没有什么,他看到以前不比较。当你在你周围的月球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噪音套装 - 哼着泵,泵送液体。吸气,有源音箱,你不听 - 是好莱坞发明
。
要移动在月球上应该是在一种特殊的方式。最好的办法 - 一个快人一步,模仿策马奔腾,两个快速步骤 - 跳,两个快速的步骤。在月球上,就不可能控制的平衡。应当略微倾斜在任何方向和你可能下降。但抵制容易 - 只需靠着双脚的表面。到了月球表面是很容易适应的人。低重心使它很容易的步行距离。有伟大的。认真。
它是什么:神童考虑
亚历克斯Romanovsky,24,在电话领域的软件开发,电脑游戏程序员。民国13年,她高中毕业作为一个外部的学生,在14日,他成为了国际大学
的学生
由于矿井天主教规范的一个朋友 - 这是常态,而不是最常见的异常。长达六年,我从他们的同龄人是绝对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过度的爱情有关动物的故事,但我的父母以为我在“走在前面”,我仍然不知道他怎么样的想法。我开始读四年,我的母亲记得是一项重大成就几乎到了院。六年来,我在化学课本九年级的阁楼里找到,当然,没明白。不存在的“氧化物”的订阅浓缩配方,发明不存在连接,和谐 - “臭氧氮,”这就够了我的父母决定,我走了化学极大的兴趣。看到自己,他们说服了我,所以就开始了我的业余讨伐 - 从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
家庭相传在二年级我是“乐此不疲地学习。”事实是,母亲听到外部的研究,并决定将她的儿子应得的。我不介意。第二类,我通过为期两个月(去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第四 - 在夏天,第六,第七和第八 - 两个学年。我有这些转变从等级等级喜欢,可以这么说,美观。有一些美日计划全年俄语课程三部分,并处理它在过去的一个月。
特殊的过程对我来说的复杂性没有代表。更确切地说,如果所表示的,间接的方式:本病 - 支气管炎五年来,艰难的时代,懒惰 -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掌握两种。在九年级,我被转移到物理和数学的学校,这是真的很难。我们不能说,我无法应付的节目,但“份外的优点”是不是第一次。
我没有注意到人们十七年。起初不知道如何生活是的正规知识的目标;然后我开始明白,但坏东西 - 这是非常有益戴口罩无处不在,享受依托古怪教授的好处
。
我觉得对不起那些谁失去了童年的足球。到现在为止,我不明白,为什么22人球跑。成人儿童玩具更有意思。这就是我的童年,我同意:当我发明的玩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基辅和哈萨克斯坦,至于你玩你最喜欢的玩具,交钱,并邀请到会议的事实
。
我看到很多羡慕我。但是,还没有熟悉。然后意识到,偏心 - 不一定是超人,他是没有比一般的孩子更能力,它只是不同。如果汽车不用汽油的消耗,它使用了别的东西。
它是什么:生存雷击
最大迪林,44岁,音
这是星期五。这是一个典型的七月天:阳光明媚,白云浮动郁郁葱葱......四我和同事去达勒姆打高尔夫球。我们到了第五洞,然后细雨。我们决定在树冠下等待。我记得,空气里飘荡着甜香的臭氧。这是最后一件事我记得以前闪电击中。
当位滑落,我愣了一切 - 我从来没有那么冷,但我的身体的同时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晕。随后赶来的最美妙的噪音,这是我听到过。声音太大了,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声音,说实话。我不得不说我在两个垃圾桶和splyusnuli之间放的感觉。像所有流感病毒,这是我被感染了的生活,他在人群中我厉声说道。手,脚,手指都充满了重量 - 它似乎是这样,他们权衡2000千克。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疼痛难忍痛苦。疼痛呈钝痛,酸痛,并在同一时间尖锐。我甚至伤头发和睫毛。
闪电击中一棵树在我们旁边,敲几个分支流入篷,通过一个巨大的洞,这打破,然后经历了特里,我的一个朋友。我进入它通过表冠和经历了膝盖。特里当场死亡。打破掉在了地上,闪电般站在了我,去了他的头,离开出口:八针不得不实行。现在我可以prodelyvat相当复杂的计算 - 三角那里,数学分析,但不要问我增加或减少。这是没有用的。医生说我有一件事情都井井有条,但我知道 - 他们有一些东西我隐瞒
。
它是什么:采取集体淫乱
部分
该人士不愿透露姓名
集团性是喜欢有一个受过训练的章鱼性别:你周围的固体四肢和舌头,一个人的手抓住你拉,双腿分开在嘴里的东西挤压,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感情和性欲,而事实上,卷入你的故事,也屈服于这样多。
集团性可以让你看怎么难看是毫不掩饰的欲望。除了在情况下,房子的主人或女主人让党只专门培育杂交具有完善的机构,通常不完全去那些你希望看到的。妇女仍然在这里和那里 - 从昏暗的灯光和化妆,他们大大受益。至于男人......所有这些突出的成员,啤酒肚,头发年底在所有的地方......坐下来,打伤他的阴囊可怜,不顾一切地恢复它们。弗洛伊德认为,我们都是一点点同性恋者。那么,弗洛伊德是对没有争论,但如此多的男性望而却步狩猎甚至坚定的同性恋者。
尽管如此,群体性 - 这是惊人的!听到突突交配权在你的后院,很高兴能成为意外强劲。女性......一出,立即和另一个,不久后她的第三个......当你走进一个女人,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你觉得什么样的感觉,其他通过相对薄膜...
而这段时间,直到你回家乘坐出租车,第二天早上煮自己的煎蛋卷,然后坐在办公室里,你觉得只有一件事:“我在群交了一部分,我会再次这样做»
它是什么:从嗜睡症
患
旋律Zarnk,45年
如果一个正常的人要觉得自己像一个发作性睡眠病,虽然2天不肯睡觉。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的折磨。在二十一岁,我注意到,如果我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定要拉过来,有点打盹。我决定,我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睡眠,但它是发作性睡病的首发症状。一个健康的人开始梦想半小时入睡后。发作性睡眠病进入梦想的阶段瞬间。我的梦想张开眼睛,即使醒了。对我来说,梦想就像是幻觉 - 可怕的现实。如果我的梦想,我被咬伤一只蚊子,我感到奇痒难忍。它发生,我忘了几秒钟。特别是如果你做任何重复运动。有一次,我醉倒在电影院看电影时,笑了起来。我的头回落,眼前的一切黑暗。我不能动,不能头向后仰到正确的位置 - 好了,我的丈夫帮助。科学家已经接近创造可能帮助,如果我的病的药物。我不奉承自己,但很高兴去,而不用担心睡觉...
这是什么:是一个侏儒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66岁,男演员(高130厘米)
我生活在和谐的世界和自己。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很高兴。首先,当然,他们担心 - 他们无法弄清楚谁是一般出生(我出生一个大脑袋,小手和脚,并增加了30厘米)。在医院里给他的母亲立刻上前医生,谁说,相形见绌,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秩序,他们真的要我给他们科学的利益。但我的妈妈压我去她的乳房,说她把我养大。
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在爱长大,并与他们的差异性方面没有特别困难的经历。我有一个正常的公寓里,没有什么会适合在我的身高 - 标准身高厕所等。什么也没有改变专门为我。如果我是一个半 - 是的,这将是一个问题。碰巧我来说,不能达到电铃。不要担心。某处我能跳什么的起床。在极端情况下,到达,手里拿着一本书。
如果我不是一个侏儒,我没有发票,从来没有人问我要出演一部电影,然后在影院播放。当我注意到,在爵士俱乐部,并呼吁黑海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角色,我是从很远 - 我迷上了科学,电子学,音乐,抽象艺术,演艺事业没想到连。现在,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在Nikitsky门的大舞台上扮演 - 一般,没什么可抱怨的
。
唯一的问题是,一旦一个人生活。我出生于1939年,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是肌肉的一战 - ,分别与梦想的女孩一个坚强的人。我已经完全不同。有一天,我打电话爱情交待同学。它是没有过多的美味告诉我说:“是的,你看看你自己在镜子”我所有的四个妻子 - 大美和心灵的女人。因为我旁边的任何傻瓜不能。而丑也。这样的女人往往从复合物和所有试图维护自己的男人牺牲受苦。我对这个角色不适合。如果现在好耶走过来,问我,如果我想,我的胳膊和腿的正常长度,我会说,“不,我想我过的生活。我是个什么»。
它是什么:是高于一切
布拉德利,31岁,身高230厘米,中央“达拉斯小牛»
如何开始我的一天吗?在早上,我起床去厕所 - 这意味着我必须在门的第一天前,弯下身来。我弯下腰去照镜子,弯腰洗澡(淋浴头靠在我的胸口)。要进入车内,我第一次推到机舱腿弯曲在膝盖,并把她放在乘客座位的前面。然后,他滑倒进入车内。你可以叫我“男人蛇»。
所有的衣服我穿,有必要缝订购。我有一个52英尺的大小,所以连鞋子都订购。我甚至一个睡袋和帐篷为了缝合。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异国场比赛。我们走进了更衣室。我耸立在了衣柜,看到的一切,积累:防尘,空塑料瓶,是走神知道什么时候衣裳,把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的教练 - 他为30cm我下面 - 站起来了板凳上,是在我的眼睛的水平,说:“你住在一个肮脏的世界,对吧?”这是正确的 - 我住在一个布满灰尘和肮脏的世界。当我前来参观,那么,伏在门前,就注意到了灰尘的时候门楣。和冰箱顶部总是脏。而在人群中,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秃顶。的奇观马马虎虎......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比我高,但有时我的梦想,我遇到这样的人。
它是什么:通过真人秀
定向
列昂尼德·居内伊,42,的真人秀节目“DOM-1”,“DOM-2”,“大哥«
主任
恐怖的是,什么都不指挥。所以,你学到了什么都生活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任务 - 这是美丽的,在没有任何干预,删除把学员自己。你可以把它叫做冷嘲热讽。不管你怎么同情态度的参与者,为企业着想,选择情节有趣的观众,而不是一个在最好的指示灯显示的功臣。项目参与者知道,他们将记录24小时,他们同意了。 Ciloy他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拖着。如果我的孩子想在这类节目采取行动,我可能会试图劝阻他,但干预 - 不是。唯一的一点,他就必须记住:在真人秀节目,在法庭上 - 你说什么都可以用来对付你
。
它是什么:是人质
纳塔利娅·梅德韦杰夫41,一个摄影师
当事件发生在Budennovsk,我的老板不准我去杂志说,已经有两家的编辑派往那里。在抓获的女性的第四天开始离开医院婴儿。我看到这张照片,心想:“我的上帝!那么,我在这里!“飞到矿泉城。当我到了医院(我是愚蠢的人受伤的道路上),已经有记者的谁将会是自愿的,将伴随着人质车臣巴萨耶夫的边境名单。我是三百一些,但显然的机会变得有点。然后有一个新闻秘书,并要求各写一张收据,他说,在发生死亡索赔都没有。有人问:“什么是明确的 - 死吗?”“嗯, - 负责书记 - 退出门,并在那里等你。”人群散去大幅希望。三名男子离开了。我告诉他们:“我们越有,越少的机会,他们会杀了。”其结果是,累计14人。我们去了三天......噩梦......一切的时候感觉像一袋土豆 - 的主题。如果你听到直升机的噪音,坐下,转身,动作将你的肩膀和手臂准备战斗。和理解:如果炮击,你 - 非常的事情,他会躲起来。所有在等待攻击 - 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脱下。花膜。我把它再铺设了无处不在 - 在胸罩,内裤。我已经准备好什么可能闯入进攻件。如果你看到身体的一部分,与这部电影就会明白,这就是我。在手臂,腿,胸,肩,腹, - - 到处都一样我在医院里的妇女是谁写自己的护照信息,名字到处看到的。为了鉴定。我还没来得及写,我躺在了所有的电影。当我们去那里,人们在公共汽车隐藏。当他们回来了 - 他们逃到了美国。当一切结束,男子下了车,靠在热熨斗哭泣。是的,很多男人哭了,我记得。
这是什么:是一个雌雄同体
吉姆·科斯蒂奇,48,前助理
比如我指的是所谓“阴阳人”了。我出生的时候,医生们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我地板 - 生殖器图片是矛盾的。阴道显然不存在,但没有睾丸。这身体,我还是原来,他同样可以传递一个大阴蒂或小阴茎。我叫他“falloklit。”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成长为近3,81公分。从幼儿教育,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男孩。意识到这一点,四年的家长开始给我打电话詹姆斯,但它是非官方的绰号。其实,我出生时的名字被赋予的朱迪思。它仍然是并出现在我的文档。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出国旅行 - 无法取回护照
在44年,我发现,我有一个阴道,而是融合。另外,我有个小小萎缩的子宫和卵巢。我有两条X染色体,也就是说,遗传我是个女人,但在子宫里,我得到一个巨大的剂量的雄性激素。阴道管我,但其中的油脂被释放。

警告!
该材料的含量只适合成年人意欲(18以上)。
它是什么:要在月球上行走
巴兹·奥尔德林,73岁,宇航员
月亮“土壤”可与细碎的滑石进行比较。灰尘的顶层是很松散。在灰尘厚得多一个半厘米的深度 - 仿佛把持用水泥。事实上,没有颗粒粘接 - 简单,不像地球,有空气分子的分子之间没有灰尘
。
当你把你的脚上的灰尘,脚打印得到非常清楚,而不是抹黑。先走一步,我vzmetayutsya的尘面前,她扔下小半圆。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 - 地球本身上的灰尘没有这样做。月尘做任何事情不喜欢:在真空中,它属于完全同步,右侧形成一个半圆
。
我,我可以,我试着表达自己的话的经历,但美中不足的是,月球是不同的 - 什么也没有什么,他看到以前不比较。当你在你周围的月球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噪音套装 - 哼着泵,泵送液体。吸气,有源音箱,你不听 - 是好莱坞发明
。
要移动在月球上应该是在一种特殊的方式。最好的办法 - 一个快人一步,模仿策马奔腾,两个快速步骤 - 跳,两个快速的步骤。在月球上,就不可能控制的平衡。应当略微倾斜在任何方向和你可能下降。但抵制容易 - 只需靠着双脚的表面。到了月球表面是很容易适应的人。低重心使它很容易的步行距离。有伟大的。认真。
它是什么:神童考虑
亚历克斯Romanovsky,24,在电话领域的软件开发,电脑游戏程序员。民国13年,她高中毕业作为一个外部的学生,在14日,他成为了国际大学
的学生
由于矿井天主教规范的一个朋友 - 这是常态,而不是最常见的异常。长达六年,我从他们的同龄人是绝对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过度的爱情有关动物的故事,但我的父母以为我在“走在前面”,我仍然不知道他怎么样的想法。我开始读四年,我的母亲记得是一项重大成就几乎到了院。六年来,我在化学课本九年级的阁楼里找到,当然,没明白。不存在的“氧化物”的订阅浓缩配方,发明不存在连接,和谐 - “臭氧氮,”这就够了我的父母决定,我走了化学极大的兴趣。看到自己,他们说服了我,所以就开始了我的业余讨伐 - 从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
家庭相传在二年级我是“乐此不疲地学习。”事实是,母亲听到外部的研究,并决定将她的儿子应得的。我不介意。第二类,我通过为期两个月(去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第四 - 在夏天,第六,第七和第八 - 两个学年。我有这些转变从等级等级喜欢,可以这么说,美观。有一些美日计划全年俄语课程三部分,并处理它在过去的一个月。
特殊的过程对我来说的复杂性没有代表。更确切地说,如果所表示的,间接的方式:本病 - 支气管炎五年来,艰难的时代,懒惰 -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掌握两种。在九年级,我被转移到物理和数学的学校,这是真的很难。我们不能说,我无法应付的节目,但“份外的优点”是不是第一次。
我没有注意到人们十七年。起初不知道如何生活是的正规知识的目标;然后我开始明白,但坏东西 - 这是非常有益戴口罩无处不在,享受依托古怪教授的好处
。
我觉得对不起那些谁失去了童年的足球。到现在为止,我不明白,为什么22人球跑。成人儿童玩具更有意思。这就是我的童年,我同意:当我发明的玩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基辅和哈萨克斯坦,至于你玩你最喜欢的玩具,交钱,并邀请到会议的事实
。
我看到很多羡慕我。但是,还没有熟悉。然后意识到,偏心 - 不一定是超人,他是没有比一般的孩子更能力,它只是不同。如果汽车不用汽油的消耗,它使用了别的东西。
它是什么:生存雷击
最大迪林,44岁,音
这是星期五。这是一个典型的七月天:阳光明媚,白云浮动郁郁葱葱......四我和同事去达勒姆打高尔夫球。我们到了第五洞,然后细雨。我们决定在树冠下等待。我记得,空气里飘荡着甜香的臭氧。这是最后一件事我记得以前闪电击中。
当位滑落,我愣了一切 - 我从来没有那么冷,但我的身体的同时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晕。随后赶来的最美妙的噪音,这是我听到过。声音太大了,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声音,说实话。我不得不说我在两个垃圾桶和splyusnuli之间放的感觉。像所有流感病毒,这是我被感染了的生活,他在人群中我厉声说道。手,脚,手指都充满了重量 - 它似乎是这样,他们权衡2000千克。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疼痛难忍痛苦。疼痛呈钝痛,酸痛,并在同一时间尖锐。我甚至伤头发和睫毛。
闪电击中一棵树在我们旁边,敲几个分支流入篷,通过一个巨大的洞,这打破,然后经历了特里,我的一个朋友。我进入它通过表冠和经历了膝盖。特里当场死亡。打破掉在了地上,闪电般站在了我,去了他的头,离开出口:八针不得不实行。现在我可以prodelyvat相当复杂的计算 - 三角那里,数学分析,但不要问我增加或减少。这是没有用的。医生说我有一件事情都井井有条,但我知道 - 他们有一些东西我隐瞒
。
它是什么:采取集体淫乱
部分
该人士不愿透露姓名
集团性是喜欢有一个受过训练的章鱼性别:你周围的固体四肢和舌头,一个人的手抓住你拉,双腿分开在嘴里的东西挤压,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感情和性欲,而事实上,卷入你的故事,也屈服于这样多。
集团性可以让你看怎么难看是毫不掩饰的欲望。除了在情况下,房子的主人或女主人让党只专门培育杂交具有完善的机构,通常不完全去那些你希望看到的。妇女仍然在这里和那里 - 从昏暗的灯光和化妆,他们大大受益。至于男人......所有这些突出的成员,啤酒肚,头发年底在所有的地方......坐下来,打伤他的阴囊可怜,不顾一切地恢复它们。弗洛伊德认为,我们都是一点点同性恋者。那么,弗洛伊德是对没有争论,但如此多的男性望而却步狩猎甚至坚定的同性恋者。
尽管如此,群体性 - 这是惊人的!听到突突交配权在你的后院,很高兴能成为意外强劲。女性......一出,立即和另一个,不久后她的第三个......当你走进一个女人,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你觉得什么样的感觉,其他通过相对薄膜...
而这段时间,直到你回家乘坐出租车,第二天早上煮自己的煎蛋卷,然后坐在办公室里,你觉得只有一件事:“我在群交了一部分,我会再次这样做»
它是什么:从嗜睡症
患
旋律Zarnk,45年
如果一个正常的人要觉得自己像一个发作性睡眠病,虽然2天不肯睡觉。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的折磨。在二十一岁,我注意到,如果我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定要拉过来,有点打盹。我决定,我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睡眠,但它是发作性睡病的首发症状。一个健康的人开始梦想半小时入睡后。发作性睡眠病进入梦想的阶段瞬间。我的梦想张开眼睛,即使醒了。对我来说,梦想就像是幻觉 - 可怕的现实。如果我的梦想,我被咬伤一只蚊子,我感到奇痒难忍。它发生,我忘了几秒钟。特别是如果你做任何重复运动。有一次,我醉倒在电影院看电影时,笑了起来。我的头回落,眼前的一切黑暗。我不能动,不能头向后仰到正确的位置 - 好了,我的丈夫帮助。科学家已经接近创造可能帮助,如果我的病的药物。我不奉承自己,但很高兴去,而不用担心睡觉...
这是什么:是一个侏儒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66岁,男演员(高130厘米)
我生活在和谐的世界和自己。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很高兴。首先,当然,他们担心 - 他们无法弄清楚谁是一般出生(我出生一个大脑袋,小手和脚,并增加了30厘米)。在医院里给他的母亲立刻上前医生,谁说,相形见绌,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秩序,他们真的要我给他们科学的利益。但我的妈妈压我去她的乳房,说她把我养大。
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在爱长大,并与他们的差异性方面没有特别困难的经历。我有一个正常的公寓里,没有什么会适合在我的身高 - 标准身高厕所等。什么也没有改变专门为我。如果我是一个半 - 是的,这将是一个问题。碰巧我来说,不能达到电铃。不要担心。某处我能跳什么的起床。在极端情况下,到达,手里拿着一本书。
如果我不是一个侏儒,我没有发票,从来没有人问我要出演一部电影,然后在影院播放。当我注意到,在爵士俱乐部,并呼吁黑海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角色,我是从很远 - 我迷上了科学,电子学,音乐,抽象艺术,演艺事业没想到连。现在,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在Nikitsky门的大舞台上扮演 - 一般,没什么可抱怨的
。
唯一的问题是,一旦一个人生活。我出生于1939年,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是肌肉的一战 - ,分别与梦想的女孩一个坚强的人。我已经完全不同。有一天,我打电话爱情交待同学。它是没有过多的美味告诉我说:“是的,你看看你自己在镜子”我所有的四个妻子 - 大美和心灵的女人。因为我旁边的任何傻瓜不能。而丑也。这样的女人往往从复合物和所有试图维护自己的男人牺牲受苦。我对这个角色不适合。如果现在好耶走过来,问我,如果我想,我的胳膊和腿的正常长度,我会说,“不,我想我过的生活。我是个什么»。
它是什么:是高于一切
布拉德利,31岁,身高230厘米,中央“达拉斯小牛»
如何开始我的一天吗?在早上,我起床去厕所 - 这意味着我必须在门的第一天前,弯下身来。我弯下腰去照镜子,弯腰洗澡(淋浴头靠在我的胸口)。要进入车内,我第一次推到机舱腿弯曲在膝盖,并把她放在乘客座位的前面。然后,他滑倒进入车内。你可以叫我“男人蛇»。
所有的衣服我穿,有必要缝订购。我有一个52英尺的大小,所以连鞋子都订购。我甚至一个睡袋和帐篷为了缝合。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异国场比赛。我们走进了更衣室。我耸立在了衣柜,看到的一切,积累:防尘,空塑料瓶,是走神知道什么时候衣裳,把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的教练 - 他为30cm我下面 - 站起来了板凳上,是在我的眼睛的水平,说:“你住在一个肮脏的世界,对吧?”这是正确的 - 我住在一个布满灰尘和肮脏的世界。当我前来参观,那么,伏在门前,就注意到了灰尘的时候门楣。和冰箱顶部总是脏。而在人群中,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秃顶。的奇观马马虎虎......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比我高,但有时我的梦想,我遇到这样的人。
它是什么:通过真人秀
定向
列昂尼德·居内伊,42,的真人秀节目“DOM-1”,“DOM-2”,“大哥«
主任
恐怖的是,什么都不指挥。所以,你学到了什么都生活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任务 - 这是美丽的,在没有任何干预,删除把学员自己。你可以把它叫做冷嘲热讽。不管你怎么同情态度的参与者,为企业着想,选择情节有趣的观众,而不是一个在最好的指示灯显示的功臣。项目参与者知道,他们将记录24小时,他们同意了。 Ciloy他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拖着。如果我的孩子想在这类节目采取行动,我可能会试图劝阻他,但干预 - 不是。唯一的一点,他就必须记住:在真人秀节目,在法庭上 - 你说什么都可以用来对付你
。
它是什么:是人质
纳塔利娅·梅德韦杰夫41,一个摄影师
当事件发生在Budennovsk,我的老板不准我去杂志说,已经有两家的编辑派往那里。在抓获的女性的第四天开始离开医院婴儿。我看到这张照片,心想:“我的上帝!那么,我在这里!“飞到矿泉城。当我到了医院(我是愚蠢的人受伤的道路上),已经有记者的谁将会是自愿的,将伴随着人质车臣巴萨耶夫的边境名单。我是三百一些,但显然的机会变得有点。然后有一个新闻秘书,并要求各写一张收据,他说,在发生死亡索赔都没有。有人问:“什么是明确的 - 死吗?”“嗯, - 负责书记 - 退出门,并在那里等你。”人群散去大幅希望。三名男子离开了。我告诉他们:“我们越有,越少的机会,他们会杀了。”其结果是,累计14人。我们去了三天......噩梦......一切的时候感觉像一袋土豆 - 的主题。如果你听到直升机的噪音,坐下,转身,动作将你的肩膀和手臂准备战斗。和理解:如果炮击,你 - 非常的事情,他会躲起来。所有在等待攻击 - 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脱下。花膜。我把它再铺设了无处不在 - 在胸罩,内裤。我已经准备好什么可能闯入进攻件。如果你看到身体的一部分,与这部电影就会明白,这就是我。在手臂,腿,胸,肩,腹, - - 到处都一样我在医院里的妇女是谁写自己的护照信息,名字到处看到的。为了鉴定。我还没来得及写,我躺在了所有的电影。当我们去那里,人们在公共汽车隐藏。当他们回来了 - 他们逃到了美国。当一切结束,男子下了车,靠在热熨斗哭泣。是的,很多男人哭了,我记得。
这是什么:是一个雌雄同体
吉姆·科斯蒂奇,48,前助理
比如我指的是所谓“阴阳人”了。我出生的时候,医生们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我地板 - 生殖器图片是矛盾的。阴道显然不存在,但没有睾丸。这身体,我还是原来,他同样可以传递一个大阴蒂或小阴茎。我叫他“falloklit。”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成长为近3,81公分。从幼儿教育,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男孩。意识到这一点,四年的家长开始给我打电话詹姆斯,但它是非官方的绰号。其实,我出生时的名字被赋予的朱迪思。它仍然是并出现在我的文档。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出国旅行 - 无法取回护照
在44年,我发现,我有一个阴道,而是融合。另外,我有个小小萎缩的子宫和卵巢。我有两条X染色体,也就是说,遗传我是个女人,但在子宫里,我得到一个巨大的剂量的雄性激素。阴道管我,但其中的油脂被释放。
标签
另请参见
北极熊
龟11种怪异
照片画廊有趣的图片
水世界的8最美丽的风景
自行车埋在一棵树上
原始的方式来致富
Evolution'll永远需要
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在未来10年?
过山车
硬antigeyskie法律